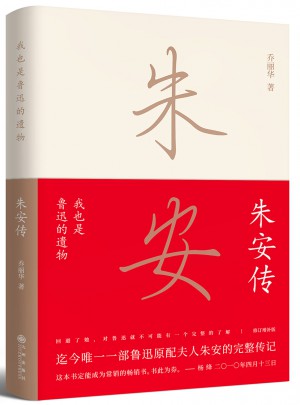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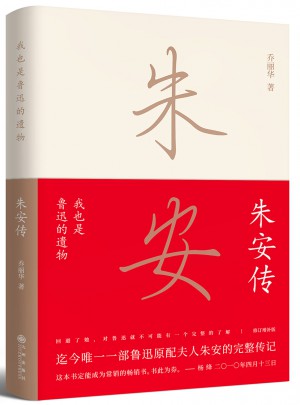
“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diǎn)一點(diǎn)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24小時(shí)會(huì)爬到墻頂?shù)?hellip;…”
“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gè)目不識(shí)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yǔ)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尋味。她凄風(fēng)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回味。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是魯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傳記,作者喬麗華通過(guò)走訪朱氏后人,實(shí)地勘查采訪,鉤沉相關(guān)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運(yùn)用報(bào)刊資料、回憶錄、文物、生活等資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duì)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wú)聲之聲。
楊絳先生讀之哀嘆,感動(dòng)推薦!朱正、陳漱渝、陳丹青、楊光祖等盛贊推薦之作。
披露魯迅婚姻與生活中諸多鮮為人知的生動(dòng)細(xì)節(jié)。
嘔心瀝血,歷時(shí)11載,平實(shí)、客觀,鉤沉朱安不為人知的69個(gè)春秋。
寥寥數(shù)語(yǔ),多少云煙往事,多少喜樂(lè)悲歡,令人體味不盡。
生前孤獨(dú),身后寂寥。風(fēng)云激蕩的歷史交匯處,一代知識(shí)分子背后傳統(tǒng)女性的命運(yùn)寫真。
書中多幅作者實(shí)地拍攝的照片和手繪布局圖,給讀者更直觀的體驗(yàn)和更強(qiáng)的代入感。
本書刊用的朱安的書信及照片,絕大部分珍藏于北京魯迅博物館,其中有些從未發(fā)表過(guò)。
一部不僅需要知識(shí)、智慧,更需要勇氣和擔(dān)當(dāng)之作。
附“朱安家世簡(jiǎn)表”“1923-1926年魯迅家用賬”“《世界日?qǐng)?bào)》等媒體對(duì)救助魯迅遺族與藏書的報(bào)道”等珍貴史料。
喬麗華,女,上海人。2001年畢業(yè)于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獲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現(xiàn)為上海魯迅紀(jì)念館研究室研究館員。多年來(lái)從事魯迅研究及現(xiàn)代作家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美聯(lián)”與左翼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2016年)、《藏家魯迅》(2004年)等。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文/陳漱渝
再版前
序章:“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母親的禮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約——1899年前后
洞房——母親的禮物
獨(dú)守——婚后的處境
惜別——舉家遷居北京
落地的蝸牛
死寂——名存實(shí)亡的家
深淵——落地的蝸牛
家用賬——真實(shí)的重?fù)?dān)
書信——與上海的距離
悲傷——魯迅去世
苦境——西三條的女主人
尾聲——祥林嫂的夢(mèng)
附錄一 朱安家世簡(jiǎn)表
附錄二 魯迅家用賬(自公歷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
附錄三 抗戰(zhàn)后北平《世界日?qǐng)?bào)》“明珠”版有關(guān)朱安的報(bào)道
主要參考文獻(xiàn)
后記
洞房——母親的禮物
“養(yǎng)女不過(guò)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兩家訂立婚約,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魯迅也曾回國(guó)探親,但婚禮并沒(méi)有舉行。我們不知道朱安的父親朱耀庭究竟去世于哪一年,他終年尚不到50歲,從朱安的年紀(jì)推算,大概就在這期間。如果是這樣,那么這也給了魯迅一個(gè)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于紹興,終年68歲,魯迅并未回國(guó)奔喪。1906年,轉(zhuǎn)眼又是兩年過(guò)去了,紹興向有“養(yǎng)女不過(guò)二十六”的規(guī)矩,而朱安已經(jīng)28歲了。
朱家臺(tái)門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但朱安的遠(yuǎn)房叔祖朱霞汀及父親朱耀庭相繼去世,對(duì)朱家臺(tái)門想必是不小的打擊。還有一點(diǎn)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復(fù)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歲月,在那個(gè)年代,到了她這樣的年紀(jì)還沒(méi)有出嫁,處境無(wú)疑是很尷尬的。
從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對(duì)窄而尖的三寸金蓮。明清以來(lái),在人們的觀念中,“在精美小鞋裝飾下的一雙纏得很好的雙腳,既是女性美,也是階層區(qū)別的標(biāo)志。”當(dāng)時(shí)一般紹興女子都纏足,否則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約5歲至7歲的時(shí)候,母親或族中的婦女就為她纏足,以便將來(lái)嫁個(gè)好人家。卻沒(méi)有想到,有24小時(shí)這雙小腳會(huì)變得不合時(shí)宜。
據(jù)周冠五回憶,魯迅曾從日本來(lái)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魯瑞則叫周冠五寫信勸說(shuō)魯迅,強(qiáng)調(diào)這婚事原是她求親求來(lái),不能退聘,否則,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譽(yù)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沒(méi)人要娶了。作為讓步,魯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進(jìn)學(xué)堂,但朱家拒絕了。
魯迅在日本時(shí)期,并沒(méi)有特別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見,他見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夠閱讀,寫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里,留辮子、纏足都是野蠻的土人的習(xí)俗,這使許多留日學(xué)生深受刺激。實(shí)際上,自康梁維新以來(lái),國(guó)內(nèi)也有逐漸形成戒纏足的輿論,放足思想已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紛紛成立不纏足會(huì)或天足會(huì),響應(yīng)者也很多。但在內(nèi)地鄉(xiāng)野,此種陋習(xí)要革除并非易事,清末的紹興顯得相對(duì)閉塞,朱家看來(lái)也是個(gè)保守的家族。應(yīng)該說(shuō),魯迅勸朱家姑娘放腳讀書,也不是心血來(lái)潮,而是真心希望縮短兩人之間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寫信,互相通通信,或許多少能培養(yǎng)出一些感情吧?可是,由于種種原因,朱安在這兩方面都沒(méi)能做到。
在當(dāng)時(shí),朱安的年紀(jì)確實(shí)很大了,朱家本來(lái)已經(jīng)憂心忡忡,偏偏有傳言說(shuō)魯迅已經(jīng)和日本女人結(jié)婚,而且還有人親眼看見他帶著兒子在神田散步。這使朱家十分驚慌,也最終促使魯瑞下決心把魯迅召回國(guó)。多年以后魯老太太懷著內(nèi)疚對(duì)人說(shuō)起她把魯迅騙回國(guó)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兒年紀(jì)大了,一再托媒人來(lái)催,希望盡快辦理婚事。因?yàn)樗麄兟牭酵饷嬗行┎蝗凰牡闹{言,說(shuō)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實(shí)在被纏不過(guò),只得托人打電報(bào)給大先生,騙他說(shuō)我病了,叫他速歸。大先生果然回來(lái)了,我向他說(shuō)明原因,他倒也不見怪,同意結(jié)婚。
因?yàn)轸斞高t遲不歸,使得周朱兩家的長(zhǎng)輩都很焦急。不得已魯瑞略施小計(jì),托人打電報(bào)謊稱自己病危,讓魯迅速歸。同時(shí)開始重修家中的房屋,準(zhǔn)備為魯迅辦婚事。
三弟周建人當(dāng)時(shí)18歲,在離家很近的塔子橋邊的馬神廟里的小學(xué)教書,母親是否曾托他寫信或打電報(bào)給大哥呢?遺憾的是在他的回憶里全然沒(méi)有提及。據(jù)他回憶,1906年夏初,他從學(xué)堂回到家,看見家里來(lái)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這時(shí)他才知道,母親急于修理房子,是因?yàn)闇?zhǔn)備給大哥辦婚事了。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憶:“為什么荒廢了幾十年的破房子,在這時(shí)候重新來(lái)修造的呢?自從房屋被太平天國(guó)戰(zhàn)役毀壞以來(lái),已經(jīng)過(guò)了四十多年,中間祖父雖點(diǎn)中了翰林,卻一直沒(méi)有修復(fù)起來(lái)。后來(lái)在北京做京官,捐中書內(nèi)閣,以及納妾,也只是花錢,沒(méi)有余力顧到家里。這回卻總算修好,可以住人了。這個(gè)理由并不是因?yàn)橛辛α啃薹孔樱依镞€是照舊的困難,實(shí)在乃因必要,魯迅是在那一年里預(yù)備回家,就此完姻的。樓上兩間乃是新房,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說(shuō)法:“魯迅是在那一年里預(yù)備回家,就此完姻的。”不過(guò)他也聲明自己當(dāng)時(shí)在外讀書,對(duì)重修房屋與魯迅結(jié)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憶里也說(shuō):“……后來(lái)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jié)果魯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應(yīng)了,說(shuō)幾時(shí)結(jié)婚幾時(shí)到,于是定局結(jié)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guó),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dāng)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 周冠五《我的雜憶》,《魯迅家庭家族和當(dāng)年紹興民俗》,第245頁(yè)。事情的進(jìn)程當(dāng)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說(shuō)的那么簡(jiǎn)單,但他的說(shuō)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xué)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jì)念魯迅逝世三周年的會(huì)上他也說(shuō)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xué)醫(yī)的。他受的是很嚴(yán)格的科學(xué)訓(xùn)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duì)人說(shuō):‘我不知什么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guó)去結(jié)婚,他不愿放棄學(xué)業(yè)不肯回去。后來(lái)家中打電報(bào)來(lái)了,說(shuō)母病危,先生回國(guó)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結(jié)婚的布置都已停當(dāng),只等他回來(lái)作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duì)事奮斗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duì)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國(guó),包辦婚姻是天經(jīng)地義,悔婚是很嚴(yán)重的事。魯老太太把魯迅騙回國(guó),實(shí)為無(wú)奈之舉。其實(shí),這24小時(shí)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犧牲掉個(gè)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yùn)。
假裝大腳的新娘
1906年農(nóng)歷六月初六,魯迅與朱安在周家新臺(tái)門的大廳舉行了婚禮。從1899年與周家少爺訂婚到二人舉行結(jié)婚儀式,朱安等了七年,終于等來(lái)了這24小時(shí)。她想必也隱約聽說(shuō)了,周家少爺對(duì)這樁婚事不太滿意。也許,就是在長(zhǎng)達(dá)七年的近乎絕望的等待中,她記住了長(zhǎng)輩們常在她耳邊說(shuō)的那句話:“生為周家人,死為周家鬼。”按當(dāng)時(shí)紹興風(fēng)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無(wú)異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恥辱。既然和周家少爺訂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沒(méi)有退路。這或許也注定了她日后凄風(fēng)苦雨的一生。
參加婚禮的有三個(gè)臺(tái)門里的本家,還有其他一些客人,老臺(tái)門的熊三公公是族長(zhǎng),這天前來(lái)主持拜堂。對(duì)舊式婚禮種種繁瑣的儀式,魯迅均一一照辦,沒(méi)有任何違抗。他后來(lái)回憶當(dāng)時(shí)的情景說(shuō):“那時(shí)家里人因?yàn)槁犝f(shuō)我是新派人物,曾擔(dān)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對(duì)舊式的婚禮。可我還是默默地按他們說(shuō)的辦了。”魯迅對(duì)鹿地亙私下的談話,見鹿地亙?yōu)槿毡景妗洞篝斞溉穼懙摹遏斞競(jìng)饔洝贰?/p>
結(jié)婚當(dāng)天,周家少爺最惹人注目的是他頭上的假辮子,對(duì)此,魯迅的從弟周光義曾有一番繪聲繪色的描述:“六月初六這24小時(shí),新臺(tái)門周家辦起喜事來(lái)。早上,新郎本來(lái)是剪掉辮子的,如今戴著一頂羅制的筒帽(有點(diǎn)像后來(lái)的拿破侖帽),裝著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辮子,身上的服裝用套袍,外面罩上紗套,腳上穿著靴子。禮堂不知道什么道理設(shè)在神堂下。新娘從花轎里走出來(lái),看去全身古裝,穿著紅紗單衫,下邊鑲有棉做的滾邊,下面是黑綢裙。一對(duì)新夫婦拜堂過(guò)后,被老嫚 舊時(shí)越中陋俗,墮民只能從事賤業(yè),不得與四民通婚。女性墮民俗稱“老嫚”,從事逢年過(guò)節(jié)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慶吊諸事去幫幫忙之類的營(yíng)生,從中得到若干賞錢、賞物。等人擁擠的送進(jìn)樓上的新房。”
周光義出生于1906年,系周椒生長(zhǎng)孫、周仲翔長(zhǎng)子。周椒生是魯迅的堂叔祖,曾把魯迅、周作人等介紹到南京江南水師學(xué)堂讀書。魯迅結(jié)婚的場(chǎng)面顯然是周光義從長(zhǎng)輩那里聽來(lái)的,或者是按照舊式婚禮的通常情況推想出來(lái)的。魯迅裝一條假辮子的事,給參加婚禮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記得很清楚。魯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辮子,然而在婚禮上卻須一切照舊,要裝上一條假辮子,戴上紅纓大帽。這對(duì)后來(lái)成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先驅(qū)的魯迅來(lái)說(shuō),無(wú)疑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裝大腳。據(jù)魯老太太回憶,魯迅曾從日本寫信回來(lái),要求朱家姑娘放腳:“大先生不喜歡小腳女人,但他認(rèn)為這是舊社會(huì)造成的,并不以小腳為辭,拒絕這門婚事,只是從日本寫信回來(lái),叫家里通知她放腳。”周冠五在《我的雜憶》里也說(shuō):“魯母知道我和魯迅在通信,就叫我寫信勸他,我寫信后得到魯迅回信,他說(shuō):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兩個(gè)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jìn)學(xué)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腳已放不大了,婦女讀書不大好,進(jìn)學(xué)堂更不愿意。”從魯迅這方面來(lái)說(shuō),最初似乎也試圖和未婚妻有所溝通,縮短彼此的距離,可是朱家并沒(méi)有理會(huì)他提出的條件。朱安的態(tài)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魯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學(xué)的洗禮,不僅自己剪了辮,也很反對(duì)女人纏足。這一點(diǎn)朱家也明白,于是這天朱家特意讓新娘穿上大一號(hào)的鞋子,假裝大腳。多年以后魯老太太回憶婚禮的情景,說(shuō)了這樣一件事:結(jié)婚那天,花轎進(jìn)門,掀開轎簾,從轎里掉出來(lái)一只新娘的鞋子。因?yàn)樗_小,娘家替她穿了一雙較大的繡花鞋,腳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轎里,“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鞋子就掉下來(lái)了。……當(dāng)時(shí)有些老人說(shuō)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這些話,但愿這門親事順利。婚后沒(méi)幾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讀書。
朱家族人對(duì)當(dāng)年婚禮上一些小小的閃失也始終耿耿于懷:“魯迅結(jié)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親上加親(周玉田是朱先生朱先生指朱鹿琴。的親姑夫),我不僅去做了送親的舅爺,還接連的吃了好幾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過(guò)了堂,雙雙被人送入洞房,當(dāng)新郎走上樓梯的時(shí)候,賓客擁擠,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又有一個(gè)賀客,被招待住在一間裝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后,講話欠檢點(diǎn),向我說(shuō)他在昨夜遇鬼。你想,這人冒失不冒失!”
這是朱安的遠(yuǎn)房堂叔朱鹿琴多年以后的憶述。在朱家人看來(lái),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家賀客說(shuō)話欠檢點(diǎn),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來(lái),新娘鞋子掉下來(lái),是很不吉利的。據(jù)周光義說(shuō),身為新郎的魯迅,那時(shí)看上去是個(gè)英俊的青年,臉上生著白白的皮膚,身材比新娘高一點(diǎn)。而新娘顯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長(zhǎng)的馬臉,別的外表的缺點(diǎn)似乎沒(méi)有。這樣的兩個(gè)人,在老輩人眼里至少是可以過(guò)日子的,他們兩個(gè)為什么婚后過(guò)不到一起?雙方的家長(zhǎng)都想不通,只好歸因于婚禮中一些不好的兆頭,互相埋怨,互相責(zé)怪。
新婚之夜
魯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jīng)定局。
當(dāng)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進(jìn)了洞房。周冠五當(dāng)時(shí)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jié)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臺(tái)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jí)一級(jí)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shè)在靠東首的一間,房?jī)?nèi)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dāng)時(shí),魯迅一句話也沒(méi)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郁,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dāng)傭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魯迅結(jié)婚時(shí),他已經(jīng)18歲。他是及時(shí)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據(jù)他的回憶:“這年夏天,魯迅先生從日本回來(lái)與朱女士結(jié)婚的。這一次時(shí)間很短,我與魯迅先生也沒(méi)有講話,他當(dāng)時(shí)的穿著怎樣我也記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卻還記得。魯迅先生結(jié)婚是在樓上,過(guò)了一夜,第二夜魯迅先生就睡到書房里去了,聽說(shuō)印花被的靛青把魯迅先生的臉也染青了,他很不高興。當(dāng)時(shí)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臺(tái)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méi)有去。后來(lái)知道是魯迅先生對(duì)這樁包辦封建婚姻很不滿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書房里睡了。”
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xiàn)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像王鶴照這樣一個(gè)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個(gè)不為人所知的細(xì)節(jié):魯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鶴照的回憶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細(xì)節(jié),只是缺少旁證。有人指出,當(dāng)時(shí)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著蓋被子。對(duì)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méi)有這么戲劇性。據(jù)他說(shuō),當(dāng)時(shí)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dān)心著新夫婦的動(dòng)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fā)現(xiàn)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兩三天以后,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里了,晚上先看書,然后睡在母親的床邊的一張床里。
王鶴照說(shuō)因?yàn)轸斞傅诙煸绯坎桓吲d,“當(dāng)時(shí)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臺(tái)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méi)有去。”魯迅即便沒(méi)有拜老臺(tái)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duì)木制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jìn)來(lái),擺放在新娘床上,說(shuō):“官官來(lái)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討賞封。
接下來(lái)是“頭箸飯”,新郎新娘及時(shí)次一起吃飯,自然也只是一個(gè)儀式而已。之后要“上廟”,新夫婦坐著轎,老嫚、吹手跟在轎后,先到當(dāng)坊“土谷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dāng)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里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zhǎng)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接受小輩的拜禮。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門”,亦叫“轉(zhuǎn)郎”,新夫婦往女家回門,在老嫚、吹手的簇?fù)硐拢I來(lái)到女家,至大廳拜女家祖先,參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后,還要請(qǐng)新郎進(jìn)入內(nèi)房,坐在岳母身旁聽她致照例的“八句頭”,等八句頭說(shuō)完后新夫婦辭別上轎……
魯迅“回門”一事,朱家房客陳文煥曾回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gè)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說(shuō):‘朱家姑爺來(lái)回門,沒(méi)有辮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陳文煥談朱安家母等情況》。劉和尚講的“朱家姑爺”就是魯迅,前清時(shí)剪掉辮子,簡(jiǎn)直是特大號(hào)新聞,因此引來(lái)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雖然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我們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發(fā)生了什么,魯迅為什么會(huì)這么失望。對(duì)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yàn)橹彀布炔蛔R(shí)字,也沒(méi)有放足:“結(jié)婚以后,我大哥發(fā)現(xiàn)新娘子既不識(shí)字,也沒(méi)有放足,他以前寫來(lái)的信,統(tǒng)統(tǒng)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nèi)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rèn)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yīng)這樣一個(gè)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huì)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shuí)知會(huì)全盤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guò)遠(yuǎn)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duì)此沒(méi)有任何思想準(zhǔn)備。
周作人則說(shuō)“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fā)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lái)看,朱安的身材確實(shí)偏于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jié)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訴說(shuō)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duì)好友許壽裳說(shuō)過(guò)這么一句沉痛的話: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yǎng)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duì)朱安確實(shí)毫無(wú)感情,只有供養(yǎng)的義務(wù)。其實(shí),這句話更深刻之處在于,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憐的處境。“禮物”,《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釋為“為了表示尊敬或慶賀而贈(zèng)送的物品,泛指贈(zèng)送的物品。”朱安是一個(gè)人,怎么能說(shuō)她是一件贈(zèng)送給人的物品呢?然而,事實(shí)又的確如此。按照法國(guó)人類學(xué)者列維 斯特勞斯的說(shuō)法,在原始社會(huì)或者說(shuō)是野蠻社會(huì)中,“婚姻是禮品交換最基本的一種形式,女人是最珍貴的禮物。”“組成婚姻的交換總關(guān)系不是在一個(gè)男人和一個(gè)女人間建立起來(lái)的,而是在兩群男人之間。女人僅僅是扮演了交換中的一件物品的角色,而不是作為一個(gè)伙伴……”在中國(guó)兩千多年來(lái)一夫多妻制的社會(huì)里,女性向來(lái)只是一件附屬品,一件等待被接受的“禮物”,她的命運(yùn)取決于能否被贈(zèng)送到一個(gè)好人家,能否被接受者喜愛或善待。
因?yàn)?ldquo;母親”(其實(shí)是母親所代表的社會(huì)和家族)的要求,魯迅被迫成為“禮物”的接受者。據(jù)孫伏園說(shuō),魯迅雖然當(dāng)新郎,穿靴,穿袍,戴紅纓帽子,一切都照辦。但那時(shí)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結(jié)婚前一切我聽你作主,結(jié)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時(shí)你們可得聽我。”很明顯,魯迅將朱安僅僅視為一件禮物,作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禮物,那么就隨便他怎么安置這件禮物了。從這一點(diǎn)說(shuō),他還是個(gè)主動(dòng)者。婚后沒(méi)幾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qiáng)加給他的女人。 據(jù)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此次赴日同行者共四人,另兩人為邵明之和張午樓。據(jù)周作人回憶魯迅其時(shí)的考慮是這樣的:“經(jīng)過(guò)兩年的學(xué)習(xí),魯迅已經(jīng)學(xué)完醫(yī)學(xué)校的前期的功課,因思想改變,從救濟(jì)病苦的醫(yī)術(shù),改而為從事改造思想的文藝運(yùn)動(dòng)了。所以,決心于醫(yī)校退學(xué)之后回家一轉(zhuǎn),解決多么延擱的結(jié)婚問(wèn)題,再行卷土重來(lái),作《新生》的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wú)法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的。沒(méi)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過(guò)來(lái)的。不知她是一動(dòng)不動(dòng)呆坐在新房里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guò)來(lái)人現(xiàn)身說(shuō)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zhuǎn)意的那24小時(shí)。
朱安那一聲凄慘的呼號(hào),實(shí)在動(dòng)人憐憫。常言“一雙小腳三升淚”,她卻為此成了一件無(wú)人珍惜的“棄物”!這本書定能成為常銷的暢銷書。書此為券。
—— 楊絳 (2010年4月13日)
魯迅研究已經(jīng)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卻一直冷落了朱安,真是不應(yīng)該的。回避了她,對(duì)魯迅也就不可能有一個(gè)完整的了解了。
—— 朱正
我有一個(gè)看上去有點(diǎn)兒過(guò)于大膽的想法:魯迅生命中的兩個(gè)女人,朱安與許廣平,若論誰(shuí)對(duì)魯迅的影響更大,不是許廣平而是朱安。正是朱安,使魯迅體味了封建禮教對(duì)人性的壓抑和命運(yùn)的荒誕,斷了他的后路,刺激他與傳統(tǒng)徹底決裂,一往無(wú)前、義無(wú)反顧地反抗封建禮教,與命運(yùn)進(jìn)行“絕望的抗?fàn)?rdquo;。
——陳丹青
沒(méi)有死刑判決與長(zhǎng)期苦役,無(wú)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沒(méi)有父親的專橫狂暴,無(wú)以成就卡夫卡,魯迅對(duì)朱安的冷漠,對(duì)他自己無(wú)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這在他那里同樣升華為創(chuàng)作熱情。——止庵(作家)
有些食物,本來(lái)就不太愛吃,放在那里,漸漸有點(diǎn)變質(zhì),但因?yàn)槭强粗氐娜说酿佡?zèng),又舍不得扔掉,干脆等壞到不可收拾,心安理得地拋棄,這期間,總還會(huì)看到它們,看見它們平靜地等待被自己拋棄。有點(diǎn)像魯迅待朱安。
-------閆紅
如果說(shuō)朱安的悲劇表現(xiàn)為依附性人格,中國(guó)的男人們就不依附嗎?我們有幾個(gè)男人真的擺脫了形形色色或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的人身依附?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中國(guó)不僅需要女權(quán)運(yùn)動(dòng),也需要男權(quán)運(yùn)動(dòng)。女人的敵人不是男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敵人是枷鎖——各式各樣的枷鎖。
——蕭三匝
在近現(xiàn)代史上,胡適和魯迅互為鏡像,因?yàn)橄嗤慕?jīng)歷因?yàn)椴煌倪^(guò)程而呈現(xiàn)出不同的姿態(tài),而魯迅和朱安,也互為鏡像,從魯迅的人生可以映照朱安,從朱安的人生,也可以映照魯迅。讀完《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忍不住感嘆:這一雙可憐人。
——陳遠(yuǎn)
為朱安立傳,當(dāng)然不能從中品嘗什么心靈雞湯,獲取什么勵(lì)志教誨,但正是朱安這位個(gè)性色彩鮮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無(wú)愛情結(jié)婚的惡結(jié)果”(魯迅:《隨感錄 四十》),是研究中國(guó)婦女史、倫理史的一個(gè)活標(biāo)本,對(duì)于研究魯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義。
——陳漱渝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wei yi的朱安傳記,作者盡她所能,寫出了一個(gè)真實(shí)的朱安,一個(gè)讓人無(wú)法再漠視的朱安。文筆旖旎、搖曳,文字美麗到讓人不忍釋卷,而情感的細(xì)膩、婉約,達(dá)到了一般女性都罕見的深度。感激她寫出了這么好的傳記,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了有關(guān)魯迅的一些隱秘的故事,了解了為人的不易,了解了人生的艱難。同時(shí)感受到了魯迅的偉大,他的隱忍,他的絕望,他的堅(jiān)持,他的為他人著想的偉大精神,和他的精神的傳承。
——楊光祖(西北師范大學(xué)教授,青年文學(xué)評(píng)論家)
朱安把自己看成是魯迅的遺物,祈求能夠得到一些起碼的關(guān)注,不至于晚景凄涼;魯迅把朱安看成一件禮物,他只有供養(yǎng)的義務(wù)。
讀了一段,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時(shí)代賦予我的東西,我無(wú)法擺脫,生活不易,愛情更不易,在那個(gè)思想沖擊的年代,讀讀朱安吧。放下心情,本書很值得一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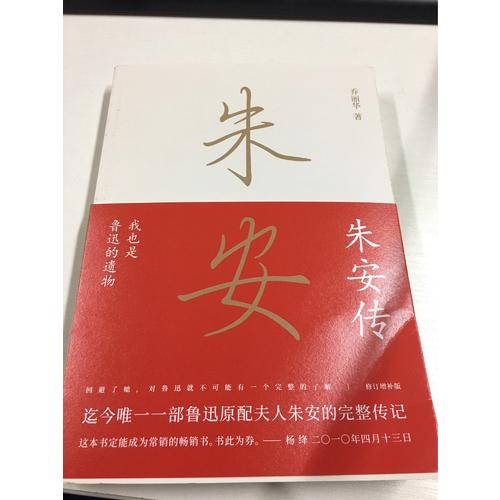 關(guān)于魯迅的新婚,后人有許多回憶和猜測(cè),卻鮮有人關(guān)心朱安是怎么熬過(guò)來(lái)的。朱安在默默地做著一切,祈求丈夫終有一天可以給她以溫暖,卻從未如愿。
關(guān)于魯迅的新婚,后人有許多回憶和猜測(cè),卻鮮有人關(guān)心朱安是怎么熬過(guò)來(lái)的。朱安在默默地做著一切,祈求丈夫終有一天可以給她以溫暖,卻從未如愿。
時(shí)代的縮影,那個(gè)年代,知識(shí)分子領(lǐng)導(dǎo)人,軍官都會(huì)拋棄糟糠之妻,再找一個(gè)讀過(guò)書的女青年,魯迅也不能幸免!好在魯迅一直敬重朱安,魯老太太也視朱安如己出!也算那個(gè)時(shí)代中的幸運(yùn)!
以前只聽說(shuō)過(guò)許廣平不是魯迅先生的原配,但是不知道原來(lái)新時(shí)代的大先生竟有個(gè)舊時(shí)代的原配小腳夫人,很是震撼,書買回來(lái)看了兩遍,真是本好書,怪不得楊絳先生推薦呢,只有了解了朱安,許廣平,周作人,才能完整地理解魯迅的文章。
大部分人都只知道許廣平,而忘記了朱安。這本書從另外一個(gè)角度,補(bǔ)全了魯迅先生的另外一段生活經(jīng)歷。
朱安在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默默無(wú)聞,之前只知道她是魯迅先生的發(fā)妻,看了書之后,才知道朱安也是個(gè)可憐人
看到這個(gè)書的標(biāo)題就被吸引了,作為魯迅的原配,她的人生令人非常同情,可以肯定的是,她是一個(gè)很不錯(cuò)的兒媳。
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一本朱安傳記,透過(guò)朱安看魯迅,更清楚的了解一些有關(guān)魯迅隱秘的故事,感受魯迅的偉大
書里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duì)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wú)聲之聲。
魯迅忍受了漫長(zhǎng)的煎熬,最終還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許廣平;而朱安,卻真的“做一世的犧牲”,陪伴她的,只有年邁的魯老太太
這本書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duì)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wú)聲之聲。
朱安是被魯迅的身影遮蔽的女人,本書對(duì)她的一生做了詳盡的描述,她的不幸不僅僅是她個(gè)人的不幸,也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悲哀。
知道魯迅 許廣平 但對(duì)原配朱安知之甚少 希望能通過(guò)此書了解一下那個(gè)時(shí)代的面貌,通過(guò)朱安,更全面了解一下魯迅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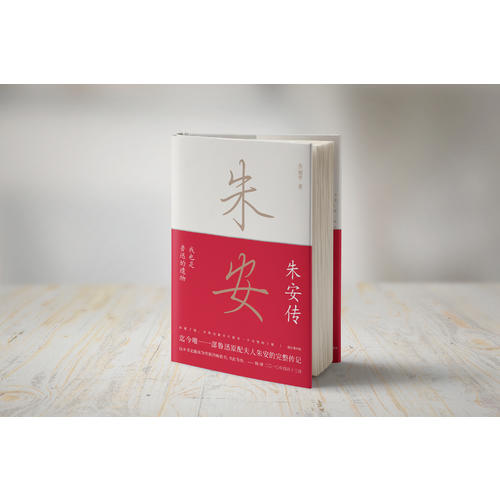 自從知道魯迅就自然知道他的愛人是許廣平,但對(duì)于朱安確很陌生,了解到朱安的一生后對(duì)魯迅的一家也有了更詳盡的了解
自從知道魯迅就自然知道他的愛人是許廣平,但對(duì)于朱安確很陌生,了解到朱安的一生后對(duì)魯迅的一家也有了更詳盡的了解
魯迅多次對(duì)友人說(shuō):“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fù)有一種贍養(yǎng)的義務(w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舊時(shí)代的炮灰,上輩給你定了,魯迅反抗不了。離婚追求自己的心愛才是正事,時(shí)代的犧牲品,你說(shuō)兩人沒(méi)共同語(yǔ)言怎么過(guò)日子,真是苦得一逼
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gè)目不識(shí)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yǔ)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尋味。她凄風(fēng)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回味。
舊時(shí)社會(huì)對(duì)于女性的冷漠,莫過(guò)于毀了她們作為一個(gè)人的存在感,沒(méi)有自己的思想,沒(méi)有自己的主見,有喜怒哀樂(lè),卻也不表達(dá)出來(lái),仿佛一尊木偶
上學(xué)的時(shí)候特別喜歡魯迅的文學(xué)作品,覺(jué)著他這個(gè)人特偉大。口誅筆伐、以筆為槍,讀了本書以后讓我對(duì)魯迅的認(rèn)識(shí)更立體化了,也更深的了解那個(gè)時(shí)代
作者通過(guò)走訪朱氏后人,實(shí)地勘查采訪,鉤沉相關(guān)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運(yùn)用報(bào)刊資料、回憶錄、文物、生活等資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
朱安,使魯迅體味了封建禮教對(duì)人性的壓抑和命運(yùn)的荒誕,斷了他的后路,刺激他與傳統(tǒng)徹底決裂,一往無(wú)前、義無(wú)反顧地反抗封建禮教,與命運(yùn)進(jìn)行“絕望的抗?fàn)帯薄?
這本書描述了魯迅原配夫人朱安不為人知的69個(gè)春秋,魯迅研究已經(jīng)有八十多年歷史了,卻回避了她,對(duì)魯迅也就不可能有一個(gè)完整的了解了。這本書本書值得擁有
朱安是周樹人的原配夫人,可是魯迅后來(lái)的發(fā)達(dá),讓他忘記了過(guò)往,風(fēng)華年代魯迅的萬(wàn)丈光芒讓朱安無(wú)所適從,只能在寂靜的角落里靜靜守候,孤獨(dú)終老,朱安傳便是這一切
如果朱安不是魯迅的夫人,也許不會(huì)那么孤單。如果朱安不是魯迅的夫人,在抗戰(zhàn)期間也許不會(huì)得到那么多人的關(guān)照。不管哪種,在那樣的時(shí)代,那樣的環(huán)境中,命運(yùn)都不會(huì)太好吧。
喜歡魯迅的書,從而想了解他的發(fā)妻是一個(gè)怎樣的女人,看了此書,也了解了一個(gè)時(shí)代女人的悲哀,此書寫的不僅僅是朱安,也是那一個(gè)時(shí)代女人的生活背景,建議大家可以選購(gòu)了解下
沒(méi)有半點(diǎn)過(guò)錯(cuò),卻承受了一生的傷害,無(wú)所謂怪誰(shuí),到頭來(lái)頂著夫妻之名,卻沒(méi)有夫妻之實(shí),也無(wú)人知曉。你口中的大先生,死都無(wú)法同穴,感慨這一生如何走下去,一個(gè)盡人皆知,一個(gè)也應(yīng)該被人知道。
魯迅與朱安的婚姻近代知識(shí)分子婚姻的縮影,而朱安是奉父母之命與知識(shí)分子結(jié)合的傳統(tǒng)女性的悲慘代表人物,在魯迅生前,名為正室卻又不是正室,在魯迅身后,能為證明自己也只是“我也是魯迅的遺物”的吶喊。
朋友推薦看的,看到一半的時(shí)候,感覺(jué)哀其不幸,怒其不爭(zhēng)。看完后覺(jué)得無(wú)論作為一個(gè)偉大的女人,還是一個(gè)卑微的女人,我們都要像蝸牛一樣努力的向上向前爬,不輕易抱怨,不輕易放棄,學(xué)會(huì)從容,方能安穩(wěn)的度過(guò)一生
作者喬麗華通過(guò)走訪朱氏后人,實(shí)地勘查采訪,鉤沉相關(guān)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運(yùn)用報(bào)刊資料、回憶錄、文物、生活等資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duì)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wú)聲之聲。
上學(xué)的時(shí)候語(yǔ)文課文好多魯迅先生的文章,但是對(duì)本人只有些許的了解。但是從他的夫人的口中才真正了解魯迅是什么樣的一個(gè)人,值得買,值得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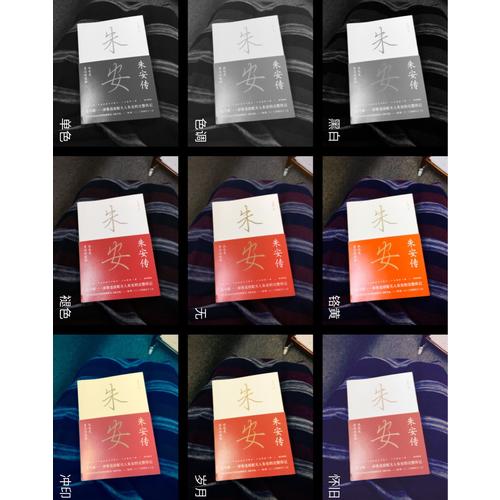 今年讀過(guò)的書里給我震動(dòng)最大的,朱安雖然聽說(shuō)過(guò),一直都不太了解,不覺(jué)得會(huì)有什么故事,但這本書徹底改變了我這種想法。因?yàn)橹彀玻斞覆懦蔀轸斞福彀驳囊簧侨绱说膲阂趾捅啵屓诵耐矗?
今年讀過(guò)的書里給我震動(dòng)最大的,朱安雖然聽說(shuō)過(guò),一直都不太了解,不覺(jué)得會(huì)有什么故事,但這本書徹底改變了我這種想法。因?yàn)橹彀玻斞覆懦蔀轸斞福彀驳囊簧侨绱说膲阂趾捅啵屓诵耐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