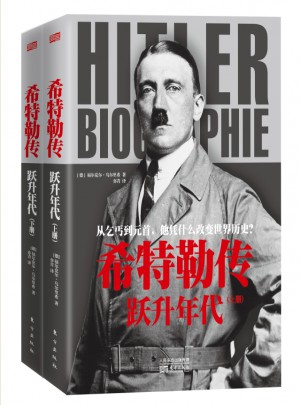
希特勒傳:躍升年代
- 所屬分類:圖書 >傳記>領(lǐng)袖首腦
- 作者:(德)[福爾克爾·烏爾里希] 著,[亦青] 譯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無
- 國(guó)際刊號(hào):9787506087247
-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 出版時(shí)間:2016-05
- 印刷時(shí)間:2016-05-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yè)數(shù):--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膠訂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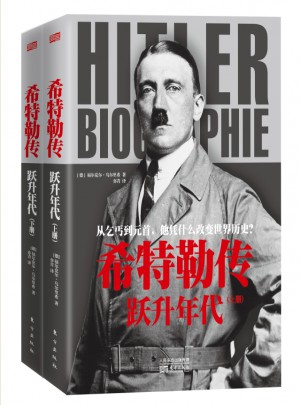
希特勒究竟是怎樣的一個(gè)人?身為歷史學(xué)家的本書作者福爾克爾 烏爾里希,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在書中細(xì)細(xì)探究德國(guó)第三帝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希特勒。這位眾所周知的獨(dú)裁者在撇下“元首”的頭銜之后,作為一個(gè)“人”,會(huì)呈現(xiàn)出何種樣貌?他有何令人喜歡或厭惡的特質(zhì)?有何天賦或才能?他的心理情結(jié)與兇殘的殺人欲望又是如何?
本書推翻了關(guān)于希特勒本人所有錯(cuò)誤的陳詞濫調(diào),從希特勒的人格特征、私人社交圈以及他與女性的關(guān)系、他的統(tǒng)治方式和理念等各個(gè)側(cè)面著手,完整而又多層次地刻畫出了一個(gè)獨(dú)特的歷史人物形象。書中大量引用與希特勒同時(shí)代人的證詞,既包括他的崇拜者,也有反對(duì)派,首度披露大量的迄今為止從未被發(fā)現(xiàn)的全新歷史文獻(xiàn)。
在作者筆下,希特勒不再是一個(gè)空洞的恐怖符號(hào)。當(dāng)一個(gè)有“魅力”的希特勒活生生地站在我們面前時(shí),我們不會(huì)忘記他犯下的滔天罪行,相反,我們的心中會(huì)生出警惕和恐懼。本書主要聚焦于希特勒從崛起至1939年獨(dú)攬大權(quán)的時(shí)期,是本世紀(jì)值得注目的希特勒傳記。
2004年9月,奧利弗•西斯貝格(Oliver Hirschbiegel)執(zhí)導(dǎo)的電影《帝國(guó)的毀滅》(Der Untergang)在德國(guó)上映,這部獲得了奧斯卡獎(jiǎng)提名的電影在全球范圍內(nèi)引起了巨大的爭(zhēng)議。影片以冷靜客觀的態(tài)度描述了希特勒藏身于地堡的后12天,希特勒被還原成一個(gè)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感情,有喜怒哀樂,他也會(huì)關(guān)心下屬,面對(duì)婦女、兒童時(shí)時(shí)流露出脈脈溫情。電影上映之后,德國(guó)媒體提出了一個(gè)問題“我們是否可以把希特勒作為一個(gè)人來刻畫?”
對(duì)此,《希特勒傳:躍升年代》的作者——德國(guó)著名傳記作家福爾克爾 烏爾里希給出了斬釘截鐵的答案:“是的,我們可以這樣做!而且我們也必須這樣做!” 本書作為文學(xué)界的《帝國(guó)的毀滅》,洋洋上百萬(wàn)字的巨著遠(yuǎn)比一部電影講述希勒特更加、更加深刻。
希特勒是一個(gè)有著強(qiáng)烈個(gè)性和多面性的人,他絕非以往人們所說“只會(huì)煽動(dòng)民眾的低層次情緒”的“眼界狹隘、能力有限的庸才”,他不僅有宣傳的口才,更有針對(duì)不同對(duì)象扮演不同角色的表演才能,希特勒是個(gè)有魅力的人。作者破除了長(zhǎng)久以來彌散于學(xué)術(shù)界和文藝界的“惡魔神話”,所以他筆下的形象更顯得晦澀復(fù)雜,更能引起人們沉重的反思。正如托馬斯•曼在《兄弟希特勒》中所言:“希特勒的出現(xiàn)并非偶然,他是一種真正正常的德國(guó)現(xiàn)象!”
對(duì)希特勒進(jìn)行人性化的描寫并不意味著為納粹脫罪,當(dāng)一個(gè)有“魅力”的希特勒活生生地站在我們面前時(shí),我們不會(huì)忘記他犯下的滔天罪行,相反,我們的心中生出警惕和恐懼,因?yàn)閻耗Р⒎翘焐模瑦耗钣谌巳褐校腔灿诿總€(gè)人的心頭,只要有合適的氣候和土壤,惡魔播撒的種子就有可能生根發(fā)芽。
福爾克爾 烏爾里希(Volker Ullrich)
1943年出生,著名傳記作家、歷史學(xué)家、專欄作家、電視媒體人。
主修歷史、文學(xué)與哲學(xué),目前居于漢堡。《時(shí)代》雜志旗下著名作家,《時(shí)代雜志歷史篇》合作出版人,1990年至2009年間曾擔(dān)任《漢堡周刊》的《政治書》主編,并出版過多部關(guān)于19世紀(jì)和20世紀(jì)歷史的專著,眾多成就使他于2008年榮獲德國(guó)耶拿大學(xué)榮譽(yù)博士頭銜。曾經(jīng)因在新聞出版業(yè)做出的杰出貢獻(xiàn)獲得德國(guó)弗雷德里希•克爾大獎(jiǎng)。《希特勒傳:躍升年代》是作者數(shù)十年心血之作,被學(xué)術(shù)界評(píng)價(jià)為本世紀(jì)最、最真實(shí)、最值得注目的希特勒傳記。
前言
1. 少年希特勒
2. 維也納歲月
3. 戰(zhàn)爭(zhēng)中的重要經(jīng)歷
4. 投身政治
5. 慕尼黑之王
6. 政變與審判
7. 蘭茲伯格監(jiān)獄——《我的奮斗》
8. 蟄伏中的“元首”
9. 德國(guó)政壇的流星
10.希特勒和女人們
11.權(quán)力撲克游戲
12.1933年1月,決定命運(yùn)的一個(gè)月
13.作為一個(gè)人的希特勒
14.建立獨(dú)裁政權(quán)
15.修訂凡爾賽條約
16.元首崇拜和民眾
17.統(tǒng)治方式和宏偉建筑
18.貝格霍夫社交圈
19.反教會(huì)的斗爭(zhēng)
20.“猶太政策”的極端化
21.通向戰(zhàn)爭(zhēng)的道路
致謝
作為一個(gè)人的希特勒
這個(gè)于1933年1月30日入主他所崇拜的帝國(guó)締造者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住過的帝國(guó)總理府的43歲男人究竟是個(gè)什么樣的人?這是一個(gè)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yàn)橄L乩盏墓_形象后面還隱藏著難以捉摸的個(gè)人形象。即使對(duì)于他最親近的親信來說,希特勒在某些方面也像個(gè)謎團(tuán)。“看不透的斯芬克斯式的人格。”希特勒的首席新聞發(fā)言人奧托•迪特里希在回憶錄中寫道。多年來有機(jī)會(huì)近距離觀察黨主席的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也承認(rèn),他“從來沒找到打開這個(gè)人靈魂深處的鑰匙”,“他真實(shí)的想法和感受對(duì)我來說始終像一本被封印的天書。”1933年后不久成為“元首”最賞識(shí)的建筑家的阿爾伯特•施佩爾在1945年6月/7月陶努斯山克蘭斯貝格城堡的及時(shí)次審訊錄供時(shí)就說過:“對(duì)他而言希特勒本人始終是個(gè)充滿矛盾和鮮明對(duì)立的謎”。“我們似乎永遠(yuǎn)無法理解他身上的某些東西”,前法國(guó)大使安德烈•弗蘭索瓦•龐塞特1943年在柏林評(píng)論。國(guó)務(wù)秘書奧托•邁斯納曾經(jīng)忠心耿耿地為希特勒工作過,就像他也曾為前任總統(tǒng)艾伯特和興登堡忠心耿耿工作過一樣,他在1953年寫的回憶錄中認(rèn)為:“對(duì)這個(gè)奇人的本性的判斷……將會(huì)永遠(yuǎn)存在爭(zhēng)議。即使是他多年的老相識(shí)或者眼見他成長(zhǎng)變化的人也很難對(duì)他下一個(gè)確切的評(píng)語(yǔ),因?yàn)樗且粋€(gè)自我封閉的孤僻者,只有少數(shù)人——也只是偶爾地——能窺見他的內(nèi)心。”
如果人們及時(shí)次近距離觀察希特勒,他們會(huì)發(fā)現(xiàn)他與印象中的截然不同。工業(yè)家君特•夸爾特(Günther Quandt)在1931年12月與希特勒會(huì)面時(shí)認(rèn)為他“僅是平庸之輩”,英國(guó)記者塞夫頓•德爾默認(rèn)為他是個(gè)“很普通的人物”,看上去像個(gè)當(dāng)過兵的商務(wù)代表。美國(guó)女記者多蘿西•湯普森則像我們知道的認(rèn)為希特勒是個(gè)“典型的小人物”。美國(guó)環(huán)球新聞社的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在1934年9月的紐倫堡黨代會(huì)上及時(shí)次見到希特勒時(shí)感到失望:“他的臉并無特殊之處——我還以為他看上去會(huì)更堅(jiān)強(qiáng)一些呢——我始終無法理解,他在歇斯底里的群眾身上無可置疑地喚醒了怎樣一種隱藏的力量,讓他受到如此瘋狂的追捧。”
所有與希特勒接觸過的同時(shí)代的人都說他五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1919年夏季,當(dāng)歷史學(xué)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在慕尼黑大學(xué)及時(shí)次看到年輕的希特勒時(shí),他首先注意到了“那雙閃爍著瘋狂而冰冷的光芒的淺藍(lán)色大眼睛”。1929年7月被維妮弗蕾德•瓦格納聘為助理和家庭女教師的莉澤洛特•施密特(Lieselotte Schmidt)像她的拜羅伊特女主人一樣著迷地崇拜著希特勒,她沒覺察出目光中的冰冷,反而看出善良和熱忱:“只需看一眼那雙美麗絕倫的紫羅蘭色眸子,就能感受到他整個(gè)人的情感和心靈。”奧托•瓦格納,1929年秋季開始為希特勒服務(wù),1946年被英國(guó)人監(jiān)禁期間還在審訊記錄中承認(rèn)他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回憶說:“從一開始那雙眼睛就牢牢吸引住我。清澈的大眼睛平靜而充滿自信地注視著我。但那種眼神似乎不是來自于眼球,而是來自于某種更加內(nèi)在的東西,我感覺就像來自于永恒。人們無法解讀其中的含義,可它在訴說,它想訴說。”1933年起當(dāng)上希特勒女秘書的克里斯塔•施羅德的描述更加理智一些:“我覺得希特勒的眼睛富有表現(xiàn)力,多數(shù)時(shí)間透出饒有興趣的研究式的目光,在說話時(shí)他的眼神變得越來越生動(dòng)。”“奇特的美麗的眼睛,”作家格爾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描述1933年11月在音樂廳舉辦的帝國(guó)文化協(xié)會(huì)開幕式上他初次見到希特勒的印象。
人們對(duì)希特勒目光的個(gè)人感受——冰冷的還是善意的,深不可測(cè)的還是饒有趣味、友好的——既取決于當(dāng)時(shí)的情境,也取決于他們對(duì)對(duì)方的看法。“崇拜者贊美目光中的力量,”希特勒的反對(duì)者康拉德•海登說,“而在冷靜的觀察者看來,那種迫視的目光顯得貪婪而刺人,毫無優(yōu)雅可言,引發(fā)的反感多于吸引力。”但即使是用批評(píng)眼光看待希特勒的來訪者——比如1933年漢夫施丹格爾在皇宮旅館向希特勒引見的美國(guó)大使威廉•愛德華•多德(William Edward Dodd)的女兒——也同樣贊美他的眼睛“引人注目,令人難忘”:“它們看上去是淺藍(lán)色的,眼神專注,令人移不開眼,似乎能產(chǎn)生催眠的魔力。”
除了眼睛之外希特勒的手最引人注目,它們“伴隨著動(dòng)作極富表現(xiàn)力,堪與眼睛媲美”,年邁的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1923年9月希特勒在拜羅伊特及時(shí)次造訪他時(shí)充滿仰慕地說。“一雙神經(jīng)質(zhì)的手關(guān)節(jié)柔軟,幾乎像女人的手。”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注意到。當(dāng)哲學(xué)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1933年5月表達(dá)出憂慮“一個(gè)沒受過教育的人能否治理國(guó)家”時(shí),他在弗萊堡的同事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回答說:“受沒受過教育無所謂……你看看那雙美麗的手!”很多同時(shí)代人抱著和這位哲學(xué)家相似的傾慕,例如帝國(guó)廣播負(fù)責(zé)人歐根•哈達(dá)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1936年12月給《新文藝》雜志的通訊稿中將希特勒“無比柔軟的手”贊美成“藝術(shù)家和偉大設(shè)計(jì)師的工具”。裝甲部隊(duì)的將軍路德維克•克呂維爾(Ludwig Crüwell)1942年10月在英軍監(jiān)獄中還表示過:“他的手非常顯眼——太美的一雙手……他的手像個(gè)藝術(shù)家。我總是看他的手。”
希特勒不僅是個(gè)天才演說家,還是個(gè)具有非凡才華的演員。“有一次他在不經(jīng)意之間自詡為歐洲最偉大的演員。”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回憶說。當(dāng)然這也是一種過分的自我美化,他坐在獨(dú)裁者位子上的時(shí)間越長(zhǎng),自我美化的趨勢(shì)就越明顯。但是他的確把戴著各種面具登場(chǎng)和輪番扮演各種角色的能力演繹成爐火純青的藝術(shù)技巧。“他是個(gè)親吻女士纖纖玉手的可愛的聊天對(duì)象,一個(gè)給孩子們分發(fā)巧克力的和藹的大叔,一個(gè)握住工人農(nóng)民長(zhǎng)滿老繭的手的正派的政治家。”在貝希施坦因和布魯克曼的沙龍里或者在席拉赫的魏瑪宅邸中喝下午茶時(shí),他穿西服打領(lǐng)帶,遵照社會(huì)禮儀扮演著好公民的角色;在國(guó)社黨黨代會(huì)上,他穿著褐色襯衫,看上去像個(gè)蔑視資產(chǎn)階級(jí)上流階層的十足的斗士。
他在演講時(shí)也游刃有余地轉(zhuǎn)換著各種角色以滿足各種場(chǎng)合的需要。“他在國(guó)會(huì)面前像個(gè)睿智的政治家;在實(shí)業(yè)家的圈子里像個(gè)思想中庸的人;在婦女們面前像個(gè)喜歡孩子的善良父親;面對(duì)大眾他像一座爆發(fā)的火山;在黨內(nèi)同志們的面前,他像個(gè)最忠誠(chéng)最勇敢的人,他號(hào)召大家做出犧牲并且決意自我犧牲。”法國(guó)大使安德烈•弗蘭索瓦•龐塞特(André François-Poncet)有幸在1935年紐倫堡的黨代會(huì)上看到希特勒登臺(tái)時(shí)不同的表現(xiàn),他驚異地發(fā)現(xiàn)希特勒對(duì)觀眾的感情具有“令人驚嘆的直覺”,“他能為每個(gè)聽眾找出一番說辭并以此贏得他需要的掌聲,他使出渾身解數(shù),輪番用辛辣、激情、熟稔和傲慢的腔調(diào)說話。”1938年11月接替弗蘭索瓦•龐塞特就任法國(guó)大使的羅伯特•庫(kù)隆德爾(Robert Coulondre)在貝格霍夫向希特勒遞交國(guó)書時(shí),他也愕然地發(fā)現(xiàn):“我還以為將在城堡中看見一位執(zhí)掌雷霆的朱庇特,沒想到卻在鄉(xiāng)村別墅里遇到一個(gè)平凡溫柔的也許還捎帶幾分靦腆的男人。我在收音機(jī)邊聽到過這位元首充滿威脅和挑戰(zhàn)意味的嘶啞喊聲,而我現(xiàn)在認(rèn)識(shí)的希特勒卻有著溫暖、平靜、友好和充滿理解力的聲音。哪一個(gè)才是真實(shí)的希特勒?也許二者都是真實(shí)的?”
希特勒該為一些可怕至極的罪行負(fù)起責(zé)任,這一點(diǎn)是世人公認(rèn)的,但歷史學(xué)家福爾克爾 烏爾里希在這本全新的《希特勒傳:躍升年代》中,探討的不只是這位獨(dú)裁者身為反猶太主義者的一面,同時(shí)也包含了他作為男性的那一面。
——《明鏡》雜志英文版
福爾克爾 烏爾里希敘述的是他在檔案資料中的新發(fā)現(xiàn)。
——德國(guó)《時(shí)代》雜志
希特勒的私生活始終是個(gè)謎團(tuán),他的一生不是用“過”的,而是用“演”的,這本新書披露了這位種族屠殺兇手身為一個(gè)毫無特色的男人的種種面相。
——德國(guó)《世界》日?qǐng)?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