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近代福州家族史為主線,講述16個影響福州乃至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家族,包括福州歷史名宦、名商,和著名手藝人的家族故事。本書以文字 圖片的方式,展示人物的離合、世事的變幻、家族血脈的流轉相承,終不過是為了解答我們從何處來,幫助我們接納自己。
鄭芳,生于江西九江,從事媒體工作15年,參與創辦本土城市雜志《homeland家園》,曾任該雜志副主編,主持編輯工作。兩年前辭職,現為獨立撰稿人、策劃人,從事城市家族史及個人史的采訪寫作。
自序
壹 林則徐的歷史爭議與家族記憶
林則徐的個人成長史
林則徐的朋友圈
福州坊巷間的林則徐后裔們
貳 沈葆楨家族:一個人文官宦世家的范本
沈葆楨:晚清“經世致用”的實踐者
宮巷內外,尋訪沈葆楨家族血脈遺產
沈葆楨與林則徐兩大家族的關系
叁 末代帝師陳寶琛家族的五代傳奇
“斬皇子”的陳若霖
辭官孝子陳承裘
帝師陳寶琛
“灣區中文電視之父”陳立鷗
地下黨員陳矩孫
肆 薩鎮冰:薩氏家族的古怪族親
族叔養大的孩子
瘦小勤奮的留學生
吝嗇的“薩菩薩”
管旗兵的豪爽岳父
孤獨的中年鰥夫
伍 福州北門龔家的百年變遷
龔易圖時代和三山舊館的興起
龔易圖的第二、三代和三山舊館的寧靜時光
龔易圖的第四、五代和三山舊館的破落消失
陸 福州較大工商家族“電光劉”的百年傳奇
資本奠基者劉齊銜
原始積累掌控者劉學恂
“電光劉”的發展與鼎盛
“電光劉”事業的頹敗
電光事業之外的劉家名人
柒 百年回春和褪色的吳氏家族
回春的東家
鬧劇牽出的易主儀式
意外庫存引出的擴張
神奇的周公百歲酒
具開拓精神的二代掌門人
尷尬的借貸關系
遭遇戰亂期貨幣貶值
捌 三代商會會長家的銀行家夢想
200個銅錢開始的發家史
羅氏金融集團的創立
金融集團之外的羅家事業
家業鼎盛的羅勉侯時期
私人錢莊的銀行家夢想
龐大家業終結于戰亂
玖 百年前福州首富家族的兩位名商
張秋舫:發跡于京果貿易
張順凡:續寫張家傳奇的年輕人
拾 福州絲線專賣尤恒盛家族盛衰史
尤恒盛的資本積累
二代房東的人事變化
臨危掌舵的尤家五房
五房系制造的全盛期
尤家后代的享樂主義生活
逐漸衰弱的尤家生意
終結于第四代的尤恒盛
拾壹 70年前飛機往返福廈的洪氏家族
從兼營航運到專營茶葉
洪家生意的幾任接班人
巨商后人的貴族生活
戰亂中洪家茶的頹敗
拾貳 老字號“美且有”落幕前的回憶
清朝舉人的轉型
美且有的股權轉讓
精明的陳家四公子
美且有的鼎盛期
戰亂時期的承襲
半個世紀的風云起伏
拾叁 聚春園發展史上的兩部家族往事
鄭春發:發跡于源春館的孤兒
鄧家父子:聚春園史上的兩位重要股東
拾肆 六個人的沈紹安脫胎漆器家族史
沈紹安:落魄家族、厭學少年、漆匠
沈作霖:制訂沈家家規
沈正鎬:秘密工場如小姐閨房
沈幼蘭:另起爐灶
沈忠英:花木蘭式女藝人
沈德椿:短暫的德記商業史
拾伍 一間叫“米家船”的裱褙店
傳家業
祖師爺
“人在店在”
新牌匾
拾陸 福州角梳盛世里的李厚記制造史
兼職商人的李盛記
第二代的商業分工
外銷為李發記帶來鼎盛期
戰火摧殘的角梳行業
隱退的角梳家族史
自序
這本書稿的出版推遲了11年。除去忙碌,更主要的原因,其實是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推動這件事——在快節奏的生活里,常常被淹沒在趕路的慌張與焦慮中,來不及停留,更舍不得花時間往回看,去關心一段過去的、與己無關的歷史。
12年前,我在福州一家都市報做記者,曾開設過一檔專欄,專欄的定位是挖掘福州世家的家族故事。專欄是時任報社總編輯李烽先生規劃的,當時被稱為報業青年才俊的他剛三十出頭,他說一個人年過三十,會開始關心歷史,需要知道自己從哪里來。那年我26歲,對這樣的說法還沒有辦法感同身受。相反,內心有種強烈的不踏實感。在我的個人教育史中,歷史從來就是一個障礙,高中花費最多時間背歷史,但歷史考試的好成績也僅僅是過及格線;大學學分低的是中國新聞史和世界新聞史。我不知道歷史書上的描述和我的生活有什么關系,自然也無法理解家族史的意義。
26歲,經歷過的大事無非輾轉過幾家媒體,采訪過一些常常出現在公眾視線下的名人,親歷過一張充滿朝氣的報紙因為經營問題戛然而止。當時,這個專欄于我的意義,只是換個角度扮演記者的角色,最關心的事是下一個家族線索在哪里、怎么提問會顯得更專業、怎樣描述一個家族的故事會更好看……一個家族怎么來,怎么去,和我的生活其實沒有關系。
在對新工作的新鮮與忐忑中,我開始了為期一年半的家族史訪問。采訪對象多半是上了年紀的老人,我和他們聊曾經居住的老房子,老房子里的故事,聊個人史,聊家族史,聊怎么看上一代和下一代,聊人生的遺憾,聊余生的愿望……當幾十上百個人的人生陸陸續續呈現在面前時,我才開始想一個人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一個人和一個家族又有什么關系,人生命中最難割舍的是什么。
人生的際遇常常是這么奇妙,你很難預測哪件事情會是一顆種子,在你未來的生活里生根發芽。離開都市報,我去了一家正在籌備的城市生活雜志。在快餐式的媒體環境里,這樣一份雜志讓生活的太多問題有了合理存在的理由。雜志社的工作是我最長的一段工作經歷,九年時間,人生的很多問題成為雜志的選題,我在形形色色采訪對象的生活里找答案——怎么生活。
只是,看過一百個理想生活的故事,并不代表你的生活也能過成那樣。問過一千個觸動人心的問題,不代表你真的可以改善你的生活。人生的太多選擇需要有足夠的沉淀才會在剛剛好的時候發酵。2015年,在離開雜志社半年后,有了這個重訪福州大家族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產生,更直接的原因是,臨近中年,十年前開始思考的問題正在悄無聲息地進入我的生活,成為我自己的人生課題。
這場跨度12年的采訪,于我是一味解藥。人生跌跌撞撞走過第三個本命年,想放下一個壓抑緊繃又好像欲罷不能的狀態,學會了解自己,學會放松,從容過后面的生活。我從哪兒來?要去哪里?這些問題,讓最親近的人及時次成為我最想了解的人。只是,習慣了的溝通方式、表達方式,常常讓了解變得無從開始。此時,重訪計劃像一把鑰匙。
99歲的龔端徽床頭放著一本打印文稿《論古文之不宜廢》,那是林紓在1917年新文化運動中捍衛古文的一篇文章,老人每天睡前會看上幾行或幾頁,琢磨文章的意思。龔端徽是林紓的兒媳,丈夫林次東是林紓的小兒子,解放前去了臺灣。1949年后,海峽分隔了她的婚姻,她開始了獨自養大三個孩子的人生。在之后的各種運動與災難中,保護和養育三個孩子并非易事,其中艱辛,老人輕描淡寫。老人的相冊里珍藏著丈夫從臺灣寄來的照片,包括新家庭的全家福,說起在臺灣再婚的丈夫,情緒平緩得像在敘述別人的故事。
龔端徽的堂弟龔鈞智97歲,清朝名宦、著名藏書家、園林宅院主人龔易圖的曾孫。采訪結束時,龔老送我和攝影師他自費編纂出版的郵票專輯。老人戴上眼鏡、端坐桌前,在扉頁上用行云流水的小楷寫下贈言,在字末蓋上印章,再用紙巾小心拭去多余印泥,舉手投足間的從容、淡泊,以及對生活的儀式感,讓人心生敬意。
年過七十的劉岳是解放前福州較大工商家族“電光劉”的后裔。12年前,我的“電光劉”及時印象開始于劉家祖墓——劉岳帶我們去福州森林公園后山掃墓。每月至少親自去一次墓地清掃垃圾,已經成為他的一個堅持了20年的生活習慣。我問他什么時候開始關注自己的家族史,他說中年開始,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他搜集了大量關于劉家的史料,以及留有家族痕跡的物件,但并不據為己有。他捐贈了大量價值不菲的家族物件給研究展覽機構,他樂意和更多人分享這個家族的歷史。
63歲的陳天培是末代帝師陳寶琛的曾侄孫。做了近四十年鄉村醫生,在說起自己的人生時,陳天培有些羞澀,他說他的愛好是寫詩詞,只是相較于家族中的多位名人,他覺得自己的水平不夠。他曾經自費出過一本詩集《磨硯室詩稿》,書中收錄了他近千首詩詞,這只是他幾十年所做詩作的小部分。雖然詩集印刷排版并不精致,詩詞中的對仗押韻也未能每首都考究,但一個人踐行四五十年的人生理想,讓我開始反思什么是生活的趣味。
72歲的沈丹昆是沈葆楨的六世嫡孫,在采訪結束后,給我發來了他曾寫過的一篇回憶自己外祖母的文章,還有其母親、妻子的照片,囑我文章中提到她們,因為“那都是我最愛的人”。老頑童一樣的沈先生常常讓我感動,他用心維系著和親人間自然、溫暖的情感。母親去世后,沈丹昆和四個姐姐曾為父母編寫了一本書《相約回憶里》,五個孩子記憶里的父母其實是各自人生中一段不可或缺的經歷。
66歲的林祝光和我的母親同齡,和那一代多數城市青年一樣,經歷上山下鄉,經歷十六七歲的年齡獨自面對無從下腳的牛糞、吸血的水蛭,吃不飽的饑餓感,以及遙遙無期的回家夢。林祝光是林則徐的第六世孫女,堅韌和要強是度過那個非常時期的方式,也是那一代選擇如何度過自己人生的方式。
……
在他們經歷的人生里,我看見自己的困惑,感受到父母祖父母經歷的時代,也體會到讓人可以放松下來的從容、溫暖和堅定。這也許就是歷史于每個個體來說較大的價值——幫助我們接納自己。家史,讓我這個在歷史感上一向愚笨的人,及時次有了切膚之感。
當這個計劃開始的時候,一種時間的緊迫感也驟然而至。從2004年到2015年,11年間可以發生太多事情,其中最無能為力的莫過于生死。重新尋訪那些家族后人,常常碰上老人已去世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仿若風箏斷線。在中國歷史上,這些老人多是經歷清朝、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時期的人;在家族史上,他們又常常是一代曾經居住于家族宅院、有過大家族生活記憶的人。如今,這些大家族的宅院多數收歸國有或改作他姓,其中多數被拆遷,極少數成為博物館等公共空間。因為無族人居住,即使在名人故居這樣的空間,除了重新修復后的物理結構與肌理,一個家族的歷史印記和血脈相承的溫度,已難以尋覓。
時間走得太快,也許了解一段家史是抵抗焦慮不安的更好開始。
,感謝12年來不斷支持這本書出版的每一位朋友,他們的鼓勵和期待給了我莫大的動力;感謝攝影師莊方,在及時次合作的11年后,奔赴美國游學前,騰出時間,拍攝近期照片;感謝攝影師陳暖、手繪地圖工作者池志海,為本書提供重要影像;感謝《homeland家園》設計師林增穎的精心編排,感謝老友阿或的視覺監督。他們的付出讓這本書得以以現在的模樣呈現。更感謝每位受訪者,愿意以莫大的勇氣回憶和分享自己及一個家族的歷史。
內文節選
一個人文官宦世家的范本:沈葆楨家族:
19世紀60年代,中國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洋務運動應運而生。關于這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維護封建統治的“自強”“求富”運動,教科書和各種歷史書籍,將大量的篇幅給了其中的中樞代表人物愛新覺羅 奕和文祥,以及地方代表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直到近年,開始有史學家認為,“像沈葆楨這樣在這場變革的實踐中走得更遠的官僚,長期以來受到不應有的忽視”。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政府用領地、主權等一系列政經特權暫時喂飽外國侵略者,國內的農民起義進入低潮,社會呈現出暫時的“穩定”局面。在清朝統治集團內,無論是清政府中樞,還是地方,已有一派人并未因這表面的“和局”而減少對清政府統治的危機感。地方要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雖然剛因剿滅太平天國而建立功勛,但他們在借助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進行鎮壓的過程中,因親眼所見外國侵略者的堅船利炮,深刻感受到了一種潛在的長遠危機。
同時期的西方各國,在新航路的開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資產階級革命、產業革命的推動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初步完成。在這個世界整體化的趨勢下,中國也正在被動卷入。洋務運動由此開始。以洋務運動為背景,沈葆楨個人史上最重要的一段也就此鋪開。
沈葆楨,字幼丹,晚清重臣林則徐的外甥和女婿。在其近60年的短短一生中,沈葆楨經歷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皇帝。在中國近代史上,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首任船政大臣、直接處理對日交涉事宜的欽差、臺灣地區近代化的開拓者。
對于這樣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自晚清以來便有多人研究。光緒九年(1879年),沈葆楨病逝,時任兩江總督,死后入史館立傳,嗣賢良祠,并在各省設立專祠。縱觀之后近百年的沈葆楨研究,也如同一張中國政治氛圍的晴雨表,時漲時落。
2000年,美籍學者龐百騰出版《沈葆楨評傳——在中國近代化的嘗試》一書,以詳盡的史料,評述了清朝末年沈葆楨創建座海軍船廠和學堂的得失,并以沈葆楨個案研究的方式,深入探討了洋務派領袖們的內心世界,以及洋務運動自身無法克服的困難。
書中,龐百騰這位出生于香港、來自美國最古老的大學——特拉華大學——的教授,給沈葆楨的評價是:“在洋務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一個真正的過渡人物,他伸向外部世界,以尋求解決中國弊端,同時仍然牢固地根植于儒家思想。沈葆楨處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清王朝正進行著‘同治中興’的背景下,他所從事的事業乃是洋務事業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改革實踐和思想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儒家‘經世致用’,已經超越了盡忠朝廷的局限而趨向于近代的民族主義。”
沈葆楨的身份,除了晚清要臣、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中國近代造船、航運、海軍建設事業的奠基人外,他還是福州一個傳統士大夫家族的重要傳承人,是林則徐賞識的女婿,是5個孩子(七子八女)的父親。之后的上百年時間,逐漸龐大的沈氏家族雖然再沒出現過像這位先祖一樣影響深遠的人物,但也不乏名人。沈葆楨之后的六七代沈家后人中,二至五代有相當數量的后人延續了沈葆楨一生曾奮斗的造船、海軍、外交幾個領域的事業。之后,沈家后人為官、經商的少,當教師、醫生、工程師、律師的多。
沈葆楨:晚清“經世致用”的實踐者
沈葆楨的祖先原籍河南,南宋時遷至浙江湖州,清初移居杭州,雍正年間來到福州安家落戶。來閩后,沈氏最初三代以游幕或商賈為生,擔任州縣屬吏,管理錢谷。傳到第四代,沈葆楨的父親沈廷楓,才摒棄游幕世業,走科舉之路。
沈廷楓雖獲功名,但只是個道光舉人,而且中舉時已經46歲,并未改變家境清貧的狀況。俗話“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了沈家當時的狀況。以教書為業的沈廷楓收入微薄,經常入不敷出,要靠妻子——林則徐六妹林惠芳——做女紅貼補家用。
那時,沈家住一間朝西的房子,冬天寒風凜冽,夏天驕陽曝曬,讀書和操作女紅同為一室,極為簡陋。為了節省菜肴、節約米糧,沈家的一日三餐常年為粥。
家境雖貧,沈家卻24小時也不敢讓孩子廢學。沈葆楨五歲開始讀書,由于他在死記硬背方面比較笨拙,沈母便逐字講解,助子成誦。從書店買回的課本粗糙,看起來吃力,沈母便手抄下來,方便其閱讀。稍微長大一些,沈葆楨便跟隨父親到外邊就讀于父親任教的學館。一旦回家,沈母必親自考察其所讀過的書。
除了讀書,沈母相當注意兒女的德育。沈葆楨小時候膽小,夜里聽見貓叫都害怕,沈母便用儒家傳統道德觀念對他進行教育。沈母問:“你敬仰古代的忠臣孝子嗎?”葆楨答:“敬仰。”沈母又問:“你知道忠孝不可以無膽嗎?”葆楨答:“不知道。”沈母隨即舉例說明,古代忠臣孝子,萬死一生,百折不撓,才能終成其志。看到孩子高興了,沈母便問:“你知道膽子是從哪兒來的嗎?”葆楨答:“他們天生大膽。”沈母立即駁斥:“不對!”接著耐心開導:“人都有受驚的時候,在這當兒,你應捫心自問,沒辦過虧心事吧,于是膽就壯了。”以后,看到兒子膽子變大,就叫他獨自往返于陰森可怕的地方,直至其膽量越來越大。
沈家父母的家教,為沈葆楨日后中舉人、入翰林院,并將沈氏帶入福州望族做了準備。而此后沈葆楨為官時表現出的耿直、剛正、獨立,也能在此找到根源。
家族奠基者
1840年,21歲的沈葆楨雙喜臨門。
一喜是與林普晴完婚,二喜是中舉人。這兩件事可以說是沈葆楨顯宦人生的開始。
林普晴是林則徐的次女,12歲時與比自己大一歲多的沈葆楨訂婚。當時的林則徐已任江蘇巡撫,這個朝廷封疆大吏能選中家境清貧的窮外甥沈葆楨做女婿,是因為對這位少年才俊的賞識。林普晴在閨中從未嘗過饑寒的滋味,來到沈家后,不愁吃穿的優裕生活沒有了,吃的是粗茶淡飯,而且要下廚操刀。不過,這位賢淑的沈夫人卻并不覺得苦。
在沈葆楨傳記中,記載著這樣一個場景:24小時,林普晴在婆婆的鏡匣中發現一張憑證,便問:“娘,這是什么東西?”沈母答:“這是質券。昨天缸里的米吃完了,把衣服、棉被送到當鋪換錢買米。”自此之后,當票成了她手中的常客。為了給沈葆楨進京趕考籌集路費,林普晴典當了嫁妝中的金手鐲,終身改戴藤鐲子。沈葆楨滯留京城多年,到中進士、點翰林時,其家積欠債務達白銀千兩,由林普晴百計補苴。
沈葆楨在仕途上的作為也并未讓這位沈夫人失望。1854至1855年間,先后任江南、貴州道監察御史。之后,一路升任。1860年,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時,已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清代的“輕車都尉”是外姓功臣與外戚的爵位稱號,如同擁有爵位的貴族,享有固定的俸祿。歷史上的和珅,曾原襲三等輕車都尉。關于沈家“一等輕車都尉”這一世職,也體現在了沈葆楨之后數代嫡長房后代的名字上。據沈葆楨六世孫沈丹昆先生介紹,從沈葆楨開始,沈家將自己的嫡長房長孫都冠以“丹”字,一方面是沈葆楨為了紀念父親丹林公(沈葆楨的父親沈廷楓,號丹林),一方面用于世襲清朝“一等輕車都尉”之職時作為“名字的記號”用。
計劃外的船政生涯
1866年3月,母親病逝,沈葆楨回福州奔喪。不久,便開始了讓他聲名遠播的船政生涯。1866年5月,閩浙總督左宗棠建議創辦福建船政。10月,左宗棠調任陜甘總督,舉薦沈葆楨為總理船政大臣。關于當年重孝在身的沈葆楨為何接受福建船政大臣這一任命,2011年的《文史參考》里有過一段描述:“左宗棠請沈葆楨出山并非一帆風順,也曾三顧茅廬,二人在這個古香古色的小院里暢談了很久,左宗棠準備打造中國自己的海軍,而沈葆楨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選。左宗棠及時次來到沈宅,懇請沈葆楨出山繼承船政事業,沈葆楨婉言拒絕。左宗棠保障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楨聯名署簽奏折,并給他推薦著名商人胡雪巖相助,所有人馬,歸其調遣。沈葆楨還是猶豫不決,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薦沈葆楨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楨‘先行接辦’,‘不準固辭’。本無心官場的沈葆楨,還是接受了這個艱巨的任務。”《沈葆楨評傳——在中國近代化的嘗試》一書這樣評價沈葆楨的這個決定,“本來他可以謀求更為高級的職務,他幾乎是抱著犧牲仕途的決心,選擇了這份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將辦公的地點設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宮巷26號(曾為宮巷11號)這個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國近代船政工業的思想發源地。
沈葆楨到任后,按左宗棠所定計劃,在馬尾征購土地,建設工廠、船塢、學堂和宿舍,開始的船政建設。當時遠東較大的造船廠——福州船政局馬尾造船廠建成,并正式投產,八年時間,造出5艘商船和11艘兵艦,當時其總噸位名列世界第十。這些輪船,后來裝備起代海軍艦隊。此外,沈葆楨在同時期創辦了“近代中國船舶工業與海軍人才的搖籃”——福建船政學堂,培養出一大批叱咤風云的人物:甲午海戰中犧牲的劉步蟾和林永升、清海軍總長劉冠雄、中國海軍元老薩鎮冰……
1879年11月,彌留之際,沈葆楨把隨侍江寧的第四子沈瑜慶喚至榻前,以斷斷續續的言語交代后事。這后事并未提及對家人、遺產的安排,而是念念不忘購買鐵甲船,要兒子為他草擬一章奏疏,希望朝廷把這作為海防建設的及時要圖。沈葆楨死后,清政府追謚他為“文肅”,并追贈太子太保銜。清朝時,太子太保從一品官,有銜無職,通常是作為一種榮譽性的官職加給重臣近臣,由此可見沈葆楨在當時朝廷中的位置與影響。
沈葆楨的性情
當沈葆楨真正從左宗棠手中接過龐大的船廠時,他發現要勝任這一職位,所需要調動的知識和能量遠遠超過了他昔日的想象。
沈葆楨知道,只有一所船廠不足以建立起近代化的國防體系。于是,他在四個領域企圖拓展中國近代化的基礎——培養新型海軍人員并組織福州艦隊、促進學科學、建設近代煤礦和鋪設及時條電報線。在煤礦、電報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領域,他獲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改革教育制度和財政制度這些更為關鍵的方面,他卻遭到了無法避免的慘敗。就改革科舉制度來說,雖然沈葆楨僅僅提出在考試內容中增添數學,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這一修訂將引發嚴重的連鎖反應。龐百騰教授分析說,這一微妙的變化“將迫使修正科舉制度的哲學基礎,改變自理學興起近千年以來被認為是學者和官員應有的基本品質”。同時,“這也會損害學者和士紳階級的既得利益”,所以,皇帝堅決地否定了沈葆楨的建議。
同樣,沈葆楨改革財政制度的想法也沒有得以實踐。依靠一套中世紀式的、中央與地方職權不明確的、充斥著貪污腐敗的財政稅收制度,不可能支撐起耗資巨大的近代國防工業。福州船政局從建立起,就面臨著資金的困難。晚年的沈葆楨曾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籌款上,但依靠個人聲望和官職的籌款只能暫時有效。之后,沈葆楨的去世對于船廠來說,不亞于一場“地震”。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884年,他苦心經營的福建水師在中法戰爭中遭受重創,幾乎全軍覆沒。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這句沈葆楨當年為鄭成功所題的詩句,也概括了沈自己的一生。
宮巷內外,尋訪沈葆楨家族血脈遺產
重新修建后的三坊七巷是福州最有人氣的景點,
從熱鬧的南街拐進宮巷,幽深的巷子、高高的馬頭墻、清冷的石板路、三三兩兩的游客,有種時光瞬間安靜下來的感覺。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達夫曾寫過一段對這條巷子的描述:“走過宮巷,見毗連的大宅,都是鐘鳴鼎食之家……兩旁進士匾額,多如市上招牌。”這些鐘鳴鼎食的大戶人家中,沈家因為晚清名臣沈葆楨而得名。
進入宮巷,經過花巷幼兒園,左側便是沈葆楨故居。仍住著沈家后人的沈葆楨故居,是宮巷導覽指示牌上的及時站,也是這條巷子中保護級別較高的兩所宅院之一。在宮巷的七個文物保護點中,沈葆楨故居和林則徐之子林聰彝的故居是僅有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只是,朱紅色斑駁的沈家大門后貼了一張手寫的紙條,“私人住宅非請勿進”,旁邊房門緊鎖,偶爾能遇見住在里面的沈家后人進出。改造后的三坊七巷,多數名人故居被政府收儲后改造成了紀念館,沈家大院算是少有未被改造的名人院子。這也讓一些慕名而來的游客只能止步于此。
幾次采訪都是和沈葆楨的六世嫡孫沈丹昆先生約好,沈先生每次在沈葆楨故居大門右側10米左右的一個側門等待。側門打開,是一溜長長的三進宅院。沈丹昆生活在上海的女兒來過幾次,稱這里像筷子,沈先生就住在“筷子”中段的一個廂房。這個房間曾是沈丹昆父母住過的地方,也是沈丹昆的曾祖父沈翊清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雖然狹長,這一列宅子卻是天井、花廳、廂房、藏書樓俱全,只是尺寸顯小巧。藏書樓前面的天井有一扇門通往隔壁的院子。隔壁其實就是沈葆楨曾經辦公的簽押房,再往東,是沈葆楨曾經住過的三進廂房。
從沈葆楨故居示意圖上清晰可見,這座沈家大院由風火墻分割的三列院落組成。沈丹昆說,這座原本是宮巷11號、面積2747平方米的沈家大院分為兩個部分,右側的兩列建于明朝天啟年間,數易其主,在清同治年間由沈葆楨買下供祖孫居住,左側靠花巷幼兒園的這一列,則是由沈丹昆的曾祖父沈翊清,即沈葆楨的長孫,在清末時購置。“曾祖父買下的這部分也是明朝時所建,他買下
來之后重新整修了一次,所以門窗、壁櫥、家具是民國時期比較簡潔的風格。”如今,沈家后人多是住在故居大門背后的三進院子。連接用于藏書的飲翠樓和簽押房的門多數時間也都關著,沈翊清的曾孫輩早已搬離老宅,只有沈丹昆每年會從上海回來小住一段,會會親戚朋友,打理打理老房子。
72歲的沈丹昆說,現在沈家院子里只住著十來個人,曾在1949年后住進來的外姓人家這幾年跟政府談好搬遷條件,陸續搬走了;家族里的年輕人也因為不習慣老宅生活,不會再來住,現在還住這里的多是和他一樣年紀的念舊老人。雖然他在初中畢業后去了上海,從此在上海安家,但從小在這兒出生,在這兒長大,早就習慣了這南方院子里的潮濕,以及這院子獨有的清凈,在上海的時候他會想念。
2015年,沈丹昆因為參加林則徐誕辰230周年紀念活動,從上海回福州住了幾個月。沒事的時候,沈丹昆會去找住在隔壁的堂弟沈達先,兩人在天井曬曬太陽、敘敘舊,“這院子里有太多的故事,太多來來往往的人,講不完……”
船政世家逐漸形成
1866年到1879年的13年間,沈葆楨在船政方面的積極作為,讓其日后獲得了“中國海軍之父”的身份,也讓沈家日后評為福州較大的船政世家成為可能。
在福州馬尾中國船政文化的官方網站上,有一篇文章《沈家船政精英不斷》,羅列了自沈葆楨開始,出自沈家的12位船政精英。沈丹昆和沈達先認為這篇文章中提到的部分人物身份有誤,但沈家與中國船政、海軍的關系,綿延數代。以下列舉沈葆楨的二三四代中在船政和海軍方面的主
不錯!速度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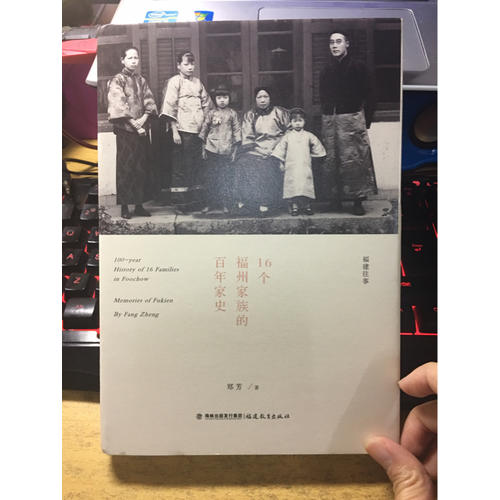 想對福州多一些了解
想對福州多一些了解
很好,非常滿意
送別人的,可以
挺不錯的。也是個比較獨特的選題。
很好很好啊!
很棒的書,很喜歡。
正版,字跡清晰,挺好的,喜歡!
買書必**當!書還真不錯,一直信賴當當。希望當當一直以這種良好姿態、健康的發展、負責的態度來服務書友。十分感謝當當給我帶來的實惠、方便和快樂!
收到了 還沒看
書不錯,值得購買
書不錯,值得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