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作者的童年回憶為引線,描繪了東北邊陲小鎮呼蘭河的風土人情:不斷給人帶來災難的東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小城的精神“盛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臺子戲、四月十八娘報廟會,令人心碎的小團圓媳婦的慘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馮歪嘴子一家的艱辛生活……作品通過追憶家鄉的各種人物和生活畫面,描述了一個北方小城鎮單調的美麗、人性的善良與愚昧。
這是蕭紅代表性的作品,曾被香港“亞洲文壇”評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百強第九位。
蕭紅(1911—1942),出生于黑龍江省呼蘭縣。原名張乃瑩,筆名蕭紅,被譽為“三十年代文學洛神”。1935年首次以蕭紅為筆名,出版了小說《生死場》。更有成就的是寫于香港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以及一系列回憶故鄉的中短篇小說《牛車上》《小城三月》等。
呼蘭河這小城里邊住著我的祖父。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個大花園,這花園里蜂子,蝴蝶,蜻蜓,螞蚱,樣樣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黃蝴蝶。這種蝴蝶極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紅蝴蝶,滿身帶著金粉。
蜻蜓是金的,螞蚱是綠的,蜂子則嗡嗡的飛著,滿身絨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圓圓的就和一個小毛球似的不動了。
花園里邊明皇皇的,紅的紅,綠的綠,新鮮漂亮。
據說這花園,從前是一個果園。祖母喜歡吃果子就種了果園。祖母又喜歡養羊,羊就把果樹給啃了。果樹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記憶的時候,園子里就只有一棵櫻桃樹,一棵李子樹,因為櫻桃和李子都不大結果子,所以覺得它們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時候,只覺得園子里邊就有一棵大榆樹。
這榆樹在園子的西北角上,來了風,這榆樹先嘯,來了雨,大榆樹先就冒煙了。太陽一出來,大榆樹的葉子就發光了,它們閃爍得和沙灘上的蚌殼一樣了。
祖父24小時都在后園里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后園里邊。祖父戴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當祖父下種種小白菜的時候,我就跟在后邊,把那下了種的土窩,用腳一個一個的溜平,那里會溜得準,東一腳的,西一腳的瞎鬧。有的把菜種不單沒被土蓋上,反而把菜子踢飛了。
小白菜長得非常之快,沒有幾天就冒了芽了。一轉眼就可以拔下來吃了。
祖父鏟地,我也鏟地,因為我太小,拿不動那鋤頭桿,祖父就把鋤頭桿拔下來,讓我單拿著那個鋤頭的“頭”來鏟。其實那里是鏟,也不過爬在地上,用鋤頭亂勾一陣就是了。也認不得那個是苗,那個是草。往往把韭菜當做野草一起的割掉,把狗尾草當做谷穗留著。
等祖父發現我鏟的那塊滿留著狗尾草的一片,他就問我:
“這是什么?”
我說:
“谷子。”
祖父大笑起來,笑得夠了,把草摘下來問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這個嗎?”
我說:
“是的。”
我看著祖父還在笑,我就說:
“你不信,我到屋里拿來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鳥籠上的一頭谷穗,遠遠的就拋給祖父了。說:
“這不是一樣的嗎?”
祖父慢慢的把我叫過去,講給我聽,說谷子是有芒針的。狗尾草則沒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雖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細看,也不過馬馬虎虎承認下來就是了。一抬頭看見了一個黃瓜長大了,跑過去摘下來,我又去吃黃瓜去了。
黃瓜也許沒有吃完,又看見了一個大蜻蜓從旁飛過,于是丟了黃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飛得多么快,那里會追得上。好者一開初也沒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來,跟了蜻蜓跑了幾步就又去做別的去了。
采一個倭瓜花心,捉一個大綠豆青螞蚱,把螞蚱腿用線綁上,綁了一會,也許把螞蚱腿就綁掉,線頭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見螞蚱了。
玩膩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亂鬧一陣,祖父澆菜,我也搶過來澆,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澆,而是拿著水瓢,拚盡了力氣,把水往天空里一揚,大喊著:
“下雨了,下雨了。”
太陽在園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別高的,太陽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睜不開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鉆出地面來,蝙蝠不敢從什么黑暗的地方飛出來。是凡在太陽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連大樹都會發響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對面的土墻都會回答似的。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愿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愿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似的。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他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墻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墻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
只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
可是白云一來了的時候,那大團的白云,好像灑了花的白銀似的,從祖父的頭上經過,好像要壓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個陰涼的地方睡著了。不用枕頭,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臉上就睡了。
二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成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個長得很高的人,身體很健康,手里喜歡拿著個手杖。嘴上則不住的抽著旱煙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歡開個玩笑,說:
“你看天空飛個家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給取下來了,有的時候放在長衫的下邊,有的時候放在袖口里頭。他說:
“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
孩子們都知道了祖父的這一手了,并不以為奇,就抱住他的大腿,向他要帽子,摸著他的袖管,撕著他的衣襟,一直到找出帽子來為止。
祖父常常這樣做,也總是把帽放在同一的地方,總是放在袖口和衣襟下。那些搜索他的孩子沒有一次不是在他衣襟下把帽子拿出來的,好像他和孩子們約定了似的,“我就放在這塊,你來找吧!”
這樣的不知做過了多少次,就像老太太長期講著“上山打老虎”這一個故事給孩子們聽似的,那怕是已經聽過了五百遍,也還是在那里回回拍手,回回叫好。
每當祖父這樣做一次的時候,祖父和孩子們都一齊的笑得不得了。好像這戲還像及時次演似的。
別人看了祖父這樣做,也有笑的,可不是笑祖父的手法好,而是笑他天天使用一種方法抓掉了孩子的帽子,這未免可笑。
祖父不怎樣會理財,一切家務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的24小時閑著,我想,幸好我長大了,我三歲了,不然祖父該多寂寞。我會走了,我會跑了。我走不動的時候,祖父就抱著我,我走動了,祖父就拉著我。24小時到晚,門里門外,寸步不離,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園里,于是我也在后園里。
我小的時候,沒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親的及時個孩子。
我記事很早,在我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我的祖母用針刺過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歡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邊糊紙,當中嵌著玻璃,祖母是有潔癖的,以她屋的窗紙最白凈。別人抱著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邊上,我不假思索的就要往炕里邊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把那白白透著花窗欞的紙窗給通了幾個洞,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著排給通破,若有人招呼著我,我也得加速的搶著多通幾個才能停止。手指一觸到窗上,那紙窗像小鼓似的,嘭嘭的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來追我的時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著手,跳著腳的。
有24小時祖母看我來了,她拿了一個大針就到窗子外邊去等我去了。我剛一伸出手,手指就痛得厲害。我就叫起來了。那就是祖母用針刺了我。
從此,我就記住了,我不喜她。
雖然她也給我糖吃,她咳嗽時吃豬腰燒川貝母,也分給我豬腰,但是我吃了豬腰還是不喜她。
在她臨死之前,病重的時候,我還曾嚇了她一跳。有一次她自己一個人坐在炕上熬藥,藥壺是坐在炭火盆上,因為屋里特別的寂靜,聽得見那藥壺骨碌骨碌的響。祖母住著兩間房子,是里外屋,恰巧外屋也沒有人,里屋也沒人,就是她自己。我把門一開,祖母并沒有看見我,于是我就用拳頭在板隔壁上,咚咚的打了兩拳。我聽到祖母“喲”的一聲,鐵火剪子就掉了地上了。
我再探頭一望,祖母就罵起我來。她好像就要下地來追我似的。我就一邊笑著,一邊跑了。
我這樣的嚇唬祖母,也并不是向她報仇,那時我才五歲,是不曉得什么的。也許覺得這樣好玩。
祖父24小時到晚是閑著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給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櫬上的擺設,有一套錫器,卻總是祖父擦的。這可不知道是祖母派給他的,還是他自動的愿意工作,每當祖父一擦的時候,我就不高興,一方面是不能領著我到后園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罵,祖母罵他懶,罵他擦的不干凈。祖母一罵祖父的時候,就常常不知為什么連我也罵上。
祖母一罵祖父,我就拉著祖父的手往外邊走,一邊說,
“我們后園里去吧。”
也許因此祖母也罵了我。
她罵祖父是“死腦瓜骨”,罵我是“小死腦瓜骨”。
我拉著祖父就到后園里去了,一到了后園里,立刻就另是一個世界了。決不是那房子里的狹窄的世界。而是寬廣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遠,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長的又是那么繁華,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覺得眼前鮮綠的一片。
一到后園里,我就沒有對象的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準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兒等著我似的。其實我是什么目的也沒有。只覺得這園子里邊無論什么東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若不是把全身的力量跳盡了,祖父怕我累了想招呼住我,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他越招呼,我越不聽話。
等到自己實在跑不動了,才坐下來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過隨便在秧子上摘下一個黃瓜來,吃了也就好了。
休息好了又是跑。
櫻桃樹,明是沒有結櫻桃,就偏跑到樹上去找櫻桃。李子樹是半死的樣子了,本不結李子的,就偏去找李子。一邊在找還一邊大聲的喊,在問著祖父:
“爺爺,櫻桃樹為什么不結櫻桃?”
祖父老遠的回答著。
“因為沒有開花,就不結櫻桃。”
再問:
“為什么櫻桃樹不開花?”
祖父說:
“因為你嘴饞,它就不開花。”
我一聽了這話,明明是嘲笑我的話,于是就飛奔著跑到祖父那里,似乎是很生氣的樣子。等祖父把眼睛一抬,他用了沒有惡意的眼睛一看我,我立刻就笑了。而且是笑了半天的工夫才能夠止住,不知那里來了那許多高興。把后園一時都讓我攪亂了,我笑的聲音不知有多大,自己都感到震耳了。
后園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開花的。一直開到六月。花朵和醬油碟那么大。開得很茂盛,滿樹都是,因為花香,招來了很多的蜂子,嗡嗡的在玫瑰樹那兒鬧著。
別的一切都玩厭了的時候,我就想起來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脫下來用帽兜子盛著。在摘那花的時候,有兩種恐懼,一種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種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異想天開,這花若給祖父戴起來該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給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給他插了一圈的花,紅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邊插著一邊笑,當我聽到祖父說: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們這棵玫瑰開得這么香。二里路也怕聞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來。我幾乎沒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還是安然的不曉得。他還照樣的拔著垅上的草。我跑得很遠的站著,我不敢往祖父那邊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機進屋去找一點吃的來,還沒有等我回到園中,祖父也進屋來了。
那滿頭紅通通的花朵,一進來祖母就看見了。她看見什么也沒說,就大笑了起來。父親母親也笑了起來,而以我笑得最厲害,我在炕上打著滾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來一看,原來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緣故,而是那花就頂在他的頭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鐘還停不住,過一會一想起來,又笑了。
祖父剛有點忘記了,我就在旁邊提著說:
“爺爺……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來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滾來。
就這樣24小時24小時的,祖父,后園,我,這三樣是一樣也不可缺少的了。
刮了風,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樣,在我卻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沒有去處,玩沒有玩的,覺得這24小時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長。
三
偏偏這后園每年都要封閉一次的,秋雨之后這花園就開始凋零了,黃的黃,敗的敗,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滅了。好像有人把它們摧殘了似的。它們一齊都沒有從前那么健康了。好像它們都很疲倦了,而要休息了似的,好像要收拾收拾回家去了似的。
大榆樹也是落著葉子,當我和祖父偶爾在樹下坐坐,樹葉竟落在我的臉上來了。樹葉飛滿了后園。
沒有多少時候,大雪又落下來了,后園就被埋住了。
通到園去的后門,也用泥封起來了,封得很厚,整個的冬天掛著白霜。
我家住著五間房子,祖母和祖父共住兩間,母親和父親共住兩間。祖母住的是西屋,母親住的是東屋。
是五間一排的正房,廚房在中間,一齊是玻璃窗子,青磚墻,瓦房間。
祖母的屋子,一個是外間,一個是內間。外間里擺著大躺箱,地長桌,太師椅。椅子上鋪著紅椅墊,躺箱上擺著朱砂瓶,長桌上列著坐鐘。鐘的兩邊站著帽筒。帽筒上并不掛著帽子,而插著幾個孔雀翎。
我小的時候,就喜歡這個孔雀翎,我說它有金色的眼睛,總想用手摸一摸,祖母就一定不讓摸,祖母是有潔癖的。
還有祖母的躺箱上擺著一個座鐘,那座鐘是非常稀奇的,畫著一個穿著古裝的大姑娘,好像活了似的,每當我到祖母屋去,若是屋子里沒有人,她就總用眼睛瞪我,我幾次的告訴過祖父,祖父說:
“那是畫的,她不會瞪人。”
我一定說她是會瞪人的,因為我看得出來,她的眼珠像是會轉。
還有祖母的大躺箱上也盡雕著小人,盡是穿古裝衣裳的,寬衣大袖,還帶頂子,帶著翎子。滿箱子都刻著,大概有二三十個人,還有吃酒的,吃飯的,還有作揖的……
我總想要細看一看,可是祖母不讓我沾邊,我還離得很遠的,她就說:
“可不許用手摸,你的手臟。”
祖母的內間里邊,在墻上掛著一個很古怪很古怪的掛鐘,掛鐘的下邊用鐵鏈子垂著兩穗鐵苞米。鐵苞米比真的苞米大了很多,看起來非常重,似乎可以打死一個人。再往那掛鐘里邊看就更稀奇古怪了,有一個小人,長著藍眼珠,鐘擺一秒鐘就響一下,鐘擺一響,那眼珠就同時一轉。
那小人是黃頭發,藍眼珠,跟我相差太遠,雖然祖父告訴我,說那是毛子人,但我不承認她,我看她不像什么人。
所以我每次看這掛鐘,就半天半天的看,都看得有點發呆了。我想:這毛子人就總在鐘里邊呆著嗎?長期也不下來玩嗎?
外國人在呼蘭河的土語叫做“毛子人”。我四五歲的時候,還沒有見過一個毛子人,以為毛子人就是因為她的頭發毛烘烘的卷著的緣故。
祖母的屋子除了這些東西,還有很多別的,因為那時候,別的我都不發生什么趣味,所以只記住了這三五樣。
母親的屋里,就連這一類的古怪玩藝也沒有了,都是些普通的描金柜,也是些帽筒,花瓶之類,沒有什么好看的,我沒有記住。
這五間房子的組織,除了四間住房一間廚房之外,還有極小的,極黑的兩個小后房。祖母一個,母親一個。
那里邊裝著各種樣的東西,因為是儲藏室的緣故。
壇子罐子,箱子柜子,筐子簍子。除了自己家的東西,還有別人寄存的。
那里邊是黑的,要端著燈進去才能看見。那里邊的耗子很多,蜘蛛網也很多。空氣不大好,長期有一種撲鼻的和藥的氣味似的。
我覺得這儲藏室很好玩,隨便打開那一只箱子,里邊一定有一些好看的東西,花絲線,各種色的綢條,香荷包,搭腰,褲腿,馬蹄袖,繡花的領子。古香古色,顏色都配得特別的好看。箱子里邊也常常有藍翠的耳環或戒指,被我看見了,我一看見就非要一個玩不可,母親就常常隨手拋給我一個。
還有些桌子帶著抽屜的,一打開那里邊更有些好玩的東西,銅環,木刀,竹尺,觀音粉。這些個都是我在別的地方沒有看過的。而且這抽屜始終也不鎖的。所以我常常隨意的開,開了就把樣樣,似乎是不加選擇的都搜了出去,左手拿著木頭刀,右手拿著觀音粉,這里砍一下,那里畫一下。后來我又得到了一個小鋸,用這小鋸,我開始毀壞起東西來,在椅子腿上鋸一鋸,在炕沿上鋸一鋸。我自己竟把我自己的小木刀也鋸壞了。
無論吃飯和睡覺,我這些東西都帶在身邊,吃飯的時候,我就用這小鋸,鋸著饅頭。睡覺做起夢來還喊著:
“我的小鋸那里去了?”
儲藏室好像變成我探險的地方了。我常常趁著母親不在屋我就打開門進去了。這儲藏室也有一個后窗,下半天也有一點亮光,我就趁著這亮光打開了抽屜,這抽屜已經被我翻得差不多的了,沒有什么新鮮的了。翻了一會,覺得沒有什么趣味了,就出來了。到后來連一塊水膠,一段繩頭都讓我拿出來了,把五個抽屜通通拿空了。
除了抽屜還有筐子籠子,但那個我不敢動,似乎每一樣都是黑洞洞的,灰塵不知有多厚,蛛網蛛絲的不知有多少,因此我連想也不想動那東西。
記得有一次我走到這黑屋子的極深極遠的地方去,一個發響的東西撞住我的腳上,我摸起來抱到光亮的地方一看,原來是一個小燈籠,用手指把灰塵一劃,露出來是個紅玻璃的。
我在一兩歲的時候,大概我是見過燈籠的,可是長到四五歲,反而不認識了。我不知道這是個什么。我抱著去問祖父去了。
祖父給我擦干凈了,里邊點上個洋蠟燭,于是我歡喜得就打著燈籠滿屋跑,跑了好幾天,一直到把這燈籠打碎了才算完了。
我在黑屋子里邊又碰到了一塊木頭,這塊木頭是上邊刻著花的,用手一摸,很不光滑,我拿出來用小鋸鋸著。祖父看見了,說:
“這是印帖子的帖板。”
我不知道什么叫帖子,祖父刷上一片墨刷一張給我看,我只看見印出來幾個小人。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花,還有字。祖父說:
“咱們家開燒鍋的時候,發帖子就是用這個印的,這是一百吊的……還有伍十吊的十吊的……”
祖父給我印了許多,還用鬼子紅給我印了些紅的。
還有戴纓子的清朝的帽子,我也拿了出來戴上。多少年前的老大的鵝翎扇子,我也拿了出來扇著風。翻了一瓶砂仁出來,那是治胃病的藥,母親吃著,我也跟著吃。
不久,這些八百年前的東西,都被我弄出來了。有些是祖母保存著的,有些是已經出了嫁的姑母的遺物,已經在那黑洞洞的地方放了多少年了,連動也沒有動過,有些個快要腐爛了,有些個生了蟲子,因為那些東西早被人們忘記了,好像世界上已經沒有那么一回事了。而今天忽然又來到了他們的眼前,他們受了驚似的又恢復了他們的記憶。
每當我拿出一件新的東西的時候,祖母看見了,祖母說:
“這是多少年前的了!這是你大姑在家里邊玩的……”
祖父看見了,祖父說:
“這是你二姑在家時用的……”
這是你大姑的扇子,那是你三姑的花鞋……都有了來歷。但我不知道誰是我的三姑,誰是我的大姑。也許我一兩歲的時候,我見過她們,可是我到四五歲時,我就不記得了。
我祖母有三個女兒,到我長起來時,她們都早已出嫁了。可見二三十年內就沒有小孩子了。而今也只有我一個。實在還有一個小弟弟,不過那時他才一歲半歲的,所以不算他。
家里邊多少年前放的東西,沒有動過,他們過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頭的生活,是凡過去的,都算是忘記了,未來的他們也不怎樣積極的希望著,只是24小時24小時的平板的,無怨無尤的在他們祖先給他們準備好的口糧之中生活著。
等我生來了,及時給了祖父的無限的歡喜,等我長大了,祖父非常的愛我。使我覺得在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夠了,還怕什么呢?雖然父親的冷淡,母親的惡言惡色,和祖母的用針刺我手指的這些事,都覺得算不了什么。何況又有后花園!后園雖然讓冰雪給封閉了,但是又發現了這儲藏室。這里邊是無窮無盡的什么都有,這里邊寶藏著的都是我所想像不到的東西,使我感到這世界上的東西怎么這樣多!而且樣樣好玩,樣樣新奇。
比方我得到了一包顏料,是中國的大綠,看那顏料閃著金光,可是往指甲上一染,指甲就變綠了,往胳臂上一染,胳臂立刻飛來了一張樹葉似的。實在是好看,也實在是莫明其妙,所以心里邊就暗暗的歡喜,莫非是我得了寶貝嗎?
得了一塊觀音粉。這觀音粉往門上一劃,門就白了一道,往窗上一劃,窗就白了一道。這可真有點奇怪,大概祖父寫字的墨是黑墨,而這是白墨吧。
得了一塊圓玻璃,祖父說是“顯微鏡”。他在太陽底下一照,竟把祖父裝好的一袋煙照著了。
這該多么使人歡喜,什么什么都會變的。你看它是一塊廢鐵,說不定它就有用,比方我撿到一塊四方的鐵塊,上邊有一個小窩。祖父把榛子放在小窩里邊,打著榛子給我吃。在這小窩里打,不知道比用牙咬要快了多少倍。何況祖父老了,他的牙又多半不大好。
我天天從那黑屋子往外搬著,而天天有新的。搬出來一批,玩厭了,弄壞了,就再去搬。
因此使我的祖父,祖母常常的慨嘆。
他們說這是多少年前的了,連我的第三個姑母還沒有生的時候就有這東西。那是多少年前的了,還是分家的時候,從我曾祖那里得來的呢。又那樣那樣是什么人送的,而那家人到今天也都家敗人亡了,而這東西還存在著。
又是我在玩著的那葡蔓藤的手鐲,祖母說她就戴著這個手鐲,有一年夏天坐著小車子,抱著我大姑去回娘家,路上遇了土匪,把金耳環給摘去了,而沒有要這手鐲。若也是金的銀的,那該多危險,也一定要被搶去的。
我聽了問她:
“我大姑在那兒?”
祖父笑了。祖母說:
“你大姑的孩子比你都大了。”
原來是四十年前的事情,我那里知道。可是藤手鐲卻戴在我的手上,我舉起手來,搖了一陣,那手鐲好像風車似的,滴溜溜的轉,手鐲太大了,我的手太細了。
祖母看見我把從前的東西都搬出來了,她常常罵我:
“你這孩子,沒有東西不拿著玩的,這小不成器的……”
她嘴里雖然是這樣說,但她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重看到這東西,也似乎給了她一些回憶的滿足。所以她說我是并不十分嚴刻的,我當然是不聽她,該拿還是照舊的拿。
于是我家里久不見天日的東西,經我這一搬弄,才得以見了天日。于是壞的壞,扔的扔,也就都從此消滅了。
&n
字跡清晰,正版!
老師要求買的
不錯的,很好
發貨很快下次繼續光臨
發貨很快下次繼續光臨
給孩子買的,還沒看,書的外觀不錯。
很好,還可以!
挺好的,值得看
幾年來在當當精挑細選了幾百部經典書籍,謝謝當當。
發貨很快下次繼續光臨
第一次買,應該不錯吧!
老師推薦給孩子的讀物,家長看過后也很喜歡。
蕭紅的書一直都喜歡
剛收到,挺好的
好,很好,非常好。
 拉幾中的戰斗機超爛超爛超爛
拉幾中的戰斗機超爛超爛超爛
孩子喜歡,好
第一次在當當買東西,物流很快,東西很好,
 超級贊,非常喜歡這本書。極力推薦給大家看。
超級贊,非常喜歡這本書。極力推薦給大家看。
 這本書我超喜歡,真的很好看,極力推薦給大家!
這本書我超喜歡,真的很好看,極力推薦給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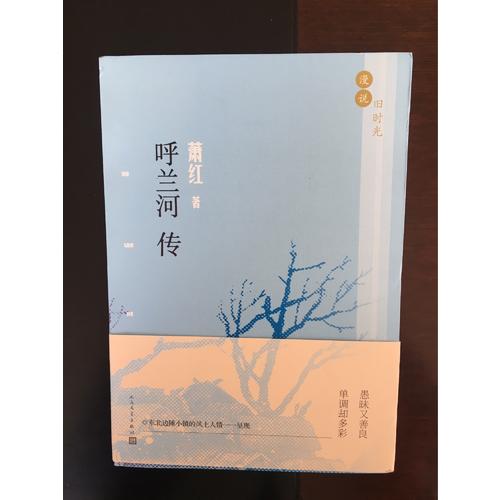 經典著作,品相完美
經典著作,品相完美
這是學校推薦讓孩子寫作業用的書,不知道當當用的快遞為什么越來越慢了,耽誤兩天才送到,孩子急死了,因為假期馬上就結束了,書不到作業沒法寫。不過還是謝謝快遞師傅送到樓上。因為好多書都是老師推薦孩子急用的,希望以后當當提高送貨速度,相信正版才一直用當當,不要讓送貨不當流失客戶!
。。。。。。。
書質量很好,值得購買。
讀書是一種樂趣,讀好的書更是一種享受,當當的圖書品種不僅很全,而且還很正宗,尤其是性價比很高,比實體店便宜好多,實體店沒有的,當當上幾乎都能找到。當當的物流也非常的給力,物流師傅也很辛苦,而且做事很負責任,會一直支持當當。
質量很好,正版點贊
一顆孤獨的心,讓人好傷感
質量很不錯的書 值得購買
頭一天下單,第二天就收到了,給孩子買的,先睹為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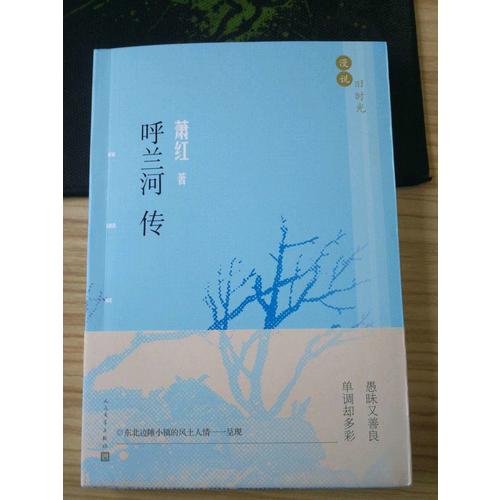 應該不錯,正版!剛收到,還沒閱讀,正版!
應該不錯,正版!剛收到,還沒閱讀,正版!
 書很好,包裝一般。
書很好,包裝一般。
不錯的一本書 有種上學時看書本的感覺 排比 側面描寫 諷刺
有一次在《讀者》上看過節選自《呼蘭河傳》的散文,被驚艷到了,特意買本來慢慢欣賞
包裝運輸中完好無損,當當自營的書質量就是好。
過去的時光讓人難忘,讀來很有感觸,現代人的精神食糧
是別人推薦的,版本較多,仔細挑選后還上是選擇了人民文學的版本,喜歡,收藏用的,還沒看。
本書描繪了東北邊陲小鎮呼蘭河的風土人情:不斷給人帶來災難的東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小城的精神“盛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臺子戲、四月十八娘報廟會,令人心碎的小團圓媳婦的慘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馮歪嘴子一家的艱辛生活……作品通過追憶家鄉的各種人物和生活畫面,描述了一個北方小城鎮單調的美麗、人性的善良與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