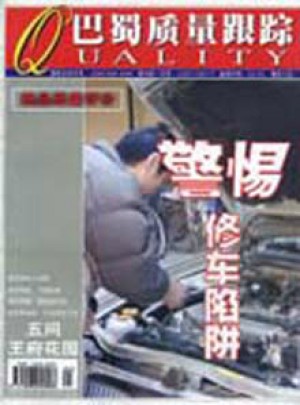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巴蜀文化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2.1濃郁的地域色彩表現色彩設計在包裝設計中占據重要的位置。色彩是美化和突出產品的重要因素。包裝色彩的運用是與整個畫面設計的構思、構圖緊密聯系的。一提到四川、巴蜀文化,人們第一印象應該是豐富的色彩,如同川菜一樣活色生香。巴蜀地氣候濕潤,川人“好吃”,由于地域潮濕,自古以來就愛食辣和麻以達到驅寒的目的,麻辣也自然成為了巴蜀文化的一份子。土特產的包裝比如郫縣豆瓣、新繁泡菜、燈影牛肉就會使用到紅色、棕色,傳達出中國氣息。在四川,鱗次櫛比、青瓦白墻的木屋,狹窄悠長的青石板街道、木柱支撐的寬敞街檐是古鎮給人最為深刻而直觀的視覺印象,也是古鎮文化的外部特征,所以,我們將其作為四川古鎮的典型視覺符號。從這一典型視覺符號中,我們可以提取出青石板路、寬敞街檐、青瓦屋面、木排架、白粉墻、老戲臺、吊腳樓、老榕樹、小橋、流水等形態元素,青灰色、白色、綠色、黑色、棕灰色等色彩元素,以及融古舊、質樸、閑適、恬淡為一體的風格元素。而四川茶館在本地人的生活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由茶碗、茶蓋和茶船組成的蓋碗茶杯,長嘴茶壺,老虎灶,竹扶手椅,白色、黃銅色、棕色、竹黃色,恬淡、隨性,分別代表著四川茶館的設計形態元素、色彩元素和風格元素。四川皮影則使用鮮明的紅黃藍黑色,川劇作為巴蜀文化又一個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使用黑、紅、白為基本色,藍、綠、金、銀、灰、粉紅、姜黃為輔助色,運用上,講求明快、單純、鮮而不艷,淡能傳神。綜上所述,巴蜀文化的色彩運用有著很強烈的裝飾意味。
2.2圖形的表現地域性土特產品就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較為獨特的產品,它的文化特征深受文化底蘊的影響。以巴蜀地區為例,設計師經常使用傳統的能凸顯川味的圖形進行設計。例如金沙遺址的太陽神鳥紋飾,四川茶館的蓋碗、長嘴茶壺、竹圈手椅,川劇臉譜,四川皮影戲,蜀錦,蜀繡,綿竹年畫等,將這些視覺符號化為設計元素,融入到包裝的外形、構圖和材料之中,方能實現土特產品包裝的地域性文化信息傳達。比如說四川閬中地區出名的小吃“張飛牛肉”,有傳說稱劉、關、張三人在桃園結拜兄弟時,曾大擺酒席,為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張飛把他多年制作牛肉的方法說出來,供廚師制作。而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跡是成都武侯祠,這個傳說就凸顯了巴蜀文化。“張飛牛肉”所采用的禮品包裝設計是紅色和黑色的川劇臉譜,采用的字體也是傳統的書法。川劇臉譜是川劇展現給觀眾的最直觀的視覺形象,也是人們區別川劇和其他劇種的一個重要標志,張飛牛肉將川劇的這一視覺藝術形象進行深度大眾文化層面的開發應用,給產品注入了巴蜀文化的藝術魅力,使它地域特色更加明確,使產品更加親切。這是很簡單的例子,卻讓我們看到了產品背后豐富的地理、歷史、傳統文化等內容。而一些禮品包裝,比如彝族的漆器的包裝是從巴蜀文化中傳統工藝品中提取,用了大量的裝飾圖形。其他的諸如蜀錦、蜀繡、扎染、綿竹年畫都是如此,使本土包裝設計具有了視覺上豐富的表現力。
2.3材質的影響
2.3.1紡織品布料及紡織品在本土包裝設計中經常使用,一般來說傳遞出質樸、隨意輕松的感覺,與現代人們崇尚自然的心態不謀而合。巴蜀特產中蜀繡、蜀錦、扎染等既是巴蜀文化的土特產,又可以將這種材質和表現形式作為一種包裝材質運用到土特產的包裝中。成都本土小吃棒棒娃手撕牛肉就使用了布料縫制的標簽和口袋,深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
篇2
完善群眾文化藝術服務體系、擴大文化產業總體規模、增強文化產品的競爭力勢在必行。面對經濟社會發展對文化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從新的高度、以新的視角深刻認識群眾文化藝術建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她對于促進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經濟發展是文化繁榮的基礎,社會進步是文化興盛的條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隨文化的興盛和繁榮。
一、群眾文化藝術的內涵及其特征
群眾文化藝術是人們自娛自樂、表達感情的重要手段,植根于廣泛的群眾基礎之上,它貫穿于廣大群眾的勞動生產、生活過程之中。群眾文化藝術是指人們職業外,自我參與、自我娛樂、自我開發的社會性文化。是以娛樂和陶冶情操方式為主要內容,以自娛自教為主導,以滿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為目的社會歷史現象或是指以廣大群眾以自身為活動主體,以人民群眾活動為主體,反映當地社會生活,以滿足自身精神生活需求為目的文化或意識形態。
二、群眾文化藝術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群眾文化藝術促進社會發展是由群眾文化藝術的三大基本功能即宣傳教化作用、普及知識作用、精神調劑作用決定的,并通過三大基本功能的發揮,達到促進社會和諧的總體目標。群眾文化藝術在促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和諧發展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先進、科學、健康的群眾文化藝術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特殊作用,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繁榮群眾文化藝術是當今新形勢下的一項特殊的任務。群眾文化藝術在社會發展中具有以下作用:
(一)群眾文化藝術能夠促進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發展是文化繁榮的基礎,社會進步是文化興盛的條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隨文化的興盛和繁榮。
(二)群眾文化藝術為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群眾文化藝術的社會教育效能具有廣泛、業余、靈活、方便、普及、實用形式多樣的特點,可以為廣大群眾開辟廣闊的學習空間,不斷提高社會成員的科學文化素質;群眾文化藝術具有寓教于樂的功效,讓參與者在輕松活潑的群眾文化藝術活動中獲得知識,增長才智,因而更富有吸引力。群眾文化藝術通過參與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可以提高社會的整體素養,促進社會更加和諧。
(三)群眾文化藝術為社會發展提供精神支撐。群眾文化藝術具有傳播和整合效能。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基礎。樹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需要先進文化的引導、整合。通過積極創作弘揚和諧精神的優秀群眾文化藝術產品,通過廣泛的群眾文化藝術活動,可以表達和諧社會的理想,宣傳社會發展的主張,使社會發展的精神深入人心。
三、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的主導方向
要使群眾文化藝術在社會發展中能大有作為,必須明確群眾文化藝術發展的主導方向,找準群眾文化藝術發展的重點、難點,采取強有力的措施。
(一)大力開展與普及群眾文化藝術活動。當前的群眾基本文化需要,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個性凸顯以替代成為活動主題,過去以館、站組織開展活動為主,轉變為群眾依靠自身設施開展活動為主。針對此種狀況,群眾文化單位要改變原有工作模式,實現角色轉變。
(二)高度重視群眾文化藝術工作。落實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的公共責任,各級政府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保障廣大群眾的文化基本權益以及社會發展的高度認識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的重要性、緊迫性。特別要明確群眾文化藝術事業是公益性事業,發展群眾文化藝術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把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納入城鄉建設規劃,納入精神文明建設總體規劃,納入財政預算,納入領導干部目標責任考核;要采取有力措施,確保群眾文化藝術的可持續發展。
(三)切實加強群眾文化藝術場所建設。一是要真正體現齊抓共管。爭取上級和政府在政策、資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并在各級政策制定中增加一些硬性指標和要求,讓文化軟實力真正硬起來。二是要真正體現齊抓共建。首先要把文化建設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總體規劃及新農村建設規劃,努力實現文化設施現代化,文化工作制度化,服務對象社會化,活動形式多樣化的新格局。其次要加大人員隊伍建設的投入,進一步落實編制、人員、經費,特別是要加大基層宣傳經費。第三是要創新培養人才模式,通過核定編制,公開選拔等辦法,既解決管理人才問題,同時又解決專業藝術人才問題。三是要建立齊抓共享。主要是解決文化成果不能共享的問題。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工作機制和監督機制,把文化惠民工程落到實處,讓千家萬戶都能享受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是各級各部門要把送政策、送科技、送衛生、幫扶活動與送文化有機結合。
總之,社會發展需要群眾文化藝術的發展,群眾文化藝術蓬勃發展,必定會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1]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10、12、355.
[2]沃林格.抽象與移情[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5,21.
篇3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要求體現在文化陣地建設和城鄉基層文化活動中。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構等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是廣大群眾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場所和宣傳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陣地。對這些陣地要積極建設、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間文化資源,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廣泛開展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眾文化活動。以通俗文學、流行音樂、電視文藝、網絡文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繁榮,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文化糟粕。原創網站:
篇4
一、避暑山莊與外八廟開發現狀
(一)承德避暑山莊與外八廟文物管理困難
承德避暑山莊以及周圍外八廟的旅游資源十分地豐富,各個縣都有自己獨特的旅游資源正待開發,在很多地區都有各自不同的旅游去處,比如灤平縣、興隆縣以及豐寧縣等幾個旅游重地,都有各自不同的旅游景區,景區天然形成,包括森林公園、大型湖泊以及濕地,還有金山嶺長城等知名旅游景點分布。最重要的是承德市內,旅游資源有皇家園林、避暑山莊以及周圍的寺廟群外八廟等去處,去過承德旅游的游客都有瀏覽往返的感覺。不過存在于避暑山莊或者外八廟中的文物保護問題卻日益嚴峻起來,游客對文物的鑒別能力不夠,經常會給文物造成無意識的損壞,這一點在目前的承德市旅游資源開發中卻并未被重視起來。
(二)分散的旅游景點文物難以集中管理
雖然承德市下屬諸多縣中有很多的旅游資源,承德室內也有眾多的旅游資源,尤其以避暑山莊和外八廟聞名全國,但是承德市下屬的各個縣的旅游資源中,也有很多的文物存在,而各個縣對于旅游資源的認識程度不足,造成文物的丟失或者損壞,縣級文物部門并沒有重視這個問題,而將旅游資源中的文物進行產業化還為期尚早。對于文物進行集中管理,效仿其他擁有大量文物的旅游景點,才能夠確保承德市旅游資源中文物的保護工作落實到位。
二、解決山莊與外八廟開發問題的對策研究
(一)加強文物保護區內的游客管理
對于承德市文物保護區內的文物保護條例進行強化管理,是保證文物能夠被保護起來的第一個方法,要首先確保將文物進行有效保護,才能夠談文物產業化問題。文物產業化的前提是好存在一定數量以及完整度的文物群,然后將其用特殊方法納入現代經濟發展鏈條之中,進而產生利益增值的手段。而針對承德市避暑山莊以及外八廟中文物的保護問題,承德市旅游管理部門應該對其加強旅游區域的游客管理,充分利用各種宣傳手段進行游客的文物教育,讓游客感覺到文物的價值以及破壞文物所要承擔的責任,這樣才能夠有效阻止文物被破壞。同時在景區內的文物周邊設置提示標牌,標明文物年代以及在游覽過程中的注意事項,使游客能夠注意此文物的價值所在,這對文物的保護有著很好的作用。如果條件允許,可以在大型文物周邊安裝監控設備與擴音設備,在向游客開放的時候進行監督、實時警告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文物保護方法。
(二)依照政府政策文件,加強部門溝通
針對承德市以及下屬各縣旅游資源中的文物保護問題,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應該主動聯系縣級文物部門,充分協調部門之間的互動,攜手將文物通過一定的方法保護起來。不僅如此,文物保護部門應該牽頭聯絡政府其他相關部門,統一解決旅游資源開發問題。文物保護部門還應與承德市的旅游開發公司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充分利用縣級旅游資源進行旅游開發公司的招標,將中標的旅游公司統一管理,服從政府調配,充分重視文物價值,盡快形成旅游業中的文物產業化發展模式,為當地政府部門創收。對于承德市以及下屬各縣的城鎮化建設與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問題,文物保護部門應該堅決落實文物保護法中的規定,聯絡各級部門將城市基本建設之前的文物勘察工作資金落實到位,招攬專業技術人員進行實地勘察,確保文物不被損壞。
(三)統一管理旅游資源盡快打造文物產業化鏈條
文物產業化,從字面上講就是將我們的先人們留下的有價值的東西轉變成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渠道。文物產業化,將文物的價值體現出來,將其轉變成實際的經濟利益,當然有利必有弊,在文物產業化給我們的經濟帶來突飛猛進的同時也是存在一定的弊端的。文物是歷史遺留的產品,對現代人研究歷史有個很大的幫助,文化產業化會給文物帶來一些列的“破壞”。文化產業化主要是追求的經濟利益,所以,放松管制、沒有結合現狀、環境污染等是經常出現的。利益驅動下和文物接觸的游客就會增加,這是勢必會造成文物的在某種程度上的損壞,甚至造成文物的丟失;但若加緊管理,那就會造成游客的反感,不利于產業化的發展;景區的開發,要結合景區的現狀進行,這樣會牽扯到景區的改造,往往會耗費巨額資金,還破壞了景區原有的風貌。而像承德市避暑山莊以及周圍外八廟的文物產業化問題,首先應該以文物保護部門將文物保護起來,然后促進旅游資源的統一、協調管理,這樣才能為產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承德市避暑山莊與周圍的外八廟是非常稀缺的旅游資源,承德市下屬的各個縣也有很多的旅游資源尚待開發,倘若能夠對其進行統籌管理、協調開發,并且將其中的文物進行產業化,利用地區優勢以及地理位置優勢,這一大旅游景點所產生的經濟價值將不可估量,而對承德市的經濟建設也會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由于承德市的避暑山莊以及外八廟具有悠久的歷史,同時還擁有很大的地理面積優勢,雖然旅游資源分布比較散,但是如果能夠被統一管理起來,加強道路建設,旅游景點中能容納的人流量將排在全國前列。
參考文獻:
[1]林南枝.陶漢軍.旅游經濟學[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篇5
去年,張天冉有幸讀完《古代巴蜀文化探秘》一書,最深刻的印象是書中提到的一組數據:“全國1/3的大佛造像都在重慶境內……”,從小就在大足長大的張天冉非常震驚。在這之前,他一直認為重慶的大佛不多,除了家鄉鼎鼎有名的大足石刻大佛灣,還有就是釣魚城臥佛、淶灘坐佛和潼南大佛。
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張天冉跟著書中的記載,走遍了重慶的各個角落,尋找著那一座座未知的大佛……在張天冉的書架上,有一張重慶地圖,上面用紅筆標注著每一座大佛的座標。
在中國佛教密宗體系中,有一個“五方五佛”的概念,后來經過演繹,從地理分布上重新詮釋出了中國的“五方五佛”,也就是分布在神州大地上的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的五尊大佛。
而在張天冉的“重慶大佛地圖”上,如果以渝中區為中心,佇立在重慶各地的大佛恰好也形成了“五方”之勢。
重慶為什么多大佛?
重慶“五方”都有哪些大佛?在接下來的篇章里,我們會娓娓道來。在這之前,最讓我們感興趣的話題則是——重慶怎么會有這么多大佛?
追溯巴蜀地區的佛教文化,需要將時間撥回到東漢時期。佛教自西漢末年由大月氏使者傳入中國,東漢時開始傳播。20世紀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就在四川麻浩東漢崖墓的石門額上發現了一尊孤立的佛像,證明遠在東漢時期,佛教在向中原地區傳播的同時,也沿著西南國際貿易通道,傳至巴蜀地區。此后,佛教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迅速發展,到唐代達到鼎盛。大唐帝國時期,巴蜀石窟和摩崖造像興盛發達,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以大足、潼南為主的川中石窟區。
唐末天下大亂,加上武宗和后周滅佛,北方一代的寺院受到嚴重破壞,造像活動日漸衰微,但是,在有著“天府之國”美譽的巴蜀地區卻以地方割據勢力為屏障,遭受的打擊較小。于是,重慶的佛教造像不僅沒有受到時代的沖擊,反而呈現出別開生面的景象,并且一直延續了下去——這也是重慶大佛一個極其重要的特點:中國歷史上,唐宋之后,大佛造像便走向衰落,惟獨在重慶,被認為宋代之后就消失的大佛,卻經歷了元、明、清、民國幾個時期,甚至近現代,依然還有大佛實物問世。
當然,真正促成大佛林立的深層次原因,和重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佛教最初鑿窟經像,與佛教徒修禪有著密切的關系。禪定是他們的一種修行方式,僧人習禪要進行禪思,需要有安靜的環境,造像是為了觀像而禪定,最終達到心神與佛相交互融的境界,因此佛教石窟與造像的開鑿,一般選擇在遠離城市喧囂、依山傍水、環境幽靜的地方。經書上說,“出定之時,應于靜處,若在冢間,若在樹下,若在阿練若處。”山水之佳境,使人“望峰息心,窺谷忘返”,人在山水中,心存佛國地。
重慶剛好具有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這里多山,層巒疊嶂;這里多水,浩浩蕩蕩。秀美的山川不但賦予了這座城市絕美的景致,也為眾多大佛的誕生孕育了最適宜的環境。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是:在重慶眾多的高山之間,都建造有寺院廟宇,這也正是重慶自古以來佛事之盛的最佳寫照。
不只是朝拜,更是一場旅行
大佛林立,吸引了眾多祈福求佛的香客,民間流傳的“燒頭香”更是成為每年春節的第一主題。不過,這樣的習俗受到太多追捧,反而讓一座座大佛有了“些許變味”。張天冉很直白地告訴筆者:“拜謁重慶的每一座大佛,應該是一場旅行,而不應該只是一次朝圣,或者燒香磕頭許愿那么簡單。”
事實上,時至今日,籠罩在大佛身上的神秘感漸漸褪去,它們更像是一個個從遠古遺留下來的藝術作品,其魅力遠不是供人朝拜那么簡單。
張天冉說:只有親近了一座座大佛,真正去研究過它們,才會發現佇立在重慶地圖上的這些佛像,每一座都充滿了傳奇。
翻開《古代巴蜀文化探秘》一書,可以閱讀到這樣的描述——
“全國十米以上的大佛家族中,重慶大佛至少占有三大優勢:多、大、齊。
多,重慶的大佛數量多,占據全國1/3;
篇6
一、《成都文類》誤收、漏收詩文情況的研究
關于《成都文類》誤收、漏收詩文情況的研究是現今學界對其研究的重點,共計5篇,簡述如下:
對《成都文類》漏收情況進行研究的,主要是魏紅翎《魏晉南北朝巴蜀文學研究》一文。文中對巴蜀文學的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通過梳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對《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中收錄的魏晉南北朝巴蜀文學的作品進行了糾偏和補遺,并且分別對其進行了闡釋。這一研究成果給學界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巴蜀文學提供了文獻支撐,極具文獻價值。
《成都文類》誤收情況的研究,主要有房銳《雍陶寓居云南說辨析》;趙曉蘭《花蕊夫人考辨》;趙曉蘭、佟博《所載庾闡考辨》;魏紅翎《誤收之魏晉南北朝作品考辨》。其中房銳通過將王安石編《唐百家詩選?卷一七》所錄雍陶詩與《成都文類》卷十四收錄的雍陶詩進行比較,認為王安石編《唐百家詩選》較晚出的《成都文類》完備,從而指出《成都文類》此處所載有所掛漏。[1]趙文認為《成都文類》所錄《宮詞》題記似雜取各家之說而成,且辨花蕊夫人為徐匡璋女、后蜀孟昶妃。[2]另外趙曉蘭、佟博在還認為《成都文類》卷四七《為郗鑒作檄李勢文》之篇題有誤,“為郗鑒作”當作“為庾翼(稚恭)作”,原題或因編纂者連文而致誤。[3]
《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成都文類》云:“所載不免掛漏,然創始者難工。”[4]以上四篇均對《成都文類》所錄詩文內容及作者進行了辨析,指出《成都文類》誤收的情況,并作了相應的辨證,對學界更為清晰地認識《成都文類》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對袁說友的研究,為我們進一步認識《成都文類》所錄詩文內容具有很大的幫助。此類論文主要有羅超華《論袁說友在蜀中的詩歌創作》、李小麗《袁說友易學思想初探》。其中羅超華認為袁說友的蜀中詩歌真實地記錄了其在蜀地的生活狀況,其詩歌語言樸實直白,刻畫意象豐富。[5]對袁說友蜀中詩歌的研究,如其唱和、憫農諸詩,對于我們進一步了解袁說友在蜀中的生活及思想狀況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李小麗則指出袁說友以《周易》為本,思考現實的問題和南宋王朝的命運,重視總結歷代王朝興亡成敗的規律,以利當世。[6]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袁說友始終秉持著為政治服務的變易思想,該文研究成果為我們研究袁說友組織編輯《成都文類》的緣由及選文標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
三、《成都文類》中杜詩及杜甫草堂的研究
杜甫漂泊蜀中近十年,其此階段創作作品占現存杜詩的一半以上,而《成都文類》中收錄杜詩近200首。對《成都文類》中的杜詩及草堂研究,主要有趙曉蘭、佟博《中的杜詩》,趙曉蘭《子美集開詩世界――試論中杜甫草堂詩的詞體特質》,趙曉蘭、佟博《中的杜甫草堂》。
趙曉蘭、佟博二人指出,《全蜀藝文志》與現存吳枚庵藏明刻本《成都文類》中選錄的杜詩有異文出現,究其因乃《全蜀藝文志》曾從《九家集注杜詩》等書搜采,加之其使用的《成都文類》版本與吳枚庵藏本不同。[7]另外,趙認為《成都文類》收錄的杜甫草堂詩多為實寫,且具詞體特質,給后世詞壇及南宋詠物詞以深刻影響。[8]此外,趙、佟二人在《中的杜甫草堂》一文中認為《成都文類》中杜甫的草堂詩是杜甫草堂的營建史,也是杜甫客居草堂的生活實錄。[9]以上三篇論文,給學界研究杜甫在成都居留期間的生活、思想等方面提供了的寶貴的資料和更為廣闊的空間。
四、《成都文類》中收錄有關司馬相如詩文的研究
關于《成都文類》中司馬相如的研究,僅趙曉蘭《中的司馬相如》一文。趙曉蘭指出,《成都文類》收錄與司馬相如有關詩文約三十篇,其中包括司馬相如著作、漢宋間歷代評議司馬相如或憑吊其傳說的遺跡之作、歷代提及的司馬相如之作三部分。另外趙曉蘭認為司馬相如建節往使、略定西夷,對中華文明作出了歷史性貢獻。[10]上述所論較為完整、清晰地展示了漢至宋淳熙年間文人們對司馬相如的認識及其對西南地區的歷史性貢獻。
司馬相如作為蜀中第一位大才子,對眾多蜀人及入蜀文人有著極大的影響。《成都文類》中所錄關于司馬相如的詩文高達四十首,內容十分豐富。而上述所論及漢宋間歷代文人對司馬相如的評價部分,似乎只是例舉了《成都文類》中的部分詩文,對其進行了羅列總結,并未對其內容進行深入分析。如關于司馬相如于駟馬橋入朝之事,在《成都文類》中便有范鎮《升遷》、京鏜《駟馬橋記》、宋祁《司馬相如琴臺》、京鏜《水調歌頭并序》諸篇詩文提及。關于司馬相如于駟馬橋入朝之事,《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載:“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11]又《華陽國志》卷二載:“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12]筆者認為,題柱駟馬橋之事,廣被文人們所提及,應當值得我們重視。
五、《成都文類》對后世影響的研究
《成都文類》的出現,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永《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東塘集提要》云:“深有表彰文獻之功”[4]。關于《成都文類》對后世影響的研究有以下成果:
第一,利用《成都文類》所載詩文考察某地理位置。如易立在《衡山鎮、均窯鎮與琉璃廠窯》一文,以《成都文類》所載田《丞相張公祠堂銘》、何麒《外大父丞相初登科為雒縣主簿經攝窯鎮稅官》二文為引線,通過考查華陽縣的轄境、中晚唐以后成都經濟重心的東移、琉璃廠大量窯廠、窯跡的遺存以及當地土層結構,認為衡山鎮、均窯鎮的地理位置,乃成都市東南部府河東岸的琉璃廠可能性為大。[13]第二,利用《成都文類》所錄詩文輯佚。如吳宗海《中的佚詩》一文輯佚田望《暑雪軒》《和合江亭》、房偉《訪古》、楊甲《合江泛舟》等詩[14]。對學界進一步研究《全宋詩》有指導意義。第三,對《成都文類》的總體評價。如畢庶春《廣L博采 精校存真――讀趙曉蘭教授的整理本》從趙曉蘭教授整理的《成都文類》的《序言》《后記》《附記》指出了該書保存了古本風貌,具有巨大的文獻價值、學術價值。[15]吳洪澤《的編纂得失與整理價值》一文在評價《成都文類》時引傅增湘先生語“蜀文總集,今所傳者莫先于扈仲榮等所編之《成都文類》,其書最稱罕秘。”[16]
上述所論清晰地展現了《成都文類》對后世的影響,或用其所錄詩文確定具體的地理位置,或以其所錄詩文訂補后世文集、詩集,如《全宋詩》的訂補。然以上相關研究均存在些許的不足,并未廣泛地研究《成都文類》對后世詩集、文集的編輯的影響。另外,后世各種詩集文集單行本中未見詩文,僅見于《成都文類》的研究似乎也被學界所忽視。此外,王文才《成都城坊考》(下)、詹子林《宋朝成都文化地理專題研究》二文對《成都文類》所錄田況《成都邀樂》等詩涉成都地區游宴情況及風俗進行了探討。
總之,學界對袁說友《成都文類》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這不僅體現在對《成都文類》漏收、誤收情況的研究;同時還體現在對其編輯者袁說友及其對后世的影響的研究等方面,這與不同時代人們的審美思想、倫理觀念、價值判斷等多種因素有關。對于《成都文類》的研究,大致就是這樣的情況,雖然有不足之處,但是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成都文類》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對《成都文類》的研究,或因版本流傳、散佚,學界起步較晚,但是對該書的研究是我們研究巴蜀文學與文化不容忽視的課題,如《成都文類》所錄詩文中有關蜀中教育的詩文,可以為我們清晰地展示漢至南宋淳熙年間蜀中文化的發展脈絡。又如《成都文類》共五十卷,其中所錄“記”便高達22卷,帶給我們很多的思考。再如《成都文類》涉及蜀中山川、風土、人情的詩文,可補史之缺對我們了解漢至南宋淳熙年間蜀中民俗民情,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此外,《成都文類》中所錄涉及成都歷代沿革的詩文同樣值得我們重視。
注釋:
[1]房銳:《雍陶寓居云南說辨析》,社會科學家,2005年,第4期。
[2]趙曉蘭:《花蕊夫人考辨》,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3]趙曉蘭,佟博:《所載庾闡考辨》,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4]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374頁。
[5]羅超華:《論袁說友在蜀中的詩歌創作》,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7期。
[6]李小麗:《袁說友易學思想初探》,黑龍江史志,2010年,第13期。
[7]趙曉蘭,佟博:《與中的杜詩》,杜甫研究學刊,2012年,第2期。
[8]趙曉蘭:《子美集開詩世界――試論中杜甫草堂詩的詞體特質》,杜甫研究學刊,2006年,第1期。
[9]趙曉蘭,佟博:《中的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3期。
[10]趙曉蘭:《中的司馬相如》,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11]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002頁。
[12]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頁。
[13]易立:《衡山鎮、均窯鎮與琉璃廠窯》,邊疆考古研究,2013年,第00期。
[14]吳宗海:《中的佚詩》,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第1期。
篇7
任何一種地域性的文學通史,其能否成功建構,都有一個前提,即需要確認:在此特定區域空間范圍內是否存在相對獨特且穿古今的文學演變的過程。這種過程的獨特性(與其他區域的區別度)的大小從根本上決定了此種文學史建構的意義大小。因此,文學通史之“通”,主要不是指對相關文學現象全方位無死角的搜羅(這事實上幾乎是不可能的,盡管對于較小地域范圍的文學通史來說需要做到盡可能全面),而是指對此演變過程之基本環節和線索的完整建構和書寫。同理,四川文學通史之所以有可能成其為“通史”,并不僅僅因為在四川這個區域范圍內自古而今可以羅列出大量文學現象,而是因為這些文學現象客觀上構成了相對獨特甚至自成一系的演變進程,雖然這一進程也一直處于與其他區域文學的交互影響之中。那么,四川文學之演進的相對獨特性,可以向上追溯到何時呢?已有的書寫實踐,如楊世民先生的《巴蜀文學史》和譚興國先生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學史稿》,都一致地追溯到先秦時期。但這并非不證自明的事情。為什么有必要追溯到先秦時期?先秦時期四川文學的書寫可能面臨哪些理論和技術上的問題?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一、 神話與文學的關系再辨
將四川文學通史上溯到先秦時期,前提條件自然是先秦時期巴蜀地區存在以書面或口頭的文本形態流傳后世的文學現象。顯然,符合此條件的主要是神話傳說。①毋庸諱言,學界將“先秦巴蜀文學”當作不證自明的存在,正是因為先秦巴蜀地區的確曾出現過相對而言數量比較可觀且頗具獨特文化品格的神話傳說。在已有的書寫實踐中,也正是巴蜀上古神話傳說填充了先秦時期巴蜀文學的空檔。這樣一來,很容易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即談論神話就是談論文學。認為神話是文學的一個分支,或者說是文學文體的一種,這種觀念在國內學界由來已久。上世紀初,等已經將神話與歌謠等一起劃歸“平民文學”、“民間文學”。1980年出版的鐘敬文主編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民間文學概論》更直截了當地將神話界定為民間文學的一種形式。②著名神話學家袁珂的“廣義神話論”也主張“神話的本質,始終在于文學,在于富有積極浪漫主義精神的文學”。〔1〕
但近年來,這種觀念開始引起學界的檢討。有學者指出:“中國神話學研究忽視‘神話’與‘文學’的區分,形成以文學為本位的神話觀,使其無法在神話理論上有所突破。”〔2〕還有學者從學術和文化史上追根溯源,認為“中國神話學逐漸從屬于文學研究”,與晚明及晚清時期吸納西學的機制有關,即外來的“神話”“既無法對應中國的‘天’之內容”,“也無法抵達‘格物窮理之大原本’,它只能有啟迪民心的教育之用,歸屬于西學分類的最末等級‘文學’”。〔3〕言外之意,就學理本身而言,神話研究之從屬于文學研究并非天然正確,反而是思想史的一種遮蔽。
這種檢討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所謂神話研究的“文學化”存在研究理論與研究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例如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影響甚大的“古史辨”派有很多神話方面的研究,但他們的主要目的只是將已經被歷史化的神話(主要是帝王天命神話,以及一些民間傳說)重新還原為神話,即不再視之為可信的歷史。換句話說,他們雖然將神話傳說歸入“民間文學”,但總體上說還沒有對神話進行真正的“文學”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決定了他們的研究仍屬于史學范疇。在當前的學科建制下,雖然從事神話研究的學者大多集中在文學系,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當代中國神話研究的主流就是文學研究。事實上,當代中國神話研究的主流是在批判性吸收“古史辨”派研究成果基礎上對上古神話進行的文化學研究。此類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人類學理論為指導的實證、考據式研究。其基本理念是,上古神話雖然并非信史,但包含著古人精神、信仰、觀念衍變的線索,同時曲折反映了上古時代社會、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人類歷史,此外,神話在其誕生時代本身也具有尚未得到當代學術充分認識的功能。因此,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試圖通過對上古神話的解析,來更加全面地建構古代史的歷史文化語境,這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古史辨”派的否定之否定。而對神話的“文學”研究實踐倒是頗為邊緣化的,而且很多其實尚停留在對其合理性的論證層面,以及對神話傳說的普及、介紹方面。③這說明,當代以來中國神話研究的多學科屬性至少在研究實踐上并沒有受到“神話從屬于文學”的觀念的太多干擾。而在理念方面,即使是明確主張神話本質在于文學的袁珂先生也并不否認神話研究多學科屬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④
上述對于將神話研究“文學化”的檢討,從四川文學通史書寫的角度來說,倒是有這樣一個啟示作用,即確實不能將談論神話簡單地等同于談論文學,并非所有關于先秦巴蜀神話的研究成果都直接地有助于四川文學通史的建構(盡管有間接的助益),或者都有必要被吸收進文學通史的文本之中。雖然文學史同樣屬于史學范疇,四川文學史先秦部分的書寫同樣必須有助于更加完整和客觀地建構古代史的歷史文化語境,但文學史畢竟有自己的側重點,它的首要任務是清晰梳理文學自身的發展軌跡,而這種梳理自然要以對不同歷史時期文學作品的“文學性”的研究為基礎(雖然也有必要選擇性地包含對文學現象中非“文學性”因素的變化的考察),對于文學“通”史來說就更是如此,因為文學通史既要做到盡可能全面,又必須重心突出,避免成為文學現象描述的大雜燴。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史的書寫既屬于史學范疇,又是文學的研究。至于神話的“本質”是什么,是不是文學,完全是可以懸置起來的問題,只要承認神話具有文學的屬性就可以了,而這一點恰恰是學者們的基本共識。即便反對神話研究“文學化”的學者也不否認上古神話是可以從文學角度加以研究的。因此,對于四川文學通史的書寫來說,真正的問題就在于如何認識和表述上古巴蜀神話的文學屬性及其演變,以及如何認識其在整個巴蜀文學演進史上的地位。
二、上古巴蜀神話早期文學化的不足
文學通史(尤其是較小地域范圍的文學通史)的書寫,往往有一個不為人注意的誤區,即書寫者經常為了刻意營造文學演進統貫一系的表象,對于文學活動不發達時期的文學現象進行不恰當地夸大。實際上,文學演進過程有盛有衰,本是十分正常的現象,特定時期的低谷并不一定影響整體進程的統貫性。從書寫的技術上說,對于這種情況的處理,最重要的并不是去淘選相對好的作品,更不是刻意拔高衰微期的文學成就,而應是客觀描述其特點,分析其成因。四川文學的演進歷程同樣存在相對低谷的階段,如果進行橫向比較的話,元明時期四川文學的整體成就就是比較低的,而先秦時期恐怕亦不能過高估計。
上文已述,先秦巴蜀文學的主體就是神話。而即便是主張神話本質為文學的袁珂先生也指出,神話的文學屬性在總體上存在弱變化的過程,即在“原始社會前期的活物論時期”,“文學的含意深厚”,到了“萬物有靈論”時期,“文學光輝……隱而不彰”,但“神話繼續向前發展”,終于還是會“還它固有的文學的本來面貌”。〔4〕如果考慮到“活物論”時期的中國神話保存極少,在至今留存的上古巴蜀神話中也很難分辨出這一時期的神話,那么,今日可見的先秦巴蜀神話恰恰屬于“文學光輝……隱而不彰”的神話。“隱而不彰”的原因,據袁先生的說法是由于此時“各種學科和神話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尤其是和宗教緊密結合在一起)”。〔5〕當然,這還只是就神話自身演變的一般情形而言。那么,把先秦巴蜀神話放在中國上古神話的整體狀況中來橫向地看又如何呢?
我們通常說,與古希臘神話相比,中國上古神話是零星散亂的。所謂零星散亂,實際上意味著它們沒有獲得比較完滿的審美形式。這正是其文學屬性“隱而不彰”的核心表現。不過,其實古希臘神話原先未必就不是零星散亂的,它之所以能夠獲得比較完滿的審美形式,也并非神話自然而然的發展結果,而主要是靠著一批古典詩人和哲人的整理和加工。盡管具體的方式有所不同,盡管受到歷史化的影響比較嚴重,中國上古神話中的一部分仍然經過早期智識人的吸收和改造。這種吸收和改造不僅使這部分神話很早得到書面載錄,而且使其被較高程度地文學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詩經》和《楚辭》(尤其是后者)。《詩經》和《楚辭》歷來為神話學者所重視,一般來說是由于它們對神話的載錄時間較早②,因而保存了不少原生神話的痕跡。換句話說,神話學者看重的多是其文獻價值,而非其文學價值。但如果從文學史的角度看,《詩經》《楚辭》等作品對于中國上古神話作為一種“潛文學”向真正意義之文學的遞變,或者說對神話之文學屬性的發揚,就具有更突出的意義。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屈原作品中的神話,與其所吸收的神話原型相比,就體現了“神話特質的變化,神話形態和功能的變化,以及神話整個內部構成和再生機制的變化。”〔6〕今天的許多神話學者大概并不樂意看到這些變化,因為這意味著原生神話內涵的轉換、變形,他們會希望屈原像人類學家那樣盡可能原汁原味地把他所聽聞到的神話載錄下來。但在文學史研究者的眼中,這些變化就不啻是文學之幸了,因為故事情節更加條貫、圓融了,單純神異性的神話人物真正成為具有內在精神氣質和情感活力的人的形象,生命形式的變幻不再僅僅依據生命一體化的原始神話思維直接地轉形,而要接受審美理性的引導,為詩意的形象塑造和文本主題服務,人物與外界之間神秘的相互作用被人物與環境的情感性關聯所取代。〔7〕
我們知道,作為神話文獻,巴蜀神話在整個中國古神話世界中是獨具特色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被認為是“唯一可以和中原神話比肩并論的地域神話。”〔8〕但是,比較而言,上古巴蜀神話在文學化方面就明顯遜色于北方中原神話集群和荊楚神話集群。就目前所知,上古巴蜀神話在先秦時期沒有得到較好的整理和書面載錄。①古蜀國和古巴國是否擁有成熟的文字系統,在學界尚有爭議。在先秦古籍中,保存巴蜀神話較多的是《山海經》。②但一般認為《山海經》屬于“巫書”(其中《山經》是祭祀一般山川的指南,相當于民間的“封禪書”,《海經》則是周邊之國的氏族志)③,其文本本身的文學價值比較有限。當然,這里并不是說上古神話只有經過書寫才可能獲得有價值的文學形式,只不過我們實際上難以從后世各種正史、野史、方志、筆記等文獻對上古巴蜀神話的零星載錄中真切地還原其作為口耳相傳故事的原初文本形態。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者,在社會生活狀況多變的條件下,口頭文本本身在流傳過程中較容易發生變異和各種再組合;二者,書面載錄不可能完全忠實,反而往往出于各種書寫目的對口頭文本以及舊有的書面文本進行改造;三者,部分改造可能是出于文學目的,但這就導致原初口頭文本的文學性與以書面形式附益的文學性雜糅在一起。神話學的文獻考據工作或許可以還原原初口頭文本的某些意象和情節元素,卻無法真切形象地告訴我們這些故事在先民的口中具體是怎么講的,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言:“復原的只是神話內容,而不是神話的文體原貌。”〔9〕但是,從文學的角度說,其意義在理論上應落實在這或許存在過的具體講法(即完整的語言形式)之中,而不能僅僅由梗概性的描述來提供。當然,這是對原生神話進行文學研究的一種普遍性困境。
由于上古巴蜀神話沒有在先秦時期獲得比較完滿的審美形式,四川文學通史的書寫在涉及先秦部分時就可能顯得捉襟見肘,甚至采取顧左右而言它的策略。在不能不談及審美形式的時候,只能寬泛而簡單地強調神話想象的奇幻、怪誕、夸張等,主要內容則可能以文獻的整理和考據代替審美分析,或者以反映論為依據,用神話的文化內涵代替審美分析。這實質上就是上文所說的以神話學的研究代替文學的研究。在文學史的書寫中,文獻的整理和考據只能作為一種基礎性的工作,不應成為主要內容,文化內涵誠然并非與文學屬性無關,但這種相關的前提在于必須時時將其置于與文本語言形式相統一的審美整體中來考量,而通常的神話學研究思路是將神話文本當作無關審美形式的文化標本來解析其文化內涵。在這種情況下,神話文本的語言形式表面上仍然存在,實質上卻處于被肢解、被遮蔽的狀態。
從四川文學通史書寫的角度看,上古巴蜀神話在先秦時期文學化程度較低,還直接影響了地域文學演進的統貫性,也就是說,在以神話傳說為主要內容的巴蜀先秦文學與巴蜀漢代文學之間存在一定的斷裂。眾所周知,漢代是巴蜀文學的第一座高峰,出現了以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為代表的文學大家。但是漢代興起的巴蜀辭賦并沒有從先秦時期的巴蜀神話那里得到太多的滋養,反而主要是接續和發展了《詩經》《楚辭》以來的文學傳統。學界通常將這種斷裂的原因歸之于外在的政治和文化變遷,即秦征服蜀國、巴國后,“通過派遣官員、移民、帶領巴蜀子弟出征等多種途徑,使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合流”〔10〕,到了西漢,文翁興學,教化普及,中原儒家文化更是成為巴蜀地區文化主流。這對于巴蜀文化來說,“既是一次提升也必然有所丟失。神話傳說的壓抑,便是丟失的一種。”〔11〕這種分析從宏觀的大背景著眼,固然不無道理,但如果從文學自身發展的角度來看,審美形式不完善才是更為直接的原因。比^而言,楚國同樣為秦所滅,秦漢時期,楚文化同樣與中原文化合流,但《楚辭》《莊子》等代表荊楚文化和文學成就且吸納、融合了大量荊楚神話元素的作品在新的主流文化話語系統中占據了突出的地位,從而不僅使先秦楚文學能夠在更大的地域范圍內發揮巨大影響力,同時也使楚地文學保持了更好的地域延續性。而上古巴蜀神話由于文學化程度較低,在新的主流文學話語中自然就處于被壓抑、被邊緣化的狀態,無法在后來的巴蜀文學發展中起到更直接的作用。
至于上古巴蜀神話為什么文學化程度較低,根本原因恐怕要從政治體制對文化和文學的影響去尋求。簡單來說,一者,古蜀國、古巴國那種宗教巫術氛圍濃厚的神權政體限制了文學審美的自覺和文學精英的產生。二者,古蜀國、古巴國為秦所滅的時間雖然較早(在前316年,此時距離秦的統一尚有近百年時間),但秦以法家思想為政治意識形態,實行以耕戰政策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對于強兵很有效,卻十分不利于精神文化土壤的培育。因此,巴蜀之地在秦統治的百余年間,雖然擺脫了舊有的神權政體,雖然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一些層面,但仍然不能產生能夠將神話高度文學化的文化精英。譚興國先生在其所著《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學史稿》中曾感慨:“如果天降荷馬于巴蜀大地,對這些神話傳說加以小說化的整理,未必不能產生偉大的史詩。”〔12〕這個感慨道出了阻礙巴蜀神話傳說文學化的關鍵問題在于缺少文學家,只是先秦時期巴蜀大地沒有出現荷馬,也沒有出現屈原,實在并非完全由偶然所致。
三、上古神話的文學史書寫路徑
盡管上古巴蜀神話存在文學化不足的問題,但對于四川文學通史的建構來說,它仍是繞不過去的部分。既然我們承認上古神話(尤其是上古原生神話)也有其固有的文學屬性,即便沒有經過文化精英的審美熔鑄,它也仍然可以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樣態。那么應該如何把握上古神話(以及上古巴蜀神話)的文學史位置并將其呈現在地域文學史的書寫實踐之中?本文認為大體可從以下幾個步驟著手:
首先,要完善神話譜系的還原和整理工作。目前學界對上古神話的梳理大多還限于橫向的母題或內容分類,如上古巴蜀神話按母題可分為大石母題神話、治水母題神話、蠶神母題神話等,按內容性質可分為自然神話、英雄神話、起源神話等。但是,縱向的梳理還有所不足。巴蜀神話雖然以口頭形式代代相傳,但今天可以作為研究資料的主要還是歷代載錄的書面形態文本,這些文本中的很多神話故事表面上都以上古為時代背景,但實際上夾雜了大量在后世神話思想和各種其他機緣引導下進行的改造。因此,有必要借助現代神話學理論和考證手段對歷代文獻所載錄的神話作盡可能準確的年代還原,梳理衍變的軌跡,辨識出上古巴蜀神話的概貌,以便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比較可靠的文本基礎。舉例而言,巴蜀神話中有一個著名的五丁神話,其故事見載于多種古籍且情節版本各有不同。據李誠先生研究,通過對這些不同版本的分析,可以勾勒出五丁神話故事在歷史上復雜的衍化過程,但這個故事最基本、最原始的內容就是大力神移蜀山、立巨石。此后由于某種機緣,這個神話與產生于另一地的石牛神話結合起來,初步形成了五丁以石牛開路的神話情節。再后來,五女故事以及由其衍化出來的蜀妃故事也在流傳過程中加入到這個神話之中。〔13〕這樣就在將該神話歷史化的同時賦予其某種政治道德的意涵,但這些附益恐怕是秦滅亡以后的事情了。
第二,揭示上古神話的“意態結構”。由于上古原生神話的文體形式幾乎是一個無法討論的領域,因此,如何進行美學分析就成為文學史書寫需要面對的關鍵性困難。在這個問題上,石昌渝先生的觀點是頗有啟發的。他認為神話對中國小說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意態結構方面”,它指的是“情節構思間架”。例如在《山海經?大荒北經》所載黃帝與蚩尤爭斗的神話故事中,黃帝代表正義賢君,蚩尤代表邪惡叛逆,兩方各顯神通,前者先失敗,后請來天女作幫手,終于反敗為勝。“這個情節定型為一種意態結構模式,為后世小說反復采用。” 〔14〕本文認為,對這種“意態結構”的分析總體上可視為對中國神話本體的美學層面的分析。雖然這個概念是從中國神話影響敘事文學的角度提出的,但我們說神話有其固有的文學屬性,根本依據恰恰在于神話的敘事性。雖然漢學家浦安迪有一個頗有見地的說法:“希臘神話以時間為軸心,故重過程而善于講故事;中國神話以空間為宗旨,故重本體而善于畫圖案。” 〔15〕但這只是相對而言。無論是希臘神話,還是中國神話,骨子里都是敘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用“神話”這個似乎可類比“話體”文學的詞來對應西文mythology并無根本的不當。
神話的“意態結構”應該是一個值得深入挖掘的課題。程金城先生在討論中國神話與中國敘事文學原型生成的關系時對此有進一步的發揮。他從卡西爾的神話理論中得到啟發,認為神話的感性結構、概念結構以及神話思維方式是探討上述關系的基本維度,而這些維度其實可以視為對“意態結構”之結構的深入闡釋。“神話的感性結構”大體是指神話所體現出的感知外界宇宙世界的“觀相學”方式,如中國神話與地理、博物的特殊關系,如神祗形象的獨特性等,都與此感性結構有關。神話的概念結構則是指從神話中抽象出來的“對萬物的追問及其包含的哲理”,其在中國神話中主要表現為遠古祖先的各種觀念和精神,如超越自然束縛、呼喚超人力量的精神,如關于方位、四季、地獄等的觀念。后來,隨著神話歷史化的演變,世俗化、道德化的理性意識也進入到這種概念結構之中。神話思維方式則是規定上述感性結構、概念結構的前提。〔16〕上古巴蜀神話在意態結構上與中國其他上古神話集群既有共性,也有差異性。盡管內在的同源關系決定了共性是主導方面,但對于地域文學史的建構而言,最核心的工作應該是分析和描述差異性,突出巴蜀神話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并非沒有因由,其根源在于相對特殊的地理狀況、政治空間、生活方式等所造就的巴蜀先民相對特殊的思維模式和人格精神。
第三,分析和描述上古神話影響后世文學的方式和機制。神話對后世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學界討論比較多的。這種影響大體來說有兩大途徑,一是神話的母題、意象等作為素材為后世文學家所借用,這多見于詩歌,然亦不限于詩歌。借用的同時也不斷翻新其內涵。二是上文所說的“意態結構”的影響。需要注意的是,上古神話的“意態結構”不只影響后世中國小說,而且也影響到一般視為抒情文學的中國詩歌。后者其實往往也包含著敘事成分,更重要的是,這些敘事成分或因素所呈現出的僅保留骨架和神韻的特點恰與中國上古神話的形態暗自契合。魯迅說,中國神話在后世文學中只是“第用為詩文藻飾,而于小說中常見其跡象而已”〔17〕,多少是估計過低了。當然,不論是母題、意象的頻繁借用,還是“意態結構”的廣泛滲透,本質上都是上古神話所包含的上古文化精神影響后世文學的題中之義。至于四川文學通史的書寫,在這方面自然應著眼于上古巴蜀神話對后世巴蜀文學的影響,大致可以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在專論上古神話的部分,集中列舉母題、意象、意態結構在后世巴蜀文學中的呈現和演變,如有學者討論了杜宇化鵑作為一個母題和典故在古今巴蜀文學中運用和變化的軌跡。〔18〕二是在作家個案研究中討論這種影響,如李白詩與巴蜀神話的關系。
在具體的書寫實踐中,以上三個步驟(尤其是后兩個步驟)應該充分結合起來。分開來說,第一個步驟主要是前期性、基礎性的工作,第二個步驟應視為主體內容,第三個步驟可作為延伸性的論述。
〔參考文獻〕
〔1〕〔4〕〔5〕袁珂.中國神話通論〔M〕.成都:巴蜀書社,1993: 2, 1-2,28.
〔2〕w新.檢討中國神話學研究的“文學化運動”〔J〕.燕山大學學報:哲社版,2012(3): 85-90.
〔3〕譚佳. 神話為何屬于文學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學分類為起點〔J〕.百色學院學報,2013(6): 9-14..
〔6〕〔7〕何煒.論屈賦神話及其向文學的遞變〔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2):135-142.
〔8〕袁珂,岳珍.簡論巴蜀神話〔J〕.中華文化論壇,1996(3) : 35-37.
〔9〕〔14〕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M〕.北京:三聯書店,1994: 55,55.
〔10〕〔11〕〔12〕譚興國: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學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14,4,4.
〔13〕李誠.巴蜀神話傳說芻論〔M〕. 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6: 96-102.
〔15〕浦安迪.中國敘事學〔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42-43.
篇8
從1999年起至2008年,四川考古人士配合三峽搶救性考古工作,對省內宣漢縣普光鎮進化村羅家壩文化遺址進行過三次發掘清理。1999年第一次清理墓葬6座;2003年再次發掘,清理墓葬33座;2007年又清理墓葬26座。其中時代約為戰國早期的33號大墓,最為引人注目。其墓坑寬7.3米,長9米以上;雖曾遭遇盜掘,但墓坑東部仍出土銅器130余件,其中禮器有鼎、缶、簠、甗、敦、罍、壺、豆(帶蓋)、鑒、匜等,其基本組合與中原文化相似,而罕見于蜀域;兵器以戈為多(21件),另有鉞、劍、矛、刀、箭鏃等;用具有釜、鍪、尖底盒、勺、鏤空器座等;工具有鑿、削、斤、手鋸、雕刀等;飾物亦有10余件;但沒有發現樂器。許多出土器物與新都馬家大墓非常相近。30多件陶器中有7件為彩繪。陶器中有尖底盞、花邊口圜底罐、缽、網墜等。根據此墓規格和出土器物情況,其并非一般貴族墓葬,應該是開明王朝時期的巴地王侯陵墓。
宣漢羅家壩遺址前后出土巴蜀銅印6件。在第二次發掘中,12號墓出土的蝴蝶形印章,蝶翅和蝶身都刻畫精美,是國內唯一的特殊印章形式,但印文銹蝕不能辨認。10號墓墓主為女性,出土圓形青銅印章,印文為漢字“王”與火焰形和蝌蚪形符號所組成,當是巴賨貴族。21號墓墓主應是武士,出土一件較薄的青銅印章,印文不可辨認。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在王侯一級的33號墓坑中,墓主骨架腰部發現一件青銅圓印,直徑約8厘米,印文經處理后相當清晰,因做工精細,被譽為最完整的巴王印章(圖二)。
新都蜀王璽印解讀
新都馬家大墓出土的方形璽印,上面刻有巴蜀特有的圖像文字(圖一)。印文可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由三個文字所組成。中心是張開的鎧甲圖像,頂上有頭盔,甲衣由25塊鎧甲片聯綴而成,是為一字。鎧甲圖像的左右兩邊,各有一牙璋圖像,右側圖像略有蝕壞,這是相同的兩個字。過去多將這種牙璋圖像解釋成“鐸”。雖然圖像的外表有突起的乳丁,與鐸相似,但中間應有鈴舌,執柄才能搖響;而且其放置方式,應該是大口朝下,方能穩定。但該圖形象是大口朝上,與鐸不合。印文下半部分也由三個文字組成,主體是兩個光頭人呈攜手狀,成為一字;而攜手之處的“三星玉版”,又是一字。下面的空處,刻有一帶蓋的罍,也是一個文字。
印文中的鎧甲圖像,顯然意在強調武力保衛,故可讀“武”。這個字應是開明王朝標志性徽記,象形氣息甚濃。對比一下大墓中出土的5件成組器物上,多刻有一種徽記文字,類似古漢字“”形;整體上看,好像宮廷洞門前面的柵欄,又像是具有左右兩根立柱的牌坊,與后面宮門互相套疊。筆者發現,這個徽記應該是印文鎧甲圖像的符號化,實為一字。其下角有一小方塊,中有斜線。筆者曾撰文論證過,這一合文應即“開明”二字。在唐宋有不少集錄古文奇字的書籍,如唐崔希裕《纂古》一書,曾收錄“古文”一字,字形就是“”,宋人轉錄時定為“明”字;筆者疑此字本是“開明”合文里的“開”字,唐人熟知,在宋人轉錄時漏掉“開”的部分,卻把“明”字的隸定結果保留下來了。宋代郭忠恕《汗簡》曾經征引古文七十一家,其中古文“日”字,是方塊形中間一根折線,或許就是那個“明”字的省文。
印文中牙璋圖像,清代吳大澂《古玉圖考》中根據《周禮·春官·大宗伯·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說,定為一種調動軍隊的信物,后來轉化為祭祀禮器。《三代吉金文存》編號“6·20享父乙簋”與“2·40作父癸鼎”銘文里均有類似的圖像文字。今人鄭魁英《話說牙璋》(《收藏》2005第11期)認為,考古界稱這種器物為“刀形端刃器”,推測由原始社會晚期的耒耜演變而來,體形狹長,柄部為長方形,刃部一般寬于柄部,有齒牙,或有欄,一般有穿孔;刃部有內凹圓弧形、內凹“V”字形和戈形帶叉形等。正確持法應是柄部朝下,刃部朝上,是祭祀農耕的禮器。三星堆1號坑出土30余件,2號坑出土20余件;大陸境外出土者,有香港大嶼山東灣1件,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1件,越南4件。香港南丫島大灣牙璋的形制比偃師二里頭到鄭州二里崗的牙璋都要晚,與廣漢三星堆的玉(石)牙璋(圖三)比較接近。最近,在越南富壽省的馮原文化遺址發掘出與三星堆一樣的牙璋。不過,也有學者根據良渚文化獸骨加工的合符,發現上面有刃有齒,認為就是牙璋的原型,故不排除牙璋是一種信物的推測。馬家陵墓璽印上的牙璋圖像,與鎧甲挨在一起,因此無法回避軍事上合符取信之義,可將這兩個牙璋文皆讀為“信”,表示開明王朝璽印的功能,是取信于民。
印文下半二人交握圖像,筆者以為是望、叢二帝政權和平交接的象征。《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皆言荊人鱉靈至蜀時,正值古蜀國洪澇災害十分嚴重的階段。鱉靈將水患制平,使蜀民安居樂業,獲得了民眾的愛戴。末代望帝隨即將王位禪讓給鱉靈,后者遂建開明王朝,自稱叢帝。現今郫縣還有望叢祠,內有二帝陵園,證明這種特殊的改朝換代形式,是以和諧穩定為主。由于政權是和平過渡,應當對這種和諧的大局廣為宣傳,所以開明時期的印章文字上,經常出現兩個漢字“王”并列現象——這在中原各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思維里,是決不允許的。印章文字中還有兩個蝌蚪圖像并列的字,應是兩個“王”字并列的簡化版,筆者已考證其為“仁”字,即推己及人之義。馬家王印上的二人交握,就是這個“仁”字的圖像化,也是對望叢二帝政權和平移交的肯定。
印文中心“三星玉版”圖像,按照古代星野學說,蜀地所對應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井宿(西方稱為雙子座),八星聚集如井,又名東井。其中比較明顯的三顆星,大致呈寶蓋形,可能就是對三星玉版的描繪。這一“三星”圖像文字,顯然有古代帝王常說的“奉天承運”之意,似可讀為“御”,表示璽印是君王所用。20世紀80年代成都沙河附近征集到一件方形銅印(圖四),印文相當特殊:全文10字,分為左右兩半,兩邊文字基本相同,但位置相互顛倒;似乎是按左上到右下的對角線方向,彼此對稱。印文由三星玉版、“心手文”、光人頭和居于中心的人體(或尸體) 5種組成。馬家大印上的“三星玉版”,是望、叢二帝友好聯合的結果,此印左上方即有此文,首先把政治大義揭出。左下接著就是兵器上常見的手臂形文和蝌蚪形文,具有后來所說的“盡忠報國”的意思。三星玉版的右邊是一橫置的光頭,似指前代望帝;光頭下面的人體輪廓線,相對的是類似篆文“大”字的人體形,居于印文的中心部分,或指傳說中浮江而上的鱉靈,即開明叢帝。這一璽印,可作馬家王印文義的補充。
馬家大印下面罍的圖像,是蜀人祭祀時常用的禮器,可讀為“禮”。這種罍形文,在其他地區印章里也能見到。如1981年蒲江縣東北公社一大隊六隊戰國墓出土一件方形銅印,上有5個禮器圖像的文字,從右至左為圓璧、方璧、圭、鐸、罍,都是禮器,推想是印主佩戴在身上的辟邪物。1992年什邡市城西絲綢廠戰國船棺墓所出方形銅印,印文為巴蜀文字,印背上卻刻有“十方王”4個漢字。其印文下半部分,左為罍的圖像 ,右為牙璋圖像,中間被一S形弧線隔開,與馬家王印的表現如出一轍。
總之,馬家王印包含的信息極其豐富,可以定為開明蜀王的璽印。印文中有開明徽記與政權象征,并有開明王朝大力提倡的主題語言“武、信、仁、禮”,其中囊括了政治信念、社會倫理、生活行為、人生哲理諸多方面的內涵。
宣漢巴王璽印解讀
宣漢羅家壩33號大墓出土的圓形銅印,現在尚無專門的研究報告公布,故僅能就個人認識談一些看法。此印為陽刻印文,上有13個巴蜀圖像文字(圖二)。中心部分自上而下直行5個字,頂上是一個“三星”圖像,與馬家王印三星玉版異曲同工,應是代表蜀地星野對應的井宿,有“奉天承運”之義。其下為一月牙形圖像,但中間有尖。筆者根據其他蜀印上與此相同的文字,常有與“王”字組合的現象,得知此文有子孫昌盛之意。其下又有銀錠形圖像文字,是表示社會穩定的意思。再下面是四個圓點包圍著的門形圖像,四點包圍相當于中原邦國名稱被方框包圍一樣,應是對國家徽記的尊重。這一門形圖像文字,在馬家大墓出土的成組器物上,皆有同樣的徽記,應是開明王朝標志。只不過宣漢大印上筆劃更加整齊,上下皆有橫劃,橫劃中間實際上是鎧甲圖像,與馬家王印略有不同的只是鎧甲的兩袖呈下垂狀而已。如果將此字看做平頂房屋,則兩側的立柱呈懸空狀,這在建筑上是不可行的。此文下面是一個十芒太陽圖像,顯然代表光明,故可讀“明”,那么這一鎧甲形文字就可以讀“開”了。這一直行印文5字,可讀為御、孫、定、開明。
中心一行的兩邊,最明顯的是左右各有一長兵器戈戟插在墩座上的圖像,表示武力保衛,故均可讀“武”。今人或將這一圖像視為樹木,這一推測須視鎧甲圖像為房屋方合;若房屋被否定,則與鎧甲相配者就應是戈戟了。在這一戈戟圖像的上下,各有一個相同的文字,左邊戈戟上下各有一個“十”字。這個字是蜀域中小的邦國名稱,今什邡市城關鎮就出土有“十方王印”,邦國舊稱為“方”,那里的小邦國即名為“十方”。現在宣漢此印證明“十方”的范圍比較寬廣,一直到川東北皆有此稱。印文右邊戈戟上下皆有一蝌蚪形文,此文成都沙河方印上已有(參見圖四)。筆者曾按《山海經》中半魚半蛇的“魚婦”形象,推測此文與古蜀王魚鳧有關,則此文應屬族徽,或指魚族,故知此印印主既是十方王族,又是魚族后裔。由于久已臣服開明王朝,故“開明”徽記大而居中,印主徽記則小而不顯眼,以示謙卑。中心行的兩邊,共有6個文字,兩個表“武”,4個表族。
在印文的左側,還有一個“丁”字形符號,似為一種短兵器,暫讀為“干”;右側有兩個蝌蚪形連體符號,在巴縣冬筍壩50號墓出土的長方形印章中,即有此字存在。由于又出土兩件同樣規格的漢字印章,與此字對應者為“仁”,故大印印文亦當為“仁”。這左右兩側的小字“干”和“仁”,標志著一武一文,應該是印主所持有的行為理念。
推測自稱十方王族的印主,應為開明蜀王直系,在巴地坐鎮,此印即其璽印。拿它與新都蜀王璽印對比,在地域性政治表現上明顯存在一定變化:新都印文上有禮器璋罍及兩人牽手圖像,呈現一種和諧景象;而此印文字的主體內容雖與之相同,但所強調的是干戈和穩定,可見巴地宣漢與開明王朝中心的新都,相互關系趨向嚴峻。
簡單的結語
在巴蜀政治核心地帶發現的這兩座王陵,首先補充了文獻記載之不足,對于《蜀王本紀》所謂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是一種澄清。開明王朝是既有文字,也有禮樂的時代。馬家蜀王印顯然是早期產物,雖在開明五至九世墓中出土,但不排除璽印刻于開明初世,成為王室的傳家寶。上面的文字以圖像式為主,以后才逐漸過渡到符號化。從墓中成組器物上的刻符可見,那時圖像文字正在向符號文字邁進。馬家大墓出土系列禮器,還有編鐘,已是王朝禮樂盛行的證明。這種禮樂文明的發展,必然有過去的基礎。這就是說,開明以前的杜宇王朝其實已有禮樂制度,并非從開明王朝才開始興起。
其次,印章的功能與社會變革有關。戰國時期,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貨物交換和貿易往來,在經濟行為方面需要一種作為憑證的信物,那就是璽印。《周禮·地官·司市》稱“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掌節》又言“貨賄用璽節”。按《周禮》規定,貨物流通,必須持有璽節作為出關入市的證明;官府征收賦稅時,也要利用璽印作為憑證。同時,王侯官吏行使職權時也須有璽印,代表權威。由此,研究者將印章功能歸納成三方面:一是誠信作用,二是標志作用,三是祝警作用。古璽印有紐有孔,可以穿綬系在腰間,隨身佩帶,顯示身份,則是標志作用。有些印文帶有吉祥幸福的內容,佩戴可起祈祥壓邪的作用,相當于護身符。有些印文屬于一種勵志箴言,隨時看到它,可起警示作用。巴蜀王侯璽印的具體功能,亦不過如此。新都、宣漢兩件璽印,一方面屬于巴蜀王侯隨身佩戴之物,表示開明王族身份;一方面顯示執政理念,既有武力后盾,又有禮信倫理,作為治世的基本準則;一方面還重視仁道,提倡和諧,作為哲理上的指導方針。戰國時期中原百家爭鳴,道儒墨法各家學說四面開花,可能會影響到巴蜀地域。印文中顯示的一些思想,如禪讓就是儒家鼓吹的王道理想,仁道和諧社會也是儒家不斷的追求。
篇9
間或對面有人過來看到他,總會喊一聲:“王老師好。”院里沒人不認得這位重慶文物修復發展史的見證人和參與者。
王海闊看著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歲月……
窺門:拔劍四顧心茫然
1981年8月的一個清晨,知了的聒噪早早開張。
趁著氣溫還沒上去,王海闊騎了哥哥的嘉陵摩托車,一路疾馳。
穿過逼仄的盤山小道,摩托車在重慶市中區(現渝中區)枇杷山正街72號前停下來。
高大的建筑院落門前赫然掛著一塊牌匾――“重慶市博物館”(現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
青年的新潮和博物館里的沉靜格格不入。
“這將是我開啟新事業的地方。”28歲的王海闊帶著滿臉自信,在博物館工作人員異樣眼光的注視下,昂首邁進了博物館的大門。
要說專業,王海闊的確不是科班出身,他是以工人身份進入重慶市博物館的。
但王海闊很有底氣,畢竟他此前在重慶市北碚玻璃模具廠當了九年模具雕刻鉗工,甚至還帶出了幾個徒弟。
“青銅器再神秘,也屬于金屬大類,做活離不開鉗工的鏨、銼、鋸、磨等功夫,只不過我原來做的是鑄鐵模具而已。”王海闊心想。
報到完畢,王海闊有些志得意滿地來到陳列部的文物修復室。推門一看,里面只有兩個人。
“我們這兒終于又進人了。”比王海闊小四歲的姚志新,顯然很歡迎他的到來。師父蔡長信有些不茍言笑,他放下手頭修復的器物,給王海闊講起了文物修復工作的性質和要求。
王海闊敏銳地察覺到,這可能是個不太受重視的冷清之地。
王海闊從工廠帶來一個習慣,每做一件東西,就記錄在專門的小本子上。
不過,到博物館三個月了,他新買的小本子上卻記得很少。
想想,被陳列部叫去幫忙搬文物布展的次數倒是比修復文物的次數還多。
“什么時候能做點有分量的東西?”收起小本子,王海闊有些沮喪。
其時,重慶并沒有多少重大的文物發現。不想干等,王海闊覺得自己也許還能做些什么。
明志:長風破浪會有時
1982年初,王海闊成了博物館圖書室的常客。
“又來看書啊?”圖書管理員親切地跟他打招呼。
“您早,我想問一下這本書有么?”王海闊指著書單上的書名問道。
“有,就在那個架子的第二排。”管理員查了查書卡,用手指去……
“哎,還是不行。”王海闊合上書,心里犯起了嘀咕,“咱們這個行當的書真少。”
這不是王海闊第一次失望。
之前他到處請教別人,好不容易搜集了一些跟文物修復相關的書,但卻發現這些書里只有一些零散的文物修復知識。
想當初,自己離開工廠時隨身帶走的那本售價八毛五分錢的《鉗工》,系統地梳理出了鉗工所需的知R技能,怎么文物修復技術反而沒有專門成體系的指導教材呢?
王海闊暗暗立志,將來一定要通過自己的文物修復實踐,寫一本像《鉗工》那樣的關于文物修復的專業教材。
1982年11月,重慶市交電公司在市中區(現渝中區)臨江支路進行基建施工時,現場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青銅器。
殘破的青銅器碎片被送進重慶市博物館的文物修復室。
王海闊眼睛都看直了,心里很是興奮,這不正是自己一直等的那陣東風么?
這批從西漢墓群出土的青銅器,因為氣候土壤等原因,銹蝕破損嚴重,沒了銅胎,無法以傳統的錫焊法完成修復,只能通過創新修復技術來修復。
此前,師父蔡長信也看中了四川美術學院用來復制泥塑版本《收租院》的玻璃鋼成型技術,便想到將其應用到文物修復中。
面對破爛成渣一樣的青銅器碎片,師徒三人卻像看到了寶貝。
不久后,這批青銅器修復完成。
王海闊將應用新材料技術修復文物的過程作了總結,并撰寫文章,投稿到《考古與文物》雜志。
“寫這有啥用?”小姚不太理解。
“這么好的技術,不應該只有我們知道。文章雖小,萬一能為今后文物修復技術學科的形成添磚加瓦,那多好。”王海闊說。
因為當時的文物專業期刊沒有為文物保護修復技術開設專欄,王海闊的文章足足排了三年的隊。
1986年,《應用玻璃鋼修復文物》一文終于發表了。
成名:一日看盡長安花
“看嘛,文物修復那群人做事拖延,一天都在耍。”
1987年,王海闊無意間聽到這樣的非議,心中有些憤懣。
怎么反擊?王海闊想起了王川平館長說的一件事――巴蜀金銀錯犀牛帶鉤因展廳陳列安全條件受限,無法展現給觀眾。
于是,王海闊主動找到館長:“館長,巴蜀金銀錯犀牛帶鉤交給我來復制吧。”
巴蜀金銀錯犀牛帶鉤是國家一級文物,造型紋飾極其精美,幾乎代表了戰國時期巴蜀青銅器的最高技藝。
“業內很少有人能做這么精細的金屬鏨刻,這點我在行。”王海闊“大言不慚”。
話是這么說,畢竟是極其珍貴的文物,復制過程中容不得半點閃失。
王海闊翻看了許多文獻資料,盡量還原出這件文物最初的制作過程,最終提交方案,決定采用失蠟法、鏤刻、鑲嵌等傳統制作工藝,對文物進行原汁原味的復制。
復制方案獲國家文物局審批通過后,王海闊立馬開始操作,他給自己預定的復制時間是一年。他不擔心自己的手藝,但對外部條件有些擔憂。
銅坯得找工廠澆鑄完成,該器最薄的地方不到兩毫米,不采用精密鑄造無法成型。
四川儀表十廠精密鑄造技術過硬,也愿意接活,這讓王海闊安下了心。
王海闊興趣濃厚,投入了大量精力,一套工藝下來,幾可亂真的復制件竟然比預期提前半年完成了。
“這算是我一生中最出彩的東西了。”王海闊摸摸復制件,有些愛不釋手。
相較于工廠的批量流水生產,文物修復全過程是以獨立的工作方式完成,這種成就感讓王海闊很是沉醉。
鞒校合欣創溝霰滔上
2017年4月,在陶瓷器修復室,90后龍杰戴著類似防毒面具的口罩,擼高了袖子,弓著腰埋著頭,拿著蘸了釉的小刷子,不停地刷在一張不到半個巴掌大的濾網上,釉料透過極其細密的濾網,均勻地涂在一件剛補了形的陶器邊沿。
“小龍是我院文物修復師承制培訓的第二批學生了,他以前在四川藝術職業學校學的就是文物修復專業。”王海闊在旁邊介紹說。
2005年,重慶市文物考古所(現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從重慶市博物館獨立出來,王海闊即將成為文化遺產研究院第一個退休的人。
但他怕院里文物修復后繼無人,技術斷代,就找到領導,請求開展師承制培訓,公開招收徒弟。
院長聽了很高興,并決定立即實行。
第一批學生來源很雜,比如孫少偉,就是王海闊從三峽考古的工地上尋來的。
孫少偉那年三十出頭,是工地上使洛陽鏟探尋墓葬遺跡的一把好手,一次協助王海闊做室內文物修復工作時,被王海闊一眼看上:“你小子挺有天賦,跟我回去學文物修復吧。”
孫少偉卻很為難,自己老大不小了,何必轉行。
“你現在在工地上是技工骨干,今后考古專業的大學生多了,就不一定了。還是跟我回去學門硬手藝吧……”
后來,孫少偉眼看著文物保護修復事業發展,心中很是慶幸自己遇到了伯樂,改變了命運。而王海闊的慧眼還不止于此。
“多虧王老師不拘一格育人才,現在我們青銅、鐵器、陶瓷都能做,但又各有擅長。”精通鐵器修復的女修復師小呂笑道。
“不要打馬虎眼,我跟你們說的技術論文寫了沒有?”王海闊問。
每隔一段時間,王海闊都要督促弟子們寫論文,進行理論總結,以提升他們的業務綜合技術能力。
篇10
師門同濟,學強張賽,皆忠義之士,情同手足;樂至四國,許都耀瓊,此皆良實,多蒙所助;蘭莉二姊,性行淑均,愛如姐弟。其他諸君,皆為志慮忠純之士,多有廣益。區區不才,有何德能,安得廣助若此?感荷之心,亦自拳拳。實驗中曾多次求教于楊(明莉)、杜(軍)二老師,受益匪淺;中心實驗室張(光輝)、鮮(曉紅)二位老師及劉姊渝萍為實驗工作大開方便之門,謹表謝忱。
家中上至期頤之祖母,中至慈愛之父母、姊姊,下至始亂之甥男,均不遺余
力以支持,融融親情,易其幸甚!謹撰此文,魚傳尺素,答報椿首!
A乎!聚散無常,盛況難再;書不盡意,略陳固陋。臨別贈言,幸承恩于魏公;登高作賦,是所望于群賢。斗膽獻拙,情之不已;一言均賦,四韻俱成。淚灑陵江,以酪逝去之歲月。
西入渝州已六霜,貌豺帳里鑄魚腸。
篇11
和所有考古遺物的研究一樣,分期是青銅器研究的一項基本工作。在分期的方法論上,應該強調把考古學類型學研究放在首位,其次再以古文字學等研究去論證和深化。前幾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關于西周青銅器的專題,就是這樣進行,取得了較好的效果①。
經過國內外很多學者的努力,中國青銅器分期的基本框架業已建立。這主要是指中原地區的青銅器而言。事實上,中國青銅器的演變是多線的,所以分期還必須同分域相結合,逐步排出各個區域不同時期的發展系列。要完成這樣的工作,自然需要長時間的投入。
青銅器分期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這里試就當前的進展情況,提出十個可能有前沿性的課題,供大家參考。
(一)中國青銅器的產生
中國學者大都認為青銅器的出現和文明起源有關,西方也有著作講到中國青銅器手工業的規模和性質使之成為文明社會的標志②。因此,探索中國青銅器產生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迄今在中國境內好多地點已有早期銅器發現,最早的如陜西臨潼姜寨的半圓形銅片,屬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這些早期銅器,品質包括紅銅、黃銅、青銅等,種類有小型工具和裝飾品。這指示我們,中國青銅器應有其自己的獨立起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魯惟一、夏含夷主編:《劍橋中國先秦史》(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
不過,目前已有的材料還不能構成青銅器產生過程的完整線索。在中國的這一過程肯定有自身的特點,需要尋找更多的依據才能確切描述。我們也不能排除其間存在境外文化影響的可能性。
(二)青銅器銘文的初始形態
一般認為青銅器銘文最先出現于商代前期,這是在將商代分為前后兩期的情況下說的。如果像近時一些學者主張的分為早中晚三期①,則銘文當始見在商代中期。
已有論著對早于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銘文進行輯錄②,其中有些器物的年代、銘文的真偽尚有爭議③。例如山東桓臺史家出土的一件觚,有銘文8字:“戍寧(予)無壽(儔),作祖戊彝”,有學者主張較早,已有論文指出形制與鄭州白家莊的觚有異④,我認為應列于商代晚期后段。
商代中期的一些銘文,有些近似陶器刻劃符號或者花紋,顯然和后來的銘文有所區別。例如國家博物館所藏傳出鄭州楊莊的鬲,銘文或釋為“亙”、“耳”等,都未必準確;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的饕餮紋錐足鼎,雙耳下口沿上各有陽文一字,勉強可釋為“冃”⑤。這類銘文的性質,特別值得探討。
(三)商末青銅器
以殷墟出土品為代表的商代晚期青銅器,近幾年由于發掘材料增多,有關認識不斷深入和豐富。特別是新發現的幾座隨葬青銅器很多的墓葬,進一步開拓了大家的眼界。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90年發掘的殷墟郭家莊160號墓,依所出陶器“時代應屬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偏晚階段”,而墓內的青銅卣與1901年陜西寶雞斗雞臺發現的卣非常相似,從而提早了后者的制作年代⑥。
殷墟三、四期青銅器的特征比較明顯⑦,當前已經有條件加以綜合歸納,然后結合非發掘品一起整理研究。因為這段時期青銅器銘文增多并且加長,還可以利用古文字學研究的成果。若干銘文有歷日和周祭,或者能與甲骨文相聯系,都十分重要。過去已有學者從這樣的角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果⑧。最近陸續出現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青銅器銘文,例如國家博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
楊曉能:《古代中國的映象:紋飾、象形文字與圖象銘文》(Xiaoneng Yang,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Decor, Pictographs,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納爾遜藝術博物館,2000年,第88—91頁。
③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頁。
④ 王宇信:《山東桓臺史家“戍寧觚”的再認識及其啟示》,《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同②楊曉能書,圖179、183。
⑥ 李學勤:《郭家莊與斗雞臺》,《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3期。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300頁。
⑧ 王世民、張亞初:《殷代乙辛時期青銅容器的形制》,《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4期。
館新入藏的作冊般銅黿等等①,對推進這方面的工作殊有裨益。
(四)商至西周的荊楚青銅器
《詩·商頌》的《殷武》篇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說明商王武丁時勢力已經達到荊楚地區,與殷墟甲骨文的記載可相印證。多年來,湖北湖南出土了數量相當多,制作也非常精美的商代青銅器,但大多見于山水之際,缺乏與當時遺址的聯系。
1996—1997年在湖南望城高砂脊②,2003—2004年在湖南寧鄉黃材炭河里③,先后發現了有青銅器隨葬的墓,墓的年代被定為西周。這些青銅器,有的形制、紋飾均和中原商代晚期的類同,有的甚至有商代晚期多見的銘文,如高砂脊的“酉”鼎④,但另有一些具有可能較晚的地方性因素,如鼎的盤口形折沿和細長下端寬展的足等。無論如何,這些器物要晚于環洞庭湖一帶過去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的大多數。
商至西周的荊楚青銅器還有待系統整理,分析其演變脈絡及與中原文化的關系,與長江上游、下游文化的關系。最近已有學者的工作⑤,為此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五)周初的“月相”
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月相”,多年間是學術界反復研討爭論的問題。近期有幾種新材料出現,可能為克服這一疑難帶來新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文獻所見的“月相”詞語,要比青銅器銘文多而復雜。在《尚書》、《逸周書》和《漢書·律歷志》所引古文《尚書》等可信材料中,“月相”共有“哉生魄”、“既望”、“朏”、“旁死霸(魄)”、“既死霸(魄)”、“既旁生霸(魄)”六個,只有“既望”、“既死霸”常見于銘文。“旁死霸”在銘文里只在晉侯蘇鐘出現一次,作“方死霸”⑥。
2003年末,在陜西岐山周公廟遺址發現甲骨文,其一片上發現了一個新的“月相”:“哉死霸”⑦。最近,在新出現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銅器上,又有另一前所未見的詞語發現。這使我們不得不考慮,西周的初年歷法的“月相”與后來的“月相”或許分屬于兩個階段,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簡化和修改了。重新思索這一問題,會為認識當時歷法的變遷有所幫助。
(六)西周厲王以下青銅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于西周晚期共和。厲王在位年《周本紀》云三十七年,有人據《世家》致疑,但總不少于二十年上下。因此,厲王至幽王的西周晚期應有九十年以上,占西周整個年數三分之一。按照青銅器發展的一般情況,在這一段時間中應該有比較明顯的變化,也就是說厲王和宣王晚年與幽王的器物理應容易區別。東遷后平王在位五十一年,這一段時間青銅器又應當有較大的變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李學勤:《作冊般銅黿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1期。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縣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縣高砂脊商周遺址的發掘》,《考古》2001年第4期。
③ 向桃初、劉頌華:《寧鄉黃材西周墓發掘的主要收獲及其意義》,《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04年第1期。
④ 同②圖一三,1、圖一四,3。
⑤ 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⑥ 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8頁。
⑦ 孫慶偉:《“周公廟遺址新出甲骨座談會”紀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20期,2004年3月。
近年發掘的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和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的大量青銅器,為探討上述時期器物的演變提供了條件。例如看晉侯墓地相當厲王晚年到共和的靖侯及夫人墓 M91、92,厘侯及夫人墓M1、M2,青銅器風格同相當宣王的獻侯及夫人墓M8、M31,穆侯及夫人墓M64、M62、M63,殤叔及夫人墓M93、M102,確有較多的差異。看來進一步整理中原地區(廣義的)這個階段的青銅器是可能的,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七)長江下游青銅器的序列
關于長江下游青銅器研究的經過,曾有學者作過概述①。這一類器物的發現和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可追溯到1954年江蘇丹徒煙墩山土墩墓和1959年安徽屯溪奕棋的土墩墓。如果再上推一些,還有江蘇儀征破山口出土的器物。
有關器物的年代問題,一直存在不同意見。例如屯溪奕棋青銅器,或主張相當西周早中期,或以為應遲至春秋。還有如江浙發現的樂器大鐃,其年代的估計學者間也甚懸殊。近些年考古材料漸多,已為解決這方面的分歧準備了條件,比如關于土墩墓的分期就有很好的討論②。
吳國和越國青銅器的發現也已大為增多,其中不乏帶有銘文的。有越王名號的兵器,包括劍、戈、矛等,非常值得注意,當前需要做的,是進行類型學的整理。考慮到楚威王敗越之后,越國破散,“諸族子爭位,或為王,或為君”③,越國末年的世系可能相當復雜,有些銘文王號不一定能與文獻對應。
(八)秦國青銅器的發展歷程
西周復亡之后在其舊地上興起的秦國,文化有著與關東顯然不同的特點,這在青銅器方面也突出地表現出來。前些年,曾有論作對秦國青銅器作過綜合分析④,現在由于出現了很多新材料,有機會加以擴展和補充。
甘肅禮縣到天水一帶的西漢水流域是秦人的發祥地。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兩處秦墓葬群遭到盜掘,隨后進行了發掘清理⑤。所出青銅器,結合過去著錄的陜西寶雞太公廟等出土品,使人們看到了從兩周之際到春秋中期秦器的演進。鳳翔南指揮M1秦景公墓在春秋晚期前段,雖然舊已盜空,還有少數器物殘片可見。再往下的秦器就很豐富了。當前我們對春秋戰國秦器所能掌握的知識,比其他列國更要多些,或許只有楚國可相比肩。
戰國時期,秦屢戰屢勝,終至兼并六國,俘取甚多,所以在秦墓及窖藏中出現的部分器物實際是戰利品,不屬于秦器的系列。這與若干周初墓葬情形相同,我們研究時應當留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
② 楊楠:《江南土墩遺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史記·越世家》。參看《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253頁。
④ 陳平:《燕秦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190、210—243頁。
⑤ 祝中熹主編:《秦西垂陵區》,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九)巴蜀文字的解讀
巴蜀文化的研討,這些年來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課題。早在20世紀40年代,以成都白馬寺出土品為導線,巴蜀青銅器進入了學者的視野,但主要是戰國時代的。后來,四川彭縣竹瓦街、新繁水觀音,加上1986年廣漢三星堆的驚人發現,揭示了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當地青銅器的面貌。不過,這些與戰國的巴蜀青銅器問的連鎖,仍然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戰國時代的巴蜀青銅器(有些屬于秦滅巴蜀以后,甚至晚及漢初)不少具有特殊的文字,即巴蜀文字。這種文字多見于兵器、樂器,也在璽印和其他物品上出現,材料越來越多,從其使用位置和特點來看,其為文字也可說是無疑的。古書或說巴蜀不知文字,可能是講不知漢字,不是沒有自己的文字。
巴蜀文字的材料積累已多,有可能像瑪雅文字那樣,試用電腦技術來分析解讀。大家了解,世界上完全沒有得到解讀的古文字不多,巴蜀文字的解讀將會成為一件大事。
(十)漢初青銅器的特色
中國青銅器的著錄和研究,一般是以漢代為下限(銅鏡除外),但學者們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先秦的器物上,對于秦漢青銅器著意較少。最近有些工作,有心改變這種趨向,如《中國青銅器全集》專設了《秦漢》卷。在銘文方面,也有專門的書籍問世①。
長時期以來,西漢早期青銅器容易與戰國晚期的器物互相混淆,這可能是因為漢初戰國時流行的藝術作風復興的緣故,然而時代究竟不同,漢初的形制、紋飾等仍有其自己的特色,細心辨別,不難認識。例如1963年陜西興平豆馬村發現的犀尊,遍體飾錯金銀云氣紋,本已定為西漢,又更正為“戰國晚期(秦)”。實際其云氣紋分瓣細碎,以銅鏡紋飾對比,是不會早到戰國的②。
近年發現了較多的西漢早期墓葬,有些是諸侯王級別的,包含了大量青銅器,多有很高的工藝水平。仔細研究這些器物的特色,將有助于解決其與戰國器相混的問題③。
________________
① 孫慰祖、徐谷甫:《秦漢金文匯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
篇12
以上所考9字均是從資陽方言里挑選出來的,具有代表性的方言本字,本文主要通過因聲求義的方法,并尋找古籍文獻進行印證,最終確定方言本字。對資陽方言本字的探討,不僅有利于我們了解資陽語言的變化發展、資陽的文化,甚至還有利于我們認識古漢語詞匯的變化,但由于文獻的不足,文章仍存在欠妥之處。
注解
①胡衛.資陽方言音系研究.四川師范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
參考文獻
[1]胡衛.資陽方言音系研究.四川師范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
[2](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09.3.
[3]桂馥.說文解字[M].北京:中局.1987.
[4]段玉裁.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文虎,張一舟,周家筠編.四川方言詞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1
[6]湯可敬撰.說文解字今釋[M].長沙.岳麓書社.2005.10.
[7]張慎儀著 張永言點校.續方言新校補 方言別錄 蜀方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5.
[8]唐樞.蜀籟[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8.
篇13
戴嘉枋以音樂史研究為題發言,認為歷史是一條河流,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的規律與結果,探討其因果關系是音樂史學一個任務。文藝的畸形繁盛是音樂為政治服務走到極端的必然結果。后音樂的大發展是對音樂的一個否定,今天有人喜歡樣板戲不是懷念樣板戲,而是對戲曲舞臺上的老戲不滿足。他指出:目前音樂史的研究呈“兩極化發展”,通史與個案的研究較多,而斷代史的研究較為薄弱;斷代史是通史的局部“放大”,應“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以歷史局外人的身份來客觀地看待研究對象,以史料為基礎對研究對象進行考證。
汪毓和就重寫近現代音樂史表示對自己著述不同意見與觀點討論的歡迎,提出“音樂史學應與民族音樂學相融合”,“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兩種結合,從而使“研究更為深刻”。向延生介紹了新版抗戰歌曲集編撰的背景及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抗戰歌曲的發展情況;同時也介紹了抗戰爆發后蕭友梅先生在給政府的報告中,提出要培養歌詠指揮、培養軍樂隊,改變音樂學院辦學思路、強調音樂為抗戰服務的一些重要史實。馮長春有關30、40年代“學院派”論爭的研究也引起與會者重視。
劉云燕對現代京劇樣板戲旦角唱腔的音樂分析,錢彤有關賀綠汀與20世紀早期流行音樂研究成果的介紹,彭麗有關彭修文研究,孟維平、李巖對近現代音樂研究提出的思考和見解,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趙廣暉教授對臺灣原住民音樂的介紹等發言,也受到關注。
追朔從前――古代史研究
修海林通過對巴蜀三組文物圖像的考證,結合文獻將其置于歷史的文化背景中進行考量,以對南宋時期的南方雜劇的角色及其表演形式分析研究,認為鼓、板、笛或鼓、板、篳笠為南宋兩種主要的雜劇樂器組合形式。賀志凌通過對新疆出土箜篌與巴洛雷克古代豎琴的比較,對箜篌的形制與淵源進行了考證,得出二者同斯基泰文化之源但不同流的結論。孔義龍的《論一弦等分取音與編鐘四聲音列》,王洪軍的《見于〈國語?周語下〉的鐘律文獻再解讀》和王清雷的《史前禮樂制度初研》,前兩文分別側重于考古學和文獻學兩種不同的方法,對鐘律進行了研究與探討,而王清雷則通過對史前鐘磬之樂的考證,對當時的禮樂制度進行了初步的分析。此外,章華英對古琴的打譜研究與理論做出總結;朱國龍對古的考釋等給學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國古代樂譜的研究,一直是音樂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薄弱環節。楊善武有《敦煌樂譜研究的新突破》的發言,他通過對同名曲《傾杯樂》旋律重合問題的探討,來證明林謙三在1955年有關琵琶定弦推論之正確,并旁證了燕樂二十八調中閏角調的存在。徐元勇對留存于海外(主要為日本)的明清樂譜的保存情況進行了研究,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新樂譜資料與照片。李穎則對明清時期唱樂記錄的形式即樂譜形式進行了歸納與總結。
古代史研究論文與發言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詳述。
學科建設與教學
鄭祖襄就中國音樂史的研究現狀發言,指出“隨著研究領域和范圍的擴大,研究層次的不斷提高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發展,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正不斷走向深入”。就目前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而言,主要體現為文獻史料研究、古代樂譜研究、古代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國樂律學史研究、音樂考古學研究、音樂思想研究、曲調考證七個主要方面。他強調了古代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重要性,針對目前研究較為薄弱的狀況,以及因缺少文獻記載對其研究所造成的困難,提出應以“考古學的方法”和“用歷史的語言代替歷史學”的觀念進行研究。并認為“考古樂器的類型學研究”和“建立一套科學的古樂器測音體系”是音樂考古學學科發展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兩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