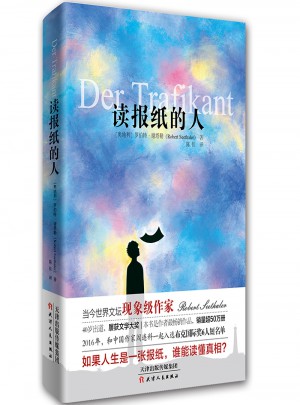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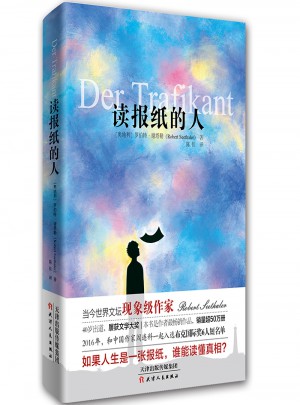
生活像一雙永不疲倦的眼睛,看著我們一次次離別和一點(diǎn)點(diǎn)成長(zhǎng)。
我們的情感在生活波瀾的激蕩中起伏浮沉,用力托起良心與欲望碰撞出的生命浪花。
在社會(huì)欲望的驅(qū)使下,賣(mài)報(bào)翁被迫害致死;心理學(xué)家弗洛伊德遠(yuǎn)走他鄉(xiāng);十七歲男主人公誓死反抗命運(yùn)的要挾;更多人則選擇了沉默和隨波逐流,將自己隱藏在黑暗的角落,謹(jǐn)小慎微地窺視著天邊的黎明。
每個(gè)人都在面對(duì)欲望的考驗(yàn),有的沉淪了,有的泯滅了,有的升華了……每個(gè)人的靈魂都在努力吟唱,且在不經(jīng)意間共同譜寫(xiě)了一篇超越性別、年齡和種族的欲望交響曲。
生活像一雙永不疲倦的眼睛,看著我們一次次離別和一點(diǎn)點(diǎn)成長(zhǎng)。
這是一本溫暖人類(lèi)情感&震動(dòng)世界文壇的心靈小說(shuō)!
作者40歲出道,屢獲文學(xué)大獎(jiǎng),2016年入圍布克國(guó)際獎(jiǎng),是當(dāng)今世界文壇現(xiàn)象級(jí)作家。
本書(shū)是作者的代表作,銷(xiāo)量超過(guò)50萬(wàn)冊(cè)。
故事曲折,情節(jié)生動(dòng):一個(gè)少年在一間報(bào)亭遇見(jiàn)心理學(xué)大師弗洛伊德,參與了一次欲望與良心的爭(zhēng)斗之旅,親情、愛(ài)情和友情的跌宕起伏見(jiàn)證著少年的一次次離別與成長(zhǎng)。
羅伯特 謝塔勒,生于1966年,奧地利超人氣小說(shuō)家。40歲出道,目前生活于維也納和柏林。羅伯特 謝塔勒的作品及獲獎(jiǎng)情況:小說(shuō)《碧內(nèi)和庫(kù)爾特》榮獲布登布洛克之屋新人獎(jiǎng)(2007)/榮獲下奧地利州文化獎(jiǎng)(2008)/電影《第二個(gè)女人》榮獲德國(guó)格里姆獎(jiǎng)(zui佳影片)(2009)/小說(shuō)《一輩子》榮獲德國(guó)格林美爾斯豪森獎(jiǎng)(2011)/榮獲布克國(guó)際獎(jiǎng)提名(2016)
1937年夏末的某個(gè)周日,一場(chǎng)異常猛烈的暴風(fēng)雨從薩爾茲卡默古特穿梭而過(guò)。這場(chǎng)暴風(fēng)雨,給弗蘭茨 胡赫爾滴答流淌的平靜生命帶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改變。
當(dāng)遠(yuǎn)處及時(shí)聲雷鳴隆隆響起,弗蘭茨跑進(jìn)了一座小漁房,他和母親就住在這里。
這里是阿特湖畔一個(gè)叫努斯多夫的小村莊。
他深深鉆入被窩,在羽絨被溫暖的庇護(hù)中聽(tīng)著外面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嘯聲。
暴風(fēng)雨從四面八方搖撼著這間小屋。
房梁呻吟著,外面的百葉窗“砰砰”地被敲打著,屋頂上長(zhǎng)滿(mǎn)青苔的木瓦在狂風(fēng)中顫動(dòng)著。陣陣暴風(fēng)裹著雨水噼里啪啦吹灑在窗戶(hù)上,窗前幾株已被折斷的天竺葵淹沒(méi)在花盆里。
在舊衣服箱子靠著的墻面上,掛著一尊鐵制耶穌,搖搖欲墜,似乎任何一秒鐘都有可能掙脫釘住它的釘子,從十字架上跳下來(lái)。
從不遠(yuǎn)處傳來(lái)漁船撞擊湖岸的聲音。船只被洶涌波浪掀起,沖向湖邊固定它們的樁子。
暴風(fēng)雨終于平息下來(lái),及時(shí)縷膽怯的陽(yáng)光斑駁地灑在炭黑色的、被幾輩人沉重的漁靴踏過(guò)的地板上,一直過(guò)渡到他的床上。
弗蘭茨蜷縮成舒適的一團(tuán),便于腦袋從被窩里伸出來(lái)環(huán)顧四周。
小屋子還立在原地,耶穌像依舊被釘在十字架上,透過(guò)濺滿(mǎn)水滴的窗戶(hù)看去,窗外閃耀著一瓣天竺葵花瓣,像一縷紅色的、柔弱的希望之光。
弗蘭茨慵懶地爬出被窩,走向小廚房,準(zhǔn)備去煮一壺高脂牛奶咖啡。灶底的柴火依然是干燥的,燒起來(lái)非常快。他向明亮的火焰里凝視了一會(huì)兒。
突然一聲響,門(mén)被打開(kāi)了。
他的母親站在低矮的門(mén)檻上。胡赫爾夫人在四十來(lái)歲人里算是一位苗條的女士了,看起來(lái)還是那么讓人賞心悅目,盡管欠缺一些精力。她像大多數(shù)在鄰近的鹽場(chǎng)、牲口棚或者避暑客棧廚房工作的本地人一樣,一生都在透支自己。
她僅僅是站在那里,一只手扶著門(mén)框柱子,微微低著頭喘息。圍裙緊貼在她身上,她的額頭上散落著幾縷凌亂的頭發(fā),鼻尖上落下幾滴水珠。
在她身后的背景里,陰郁的沙夫山高高聳入灰暗的云天,天空已經(jīng)在遠(yuǎn)處和近處又重新露出了些藍(lán)色。
弗蘭茨一直惦記著斜了的版刻圣母像,不知道是誰(shuí)在很久以前把它釘在了努斯多夫小教堂的門(mén)框上,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歲月剝蝕得體無(wú)完膚。
“你淋濕了嗎,媽媽?zhuān)?rdquo;他一邊問(wèn)著,一邊用一根鮮綠的枝條來(lái)回?fù)芘罨稹K鹆祟^,這時(shí)他才發(fā)現(xiàn),她正在哭。
她的眼淚混雜著雨水一起落下,肩膀在顫抖著。
“發(fā)生了什么?”他把枝條塞進(jìn)冒著濃煙的火中,吃驚地問(wèn)道。
她沒(méi)有回答,而是撐開(kāi)了門(mén),踉蹌地走向他,然后停在了屋子的中間。有那么一瞬間,看起來(lái)她似乎在向四周尋找著什么,舉起手做了一個(gè)無(wú)助的姿勢(shì),然后又滑落在膝前。
弗蘭茨猶豫地往前邁了一步,把手放到她的頭上,笨拙地?fù)崦?/p>
“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他用沙啞的聲音又問(wèn)了一遍。他突然有一種不適的感覺(jué),覺(jué)得自己有點(diǎn)兒傻。以前,情況剛好是相反的——他大哭大叫,母親撫摸他。
輕撫著她的頭發(fā),他觸摸到了一縷縷纖細(xì)的溫柔,他能感受到她頭皮下溫暖的脈搏在輕微地跳動(dòng)。
“他被淹死了。”她低聲地說(shuō)。
“誰(shuí)?”
“布萊寧格。”
弗蘭茨的手停了下來(lái),靜靜地放了一會(huì)兒,然后收了回來(lái)。
她掠起自己額上散亂的發(fā)絲,站起身來(lái),掀起圍裙的一角擦了擦臉。
“看你把屋子弄得烏煙瘴氣的!”她一邊說(shuō),一邊從灶臺(tái)里拿出那根鮮綠的枝條撥了撥火。
。。。 。。。
。。。 。。。
。。。 。。。
“早上好,教授先生!”奧托 森耶克說(shuō),低調(diào)地把自己的腿擺正了,“弗吉尼亞,和往常一樣?”
有一件弗蘭茨從做學(xué)徒到現(xiàn)在心里琢磨過(guò)很久的事情。在維也納,也有和在多瑙河岸邊碎石灘上一樣的所謂教授。在有的區(qū),人們甚至?xí)Q(chēng)馬肉屠夫和釀酒廠(chǎng)車(chē)夫?yàn)?ldquo;教授先生”。
然而,這次是其他的。
奧托 森耶克對(duì)這位先生問(wèn)候的方式,讓弗蘭茨馬上就清楚了,這是一位真的教授,一位真誠(chéng)的真實(shí)的教授,一位不用把自己的頭銜像牛鈴般掛在胸前搖擺,好讓他體面的教授身份能被人認(rèn)出的教授。
“是的。”老先生稍稍點(diǎn)了下頭說(shuō)道,同時(shí)他把帽子從頭上摘了下來(lái),然后從容地放在自己面前的柜臺(tái)上,“請(qǐng)給我20支煙。還有一份《新自由媒體》。”
他說(shuō)得很慢也很輕,讓人很難理解。他幾乎都沒(méi)怎么張開(kāi)嘴,他說(shuō)的每一個(gè)單詞都好像是費(fèi)很大的勁兒從牙縫里擠出來(lái)的。
“好的,教授先生!”奧托 森耶克說(shuō)道,然后向弗蘭茨點(diǎn)了點(diǎn)頭。弗蘭茨拿出了一盒20支裝的弗吉尼亞香煙,從貨架上拿出報(bào)紙,然后把東西都放在柜臺(tái)上,仔細(xì)地用包裝紙將它們包了起來(lái)。他察覺(jué)到老人看向他的視線(xiàn),好像地跟著他的每一個(gè)動(dòng)作。
“順便提一下,這是弗蘭茨。”奧托 森耶克解釋著,“從薩爾茲卡默古特來(lái)的,他還有好多要學(xué)的呢!”
老先生把頭向前伸了伸。弗蘭茨可以透過(guò)眼角看出他皮膚上的皺紋,薄得像一層薄棉紙,掛在他襯衫領(lǐng)邊上。
“薩爾茲卡默古特,”他用少見(jiàn)的扭曲著的嘴說(shuō)道,可能本是想露出一個(gè)微笑,“很漂亮的地方。”
“我是從阿特湖來(lái)的!”弗蘭茨點(diǎn)著頭。不知出于某種原因,他人生中及時(shí)次為這個(gè)奇怪的水簾洞般的故鄉(xiāng)名字感到了一絲驕傲。
“很漂亮!”教授重復(fù)了一遍。然后,他放了幾枚硬幣在柜臺(tái)上,把裝好的包裹夾在腋下,準(zhǔn)備離開(kāi)。弗蘭茨向門(mén)那邊跨了一步,想去開(kāi)門(mén)。老先生朝他點(diǎn)點(diǎn)頭。老先生走到了街上,風(fēng)馬上就把他的胡子吹亂了。“這位老先生肯定很少聞東西,”弗蘭茨心想,“肥皂味,洋蔥味,或者木屑的氣味……”
“這位教授是誰(shuí)呢?”弗蘭茨把門(mén)關(guān)上一點(diǎn)兒后問(wèn)道。他使了很大勁兒才直起了身子,解除了之前不由自主地卑躬屈膝的姿勢(shì)。
“這是教授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奧托 森耶克說(shuō)道。接著,他呻吟著讓自己陷入了屁股底下的沙發(fā)椅中。
“那位治笨蛋的醫(yī)生?”弗蘭茨用略帶震驚的聲音驚呼了一下。他當(dāng)然聽(tīng)說(shuō)過(guò)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這位教授的名聲在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傳到了地球上很遙遠(yuǎn)的地方,也傳到了薩爾茲卡默古特,勾起了當(dāng)?shù)厝说挠薮阑孟搿D切┗孟耄际顷P(guān)于各種可怕的欲念,私人診療時(shí)間里庸俗的笑話(huà),狼嚎般的女病人和隨處可見(jiàn)的赤身裸體。
“就是他!”奧托 森耶克回答,“但他的能耐可遠(yuǎn)不止治療一個(gè)有錢(qián)的笨腦袋瓜子。”
“他還有什么能耐?”
“據(jù)說(shuō),他能教會(huì)人過(guò)上一種內(nèi)心平靜的生活。當(dāng)然啦,也不是所有人,僅僅是能付得起他酬金的那些人。聽(tīng)人們說(shuō),去他門(mén)診看一個(gè)小時(shí)花的錢(qián),夠買(mǎi)市郊的半個(gè)小菜園子。這說(shuō)得可能有些夸張。他給病人治療時(shí),不用像其他醫(yī)生一樣觸碰病人。對(duì)于這個(gè)吧,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他已經(jīng)觸碰他們了,只是沒(méi)有用手去觸碰而已。”
“那他用什么去觸碰啊?”
“這我當(dāng)然知道!”奧托 森耶克開(kāi)始有些變得不耐煩了,“用思想,或者用靈魂,再或者用什么其他的玩意兒。無(wú)論如何,這些觸碰是起作用的,這才是最關(guān)鍵的。行了,你好好讀你的報(bào)紙吧,別再來(lái)吵吵我啦!”
奧托 森耶克把腰深深彎向一摞紙,從抽屜里拿了出來(lái),然后開(kāi)始用他的鋼筆和木尺子在上面畫(huà)直線(xiàn)。
弗蘭茨把額頭抵在櫥窗玻璃上,通過(guò)一條細(xì)細(xì)的透光的縫往外窺探,在他目光正前方,教授正夾著包裹朝威寧爾街下坡走。他走得很慢,邁著謹(jǐn)慎的小步子,腦袋微微垂下。
“他看上去其實(shí)挺和藹可親的,這位教授先生!”弗蘭茨深思著說(shuō)。奧托 森耶克嘆息了一聲,朝他瞥了一眼。
“他可能讓人及時(shí)眼看上去確實(shí)覺(jué)得和藹可親,但是如果你問(wèn)我的話(huà),盡管他還經(jīng)營(yíng)著神經(jīng)診所,但他畢竟已經(jīng)是個(gè)干枯老頭子了。除此之外,他還有個(gè)不小的問(wèn)題呢!”
“什么問(wèn)題?”
“他是個(gè)猶太人。”
“啊?”弗蘭茨說(shuō),“這為什么會(huì)成為一個(gè)問(wèn)題啊?”
“這馬上就會(huì)成為一個(gè)問(wèn)題,”奧托 森耶克說(shuō),“而且很快就會(huì)!”
奧托 森耶克的眼神在報(bào)亭里迷離了一會(huì)兒,就好像是要找一個(gè)安全的地方來(lái)逗留。然后,他默默笑了一下,彎下腰回到他的工作上。他仔細(xì)地用一只小海綿的尖角把擴(kuò)散到線(xiàn)條中間的一個(gè)墨點(diǎn)搌干。
弗蘭茨仍然在朝櫥窗外看。這件關(guān)于猶太人的事,他到現(xiàn)在都沒(méi)有真正理解。報(bào)紙上沒(méi)讓猶太人有過(guò)好看的圖片,而在搞笑漫畫(huà)上,他們看起來(lái)很可笑,或者是狡猾,很多時(shí)候甚至是這兩者的結(jié)合。“在這個(gè)城市,至少會(huì)有一些人,”弗蘭茨心想,“從骨子里是真正的猶太人,有著猶太式的名字,猶太式的帽子和猶太人的鼻子。”在老家努斯多夫那邊,一個(gè)都沒(méi)有。那里的本地人,由于外貌,他們頂多被臆想成可怕、卑鄙或者癡呆的人,最多被說(shuō)成是某種不好的民間故事里的人物。
那位教授正在前面坡上的街道轉(zhuǎn)彎。一陣風(fēng)掠過(guò),他的一綹頭發(fā)被吹得揚(yáng)了起來(lái),猶如一根羽毛,在他頭上飄搖了幾秒鐘。
“帽子!他的帽子哪兒去了?”弗蘭茨驚訝地叫了起來(lái)。他的視線(xiàn)落到了柜臺(tái)上,教授那頂灰色的帽子還一直放在那兒。他的話(huà)音還未落,飛一般地拿起帽子就朝馬路那邊跑過(guò)去了。
“等一下,站住,教授先生!”他大聲喊道,并揮著胳膊跑到了還有幾步就能趕上教授的街角,上氣不接下氣地把帽子遞了過(guò)去。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盯著他有點(diǎn)兒凹陷的帽子看了一眼,接了過(guò)去。作為回應(yīng),他把錢(qián)包從外套口袋里拿了出來(lái)……
“拜托您別這樣,教授先生,這是我理所應(yīng)當(dāng)做的事!”弗蘭茨用拒絕的手勢(shì)來(lái)示意著,和他想表達(dá)的意思比起來(lái),他這個(gè)手勢(shì)比畫(huà)的幅度有點(diǎn)兒夸張。
“一件理所當(dāng)然的事,當(dāng)今社會(huì)已經(jīng)沒(méi)有了!”弗洛伊德說(shuō),他的大拇指把帽檐按出了個(gè)深深的凹陷。和之前一樣,他說(shuō)話(huà)幾乎不張開(kāi)嘴,只是輕輕地?cái)D出來(lái)。為了把話(huà)聽(tīng)得更清楚,弗蘭茨把腦袋往前伸了一點(diǎn)兒,他不想錯(cuò)過(guò)這位名聲大噪的男人說(shuō)的任何一個(gè)單詞。
“我可以幫您嗎?”弗蘭茨問(wèn)道。盡管弗洛伊德拒絕了,但他還是沒(méi)能足夠快地阻止,弗蘭茨把他的包裹和報(bào)紙從胳膊下抽出來(lái),抱在自己胸前。
“這下可以了。”弗洛伊德嘟噥著,把帽子戴到頭上,然后又動(dòng)身了。
弗蘭茨忽然覺(jué)得肚子那塊兒有點(diǎn)不對(duì)勁,就在他和教授在陡然向下的街道上走的時(shí)候,好像有一個(gè)沉重的東西想要提醒他這一刻的意義。走了幾步之后,肚子里奇怪的沉重感就消失了。,當(dāng)他們經(jīng)過(guò)葛林德?tīng)柌穹蛉讼銡鉂M(mǎn)溢的停泊面包房時(shí),他看見(jiàn)了自己在沾有粉塵的櫥窗里的身影,看見(jiàn)了自己是怎么往前走的——筆挺直立,包裹夾在腋下,內(nèi)心被榮幸的感覺(jué)深深地溫暖了,來(lái)自教授身上的光芒散落在他身上,讓他突然感到非常驕傲和愜意。
“我可以問(wèn)您一個(gè)問(wèn)題嗎,教授先生?”
“那要看你問(wèn)什么問(wèn)題了。”
“真的可以嗎?您可以讓一個(gè)人的內(nèi)心變得平靜嗎?您可以讓人們過(guò)上一種井然有序的生活嗎?”
弗洛伊德把他的帽子摘了下來(lái),小心翼翼地把一綹稀松的、雪白的頭發(fā)捋到了耳后,又把帽子重新戴上,側(cè)著臉看著弗蘭茨。
“人們?cè)趫?bào)亭里是這么說(shuō)我的嗎?還是在你的老家薩爾茲卡默古特?”
“不是……”弗蘭茨聳著肩膀說(shuō)。
“如果說(shuō)我不可以把一個(gè)人的手臂掰直,但我至少不會(huì)將其整脫臼了,我的診所在現(xiàn)今來(lái)說(shuō)算是有良心的。我能夠解釋一些心理困惑,在有些充滿(mǎn)靈感的時(shí)間里,我甚至可以超越前輩的解釋。這就是全部了。”弗洛伊德擠出這些話(huà)來(lái),好像每個(gè)詞都表達(dá)著他的疼痛,“但是,我說(shuō)的這些也不是靠得住的。”他嘆息著又補(bǔ)了一句。
“您平時(shí)是怎樣工作的呢?”
“人們坐在我的沙發(fā)上,然后我們聊天。”
“這聽(tīng)起來(lái)很舒服。”
“事實(shí)是,這很少讓人舒服。”弗洛伊德回答道。然后,他從褲子口袋里拿出深藍(lán)色的針織手絹,并對(duì)著微咳了一下。
“嗯?”弗蘭茨說(shuō),“這個(gè)我有點(diǎn)兒想不通。”
他站住了,視線(xiàn)斜向上,試圖把自己所有錯(cuò)亂交織的怪誕想法集中到城市屋頂之上很遠(yuǎn)的地方,然后醞釀出想說(shuō)的話(huà)。
“然后呢?”在這位充滿(mǎn)好奇心的、有點(diǎn)兒磨纏人的賣(mài)報(bào)小伙子又一次請(qǐng)教弗洛伊德之后,教授問(wèn)道,“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現(xiàn)在,我還什么都想不出來(lái)。但這沒(méi)關(guān)系,我會(huì)再花點(diǎn)兒時(shí)間去想,再思考得久一點(diǎn)兒。除此之外,我還會(huì)買(mǎi)您的書(shū)來(lái)看。所有的書(shū),從頭到尾!”
弗洛伊德又嘆息了一聲。實(shí)際上,他想不起來(lái),他在這么短的時(shí)間里已經(jīng)嘆了多少次。
“比起去看我這個(gè)老頭的那些大部頭著作,你沒(méi)有更緊要的事情可以做嗎?”他問(wèn)。
“比如說(shuō)呢?”
“這你也要問(wèn)我?你那么年輕,可以走進(jìn)新鮮空氣里,出去郊游一次,取悅一下自己,給自己找個(gè)姑娘。”
弗蘭茨瞪大了眼睛看著他,渾身上下一陣哆嗦。“是啊!”他心想,“是啊,是啊,是啊!”他脫口喊了一句:“一個(gè)姑娘!”他喊得如此尖銳,有點(diǎn)兒嚇到了街對(duì)面剛聚到一起聊八卦的三個(gè)老婦,她們把極富藝術(shù)感的波浪頭齊齊轉(zhuǎn)向了他這邊。
“可是,哪有那么簡(jiǎn)單啊……”
弗蘭茨終于把這些話(huà)說(shuō)出來(lái)了,他已經(jīng)想了好長(zhǎng)時(shí)間,地說(shuō),是從他私處的毛發(fā)剛開(kāi)始膽怯地萌發(fā)時(shí),他的腦子和心臟就開(kāi)始被此事攪動(dòng)得不安了。
“到目前為止,大部分人都做到了。”
弗洛伊德用他的拐杖在路面上無(wú)誤地?fù)荛_(kāi)了一顆小石子。
“可這不等于我很快就能做到啊!”
“你怎么知道自己做不到啊?”
“在我們那兒,人們可能會(huì)理解木材生意,還有怎么讓去那兒避暑的游客從兜里掏出錢(qián)來(lái)。而關(guān)于愛(ài)情,全都一竅不通!”
“這沒(méi)有什么不正常的,因?yàn)闆](méi)有人能理解關(guān)于愛(ài)情的任何東西。”
“您也不理解嗎?”
“我不理解!”
“那為什么人們會(huì)一個(gè)接一個(gè)地墜入愛(ài)河?”
“年輕人,”弗洛伊德停下來(lái)說(shuō),“人們頭朝前跳進(jìn)水里,不用非得理解水吧?”
“唉!”弗蘭茨忽然覺(jué)得找不到合適的詞語(yǔ)來(lái)形容自己一直以來(lái)欲望被壓抑的不幸。接著又發(fā)出一聲:“唉!”
“別感嘆了,”弗洛伊德說(shuō)道,“我已經(jīng)到了。年輕人,可以還我的雪茄和報(bào)紙了吧?”
“那當(dāng)然了,教授先生!”弗蘭茨耷拉著腦袋,恭敬地把東西遞給了弗洛伊德。
房子入口處的小牌子上寫(xiě)著“伯格街19號(hào)”。弗洛伊德笨拙地拿出一串鑰匙,鎖開(kāi)了之后,他把消瘦的身體倚在笨重的木門(mén)上,往前推。
“我能幫……”
“不行,你不能!”弗洛伊德一邊急忙從門(mén)縫擠進(jìn)屋里,一邊發(fā)著牢騷。
“還有就是,你要記住了,”他又?jǐn)D了出來(lái),把頭伸到室外,“女人就像雪茄一樣,你被她們吸引得越深,就離享受越遠(yuǎn)。祝你度過(guò)愉快的24小時(shí)!”然后,他就消失在房子昏暗的走廊里。輕輕的“嘎吱”一聲,門(mén)鎖上了,弗蘭茨獨(dú)自站在風(fēng)中。
有時(shí)候,必須要離開(kāi);有時(shí)候,必須要留下。這就是生活。
我們來(lái)到這個(gè)世界,不是為了去尋找答案,而是要去經(jīng)歷。我們?cè)趲缀跤篮愕娜松璋抵兴奶幟鳎挥凶銐蛐疫\(yùn)的人,才能偶爾看見(jiàn)一盞小燈燃起的光明。
日子過(guò)得越長(zhǎng),生命顯得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