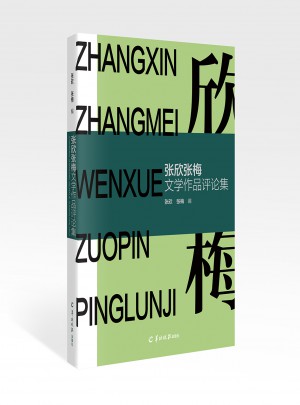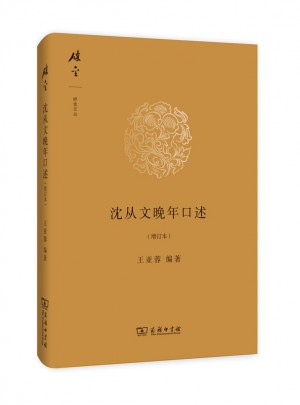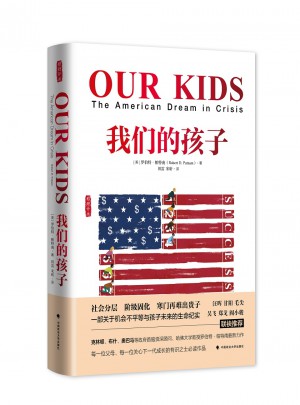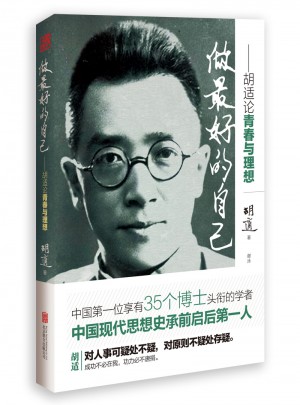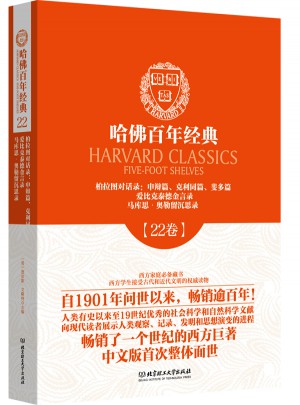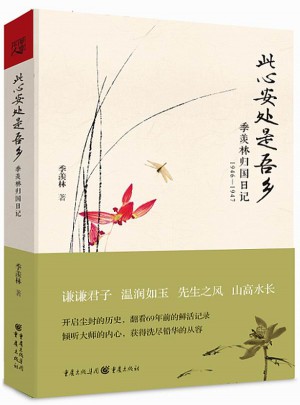明暗筆法,愛(ài)的底蘊(yùn)
——讀張欣新作《終極底牌》 陳曉明 / 1
對(duì)當(dāng)下中國(guó)的精神守望與價(jià)值期許
——看《終極底牌》的靈動(dòng)其表與深沉其里 鐘曉毅 / 5
屬于張欣的廣州故事 江 冰 / 10
百般婉轉(zhuǎn),一樣心腸
——故事和講故事的人 王 穎 / 13
在紅塵中安妥靈魂
——素描張欣 鐘曉毅 / 18
看的是小說(shuō),讀的是生活
——《梅邊》讀后感 / 23
當(dāng)代都市小說(shuō)之異流
——張欣《不在梅邊在柳邊》等三部長(zhǎng)篇閱讀記 雷 達(dá) / 27
努力發(fā)現(xiàn)城市生活的深層秘密
——評(píng)張欣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終極底牌》 孟繁華 / 31
鑄造優(yōu)雅、高貴和詩(shī)意的審美趣味
——以張欣的《終極底牌》《不在梅邊在柳邊》為例 賀紹俊 / 37
跋:此岸詩(shī)情的守望者
——我讀張欣 程文超 / 47002
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袁行霈致張欣的一封信 / 62
代跋:深陷紅塵 重拾浪漫 張 欣 / 63
都市喧囂中的價(jià)值持守與裂變
——張欣小說(shuō)解讀 賈亦真 / 65
讀者史今致張欣的一封信 / 70
浮華背后的女作家 孟 靜 / 72
漫說(shuō)張欣 陳志紅 / 75
我對(duì)周邊的生活很敏感 謝有順 / 82
顛覆自己 張 欣 / 88
寫(xiě)作是一種生活方式 張 欣 / 90
學(xué)者、作家余秋雨致張欣的一封信 / 93
張欣:《深喉》,是小說(shuō)不是調(diào)查報(bào)告 / 95
張欣:我對(duì)熱點(diǎn)事件感興趣 / 102
張欣:我給自己的定位是純文學(xué)作家 / 108
張欣暖洋洋 池 莉 / 112
張欣印象(代跋) 蔣子丹 / 118
張欣主要作品目錄 / 121
張梅文學(xué)作品評(píng)論集
張梅藝術(shù)年表 / 126
張梅《破碎的激情》 雷 達(dá) / 135
破碎的激情與啟蒙者的命運(yùn) 李 陀 / 138
從理想國(guó)的夢(mèng)中醒來(lái)
——張梅長(zhǎng)篇小說(shuō)《破碎的激情》閱讀 謝有順 / 146
尋找故事、趣味與簡(jiǎn)約 徐肖楠 / 154
平靜中的欲望與憂傷 徐肖楠 / 161003
睡眼惺忪的張梅和一座憂郁的城市 張 檸 / 167
張梅:早醒而憂郁的靈魂 黃景忠 / 174
舒緩語(yǔ)氣之中的尖聲銳聲
——評(píng)《成珠樓記憶》 李大鵬 / 182
一剪梅 荊 歌 / 185
一條更為寬闊的女性寫(xiě)作道路
——評(píng)張梅的創(chuàng)作 黃 鶯 / 187
張梅真不簡(jiǎn)單 戴洪齡 / 202
真實(shí)的快樂(lè)與悲涼 陳志紅 / 206
我讀張梅的《殊路同歸》 石 娃 / 209
此種風(fēng)情
——話說(shuō)張梅 艾曉明 / 212
你那酒汪汪的玫瑰色女狐貍眼睛 徐 坤 / 216
閑人老張 沈宏非 / 218
紅塵夢(mèng)醒自知?dú)w 鐘曉毅 / 221
孤獨(dú)的魅力
——讀張梅《保齡球館13號(hào)線》 陳淑梅 / 224
“視點(diǎn)”之外的影像
——讀張梅《保齡球館13號(hào)線》 陳偉軍 / 226
張梅筆下的另一種人生 程文超 / 229
那天去看張梅 韋映川 / 234
新穎嬗變
——讀廣東青年女作家張梅的小說(shuō) 謝望新 / 237
生命中的精靈
——讀張梅散文集《千面人生》 伊 童 / 240
塑造女人 羅 宏 / 243
文章以真為上乘
——讀張梅散文隨想 岑 桑 / 246
激情和寫(xiě)作
——張梅小說(shuō)印象 陳 虹 / 249
張梅印象記 江南藜果 / 253
我的寫(xiě)作成熟期還沒(méi)到來(lái) 龍迎春 / 255
南方故事的兩種講法
——張欣和張梅小說(shuō)新論 徐 岱 / 259
先鋒女性和傳統(tǒng)女性的內(nèi)在沖突 / 272
斯人幽雅獨(dú)立 文/夏堅(jiān)德 / 285
南都女性“浮世繪”
——評(píng)張梅小說(shuō)《酒后的愛(ài)情觀》 邵 建 / 289
天空有云才真實(shí) 梁秀辰 / 295
激情起落 相關(guān)何處
——讀張梅長(zhǎng)篇小說(shuō)《破碎的激情》 馬相武 / 299
現(xiàn)代都市人的心靈描述與透視
——讀張梅的小說(shuō) 游焜炳 / 302
于隨緣處看張梅 程 鷹 / 305
激情,一生可能只有一次
——廣州女作家張梅訪談 楊宛星 / 308
張梅和她的紫衣裳 石 明 / 316
以南方的標(biāo)準(zhǔn)生活,以北方的標(biāo)準(zhǔn)寫(xiě)作 黃 茵 / 318
都市欲望中的浮沉與掙扎
——張梅小說(shuō)中女性形象的心靈特征 齊 紅 / 322
南國(guó)都市的喧嘩與騷動(dòng)
——評(píng)張梅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破碎的激情》 朱育穎 / 330
現(xiàn)代都市與女性生存的兩種詮釋
——王安憶、張梅都市小說(shuō)比較分析 趙改燕 / 336
張梅:理想主義的荒誕處境與反諷敘述 李春華 / 344
張梅長(zhǎng)篇小說(shuō)《破碎的激情》研討會(huì)紀(jì)要 / 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