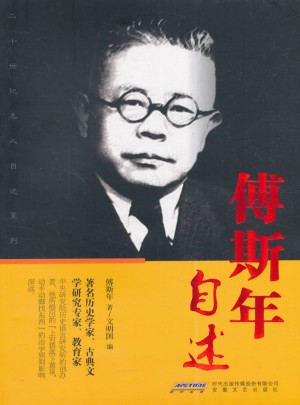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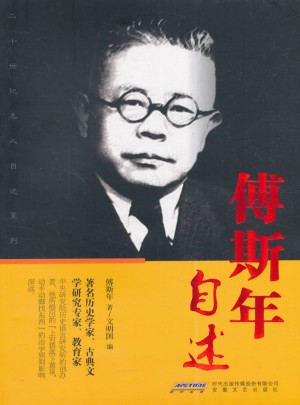
《傅斯年自述》是"二十世紀(jì)名人自述系列"的一種,為中國(guó)現(xiàn)代國(guó)學(xué)大師、歷史學(xué)家、教育家傅斯年先生的部分文集,內(nèi)容既有其學(xué)術(shù)自述,又有其與時(shí)人的交往的記錄和部分游記,還有自己撰寫的序跋、評(píng)論以及對(duì)于教育的主張,文字體現(xiàn)了作者在歷史考古和教育學(xué)等方面的深厚造詣,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省聊城人,生于儒學(xué)世家。他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xué),師從劉師培、黃侃等國(guó)學(xué)大師,后到英德留學(xué),回國(guó)后一直在教育與研究部門任職……《傅斯年自述》是"二十世紀(jì)名人自述系列"的一種,為中國(guó)現(xiàn)代國(guó)學(xué)大師、歷史學(xué)家、教育家傅斯年先生的部分文集。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省聊城人,生于儒學(xué)世家。他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xué),師從劉師培、黃侃等國(guó)學(xué)大師,后到英德留學(xué),回國(guó)后一直在教育與研究部門任職。他學(xué)識(shí)淵博,貫通中西,在歷史學(xué)、語(yǔ)言學(xué)、考古學(xué)與學(xué)校教育等方面均獲得了顯著成就,一生著述頗豐。他是我國(guó)近現(xiàn)代之交,在新舊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涌現(xiàn)出的一位著名學(xué)者、教育家和社會(huì)活動(dòng)家。
及時(shí)編 學(xué)術(shù)自述
《新潮》發(fā)刊旨趣書
《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附錄:《語(yǔ)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發(fā)刊詞
本所發(fā)掘安陽(yáng)殷墟之經(jīng)過(guò)——礅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關(guān)心文化學(xué)術(shù)事業(yè)者
一 吾等發(fā)掘之緣起及工作之宗旨
二 糾葛之突生
三 政府之主持及在開封之接洽
四 河南省政府之解決此事
第二編 人物與交游
論伯希和教授
追憶王光祈先生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fēng)格
我所認(rèn)識(shí)的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一個(gè)人物的幾片光影
一 在君的邏輯
二 在君的幾片風(fēng)趣
二 在君與政治
段繩武先生傳
倪約瑟博士歡送詞
我對(duì)蕭伯納的看法
第三編 游記
歐游途中隨感錄
北京上海道中
留英紀(jì)行
第四編 序跋與評(píng)論
中山大學(xué)民國(guó)十七年屆畢業(yè)同學(xué)錄序
劉復(fù)《四聲實(shí)驗(yàn)錄》序
跋《人境廬詩(shī)草》
《殷歷譜》序
評(píng)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guān)系》
第五編 見解與主張
考古學(xué)的新方法
教育崩潰之原因
教育改革中幾個(gè)具體事件
論學(xué)校讀經(jīng)
閑談歷史教科書
一 歷史教科書和各種自然科學(xué)教科書之不同處
二 選擇歷史事件之原則
三 教育部設(shè)定之標(biāo)準(zhǔn)
四 編歷史教科書的一個(gè)基礎(chǔ)則律
五 活的教科書
六 輔助書
七 編西洋史教科書時(shí)應(yīng)注意的幾個(gè)大題目
八 民族主義與歷史教材
九 結(jié)語(yǔ)
漫談辦學(xué)
中國(guó)學(xué)校制度之批評(píng)
一 史的略述
二 針對(duì)現(xiàn)局設(shè)立五個(gè)原則
三 方案
四 相對(duì)與均衡
五 編譯
六 余義
缺憾沒(méi)有不可彌補(bǔ)的,我們不知道則已,既經(jīng)知道,自然有彌補(bǔ)的必然。若是別人肯責(zé)備我們,發(fā)覺(jué)我們所不自覺(jué)的,我們尤其感激。有我們這一群最可愛(ài)的同社,必成一件最可愛(ài)的事業(yè)。
自從以后,我們的雜志停頓了。因?yàn)楸本┐髮W(xué)幾個(gè)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諸君多在學(xué)校里服務(wù),也有往上海的,就無(wú)暇及此了。現(xiàn)在大學(xué)恢復(fù)舊狀,我們社員又集在一起,把幾個(gè)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這筆桿下的苦斗。從今以后,我們得個(gè)新生命。過(guò)后,中國(guó)的社會(huì)趨向改變了。有覺(jué)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jué)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發(fā)作。社會(huì)上對(duì)于北大的空氣大改變。以后是社會(huì)改造運(yùn)動(dòng)的時(shí)代。我們?cè)谶@個(gè)時(shí)候,處這個(gè)地方,自然造成一種新生命。況且現(xiàn)在同學(xué)入社的多了,力量自然比先厚些。又有《新青年》記者諸位先生,答應(yīng)給我們投稿,更是可以歡喜的。同社畢業(yè)的有幾位在京,有幾位在外,加上一番社會(huì)上的實(shí)地考練,再做出的文章,當(dāng)然更要成熟些。楊振聲君往美國(guó)去,俞平伯君和我往英國(guó)去。雖有在外的,在內(nèi)的,然而精神上一氣,所以第二號(hào)及時(shí)期,不是泛泛的一面換卷數(shù),是我們的一個(gè)新擴(kuò)張。
近兩年里,為著昏亂政治的反響,種下了一個(gè)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現(xiàn)在仿佛像前清末年,革命運(yùn)動(dòng)、立憲運(yùn)動(dòng)的時(shí)代一個(gè)樣,醞釀些時(shí),中國(guó)或又有一種的平民運(yùn)動(dòng)。
所以我們雖當(dāng)現(xiàn)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兩政府之下,我們的希望并不滅殺。不過(guò)就最近兩三個(gè)月內(nèi)的情形而論,我們又生一種憂慮。這憂慮或者是一種過(guò)慮;但是如果人人有這過(guò)慮,或者于事業(yè)的將來(lái)上有益些。我覺(jué)得期刊物的出現(xiàn)太多了,有點(diǎn)不成熟而發(fā)揮的現(xiàn)象。照現(xiàn)在中國(guó)社會(huì)的麻木、無(wú)知覺(jué)而論,固然應(yīng)該有許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實(shí)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fā)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將來(lái)無(wú)益有損。精深細(xì)密的刊物尤其要緊。就現(xiàn)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細(xì)研究一個(gè)問(wèn)題而按部就班地解決它,不落在隨便發(fā)議論的一種毛病里,只有一個(gè)《建設(shè)》。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藝思想、人道主義精切勇猛地發(fā)表出來(lái),只有一個(gè)《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評(píng)論》、《少年中國(guó)》、《解放與改造》和短命的《每周評(píng)論》、《湘江評(píng)論》算最有價(jià)值。然而及時(shí)流的雖有多種,我總覺(jué)著為應(yīng)現(xiàn)時(shí)所要求,為謀方來(lái)的擴(kuò)展,還嫌實(shí)力薄些。我們?cè)菍W(xué)生,所以正是厚蓄實(shí)力的時(shí)候。我不愿《新潮》在現(xiàn)在錚錚有聲,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個(gè)切切實(shí)實(shí)的效果。我們的知識(shí)越進(jìn),人數(shù)越多,而《新潮》的頁(yè)數(shù)越減,才見我們的真實(shí)改善。
至于新潮社的結(jié)合,是個(gè)學(xué)會(huì)的雛形。這學(xué)會(huì)是個(gè)讀書會(huì),將來(lái)進(jìn)步,有些設(shè)備了,可以合伙研究幾件事務(wù)。
的目的,是宣傳一種主義。到這一層,算止境了,我們決不使它成偌大的一個(gè)結(jié)合,去處治社會(huì)上的一切事件。些小冊(cè)子,編輯一種人事學(xué)科的業(yè)書,一種思想潮流的業(yè)書,一種文藝業(yè)書,和其他刊物,是我們的事業(yè),此外也沒(méi)有我們的事業(yè)。中國(guó)的政治,不特現(xiàn)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lái),我也以為是更糟糕的。兩千年專制的結(jié)果,把國(guó)民的責(zé)任心幾乎消磨凈了。所以中國(guó)人單獨(dú)的行動(dòng)十九卑鄙齷齪,團(tuán)體的行動(dòng)十九過(guò)度逾量——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無(wú)論對(duì)于什么都不負(fù)責(zé)任。我常想,專制之后,必然產(chǎn)成無(wú)治:中國(guó)既不是從貴族政治轉(zhuǎn)來(lái)的,自然不能到賢人政治一個(gè)階級(jí)。至于賢人政治之好不好,另是一個(gè)問(wèn)題。所以在中國(guó)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對(duì)于政治關(guān)心,有時(shí)不免是極無(wú)效果、極笨的事。我們同社中有這見解的人很多。我雖心量褊狹,不過(guò)尚不致于對(duì)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惡痛絕!然而以個(gè)人的脾胃和見解的緣故,不特自己要以教書匠終其身,就是看見別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動(dòng)的,也屢起反感。同社中和我抱同樣心思的正多。常有一種極純潔的結(jié)合,而一轉(zhuǎn)再轉(zhuǎn)便成政黨的小體。如此一般人的結(jié)合,自然沒(méi)有一轉(zhuǎn)再轉(zhuǎn)的危險(xiǎn)。
那么,我們是"專心致志",辦"終身以之"的讀書會(huì)了。
我希望新潮社員從今以后,時(shí)時(shí)刻刻不忘《新潮》的改善。知道它的缺陷極透徹了,然后可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一團(tuán)體和一個(gè)人一樣,進(jìn)步全靠著覺(jué)悟——覺(jué)悟以前如何如何的不好,以后該當(dāng)如何如何,然后漸漸的到好的地界去。天地間沒(méi)有沒(méi)有缺陷的人,所以我們對(duì)于我們自己,應(yīng)該嚴(yán)格地自反,對(duì)于我們的缺陷,不特不必回護(hù),而且無(wú)所用其恨惋。如此固是很好,不過(guò)仍不到理性的境界——應(yīng)該從從容容地補(bǔ)上,改好。
……P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