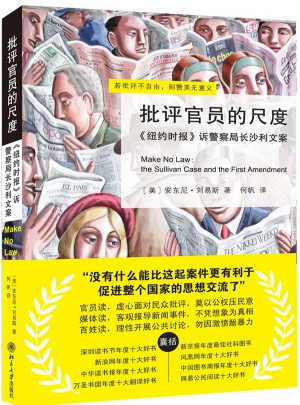
批評(píng)官員的尺度·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
- 所屬分類:圖書 >法律>外國法律與港澳臺(tái)法律>司法案例
- 作者:(美)[安東尼.劉易斯]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hào):9787301188736
- 出版社: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 出版時(shí)間:2011-08
- 印刷時(shí)間:2011-07-01
- 版次:1
- 開本:12開
- 頁數(shù):--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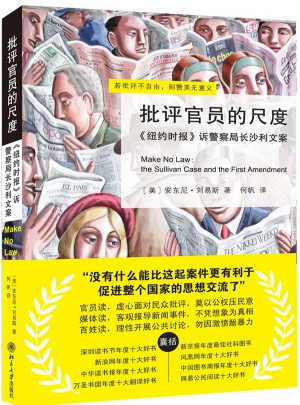
1960年,因?yàn)橐粍t批評(píng)性廣告,警察局長沙利文以誹謗為由,將《紐約時(shí)報(bào)》告上法庭,并申請巨額賠償。兩審失利后,幾乎被各地政府官員相繼提起的索賠逼至絕境的《紐約時(shí)報(bào)》,奮起上訴至聯(lián)邦較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紐約時(shí)報(bào)》訴沙利文案”中力挽狂瀾,宣布“對公共事務(wù)的討論應(yīng)當(dāng)不受抑制、充滿活力并廣泛公開”,維護(hù)了媒體、公民批評(píng)官員的自由。《紐約時(shí)報(bào)》博學(xué)記者、兩度普利策獎(jiǎng)得主安東尼?劉易斯,以翔實(shí)史料、生動(dòng)筆觸,系統(tǒng)回顧了這起新聞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并循此為線,串接起美國人民爭取言論自由的司法抗?fàn)帤v史,展現(xiàn)了霍姆斯、布蘭代斯、漢德、沃倫、布倫南、布萊克、韋克斯勒等偉大法官和律師的形象。
兩度普利策獎(jiǎng)得主安東尼 劉易斯原著,暢銷譯作《九人》譯者何帆翻譯。“我想不出什么案子,能比這起案件更有利于促進(jìn)整個(gè)國家的思想交流了。”本書以在美國家喻戶曉的“紐約時(shí)報(bào)訴沙利文案”連線展現(xiàn)了200多年來美國言論自由的司法斗爭史,既理性而堅(jiān)定地闡述和捍衛(wèi)了批評(píng)之聲與新聞自由的真正價(jià)值,同時(shí),又一再冷靜地提醒我們,自由不可濫用。
安東尼 劉易斯(Anthony Lewis),1927年3月生于紐約,畢業(yè)于哈佛學(xué)院。曾任《紐約時(shí)報(bào)》周日版編輯(1948—1952)、駐華盛頓司法事務(wù)報(bào)道記者(1955—1964)、倫敦記者站主任(1965—1972)、專欄作者(1969—2001),目前是《紐約書評(píng)》專欄作者。1955年、1963年兩度獲普利策獎(jiǎng)。劉易斯曾在哈佛大學(xué)執(zhí)教(1974—1989),并自1982年起,擔(dān)任哥倫比亞大學(xué)“詹姆斯?麥迪遜講席”教授,講授及時(shí)修正案與新聞自由。著有《吉迪恩的號(hào)角》(Gideon’s Trumpet)、《十年人物:第二次美國革命》(Portrait of a Decade: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言論的邊界:美國憲法及時(shí)修正案簡史》(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 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Amendment)。劉易斯的妻子是馬薩諸塞州較高法院首法官瑪格麗特?馬歇爾,兩人現(xiàn)居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
何帆,1978年生,湖北襄樊人,現(xiàn)為較高人民法院法官。著有《大法官說了算:美國司法觀察筆記》(法律出版社,2010)、《刑事沒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刑民交叉案件審理的基本思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譯有《九人:美國較高法院風(fēng)云》(上海三聯(lián),2010)、《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哈里?布萊克門的較高法院之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作為法律史學(xué)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聯(lián),2009)、《玩轉(zhuǎn)民主:美國大法官眼中的司法與民意》(法律出版社,2011)。主編有“美國較高法院大法官傳記譯叢”。曾為《南方周末》、《新京報(bào)》、《南方都市報(bào)》、《看歷史》雜志專欄作者。
及時(shí)章“關(guān)注他們的吶喊”
“社論式廣告”的來源形形色色,形式五花八門。人們?nèi)f萬沒有想到,1960年3月29日刊出的這則名為“關(guān)注他們的吶喊”的廣告,會(huì)在種族議題之外,掀起一輪更大的爭議,不僅成為對新聞自由的巨大考驗(yàn),并進(jìn)而演變?yōu)槊绹哉撟杂墒飞系囊蛔锍瘫?/p>
第二章蒙哥馬利的反擊
霍爾在《廣告報(bào)》上,發(fā)表了一篇?dú)鈩輿皼暗纳缯摚?ldquo;世上有兩類說謊者,一類主動(dòng)撒謊,一類被動(dòng)為之,這兩類說謊者在3月29日《紐約時(shí)報(bào)》的整版廣告中,粗魯?shù)卣u謗了蒙哥馬利市。”他叫囂道:“謊言,謊言,謊言,這就是些一心想募款的三流小說家捏造出來的故事,好欺騙那些偏聽偏信、自以為是,實(shí)際上卻屁也不知道的北方佬。”
第三章南方的憂傷
“那些從未感受過種族隔離之苦的人,很容易輕言‘等待’”,馬丁?路德?金寫道,“但是,當(dāng)你目睹暴徒對你的父母濫用私刑……當(dāng)你試圖向六歲的女兒解釋,為什么她不能像電視廣告里那樣在公園嬉戲玩耍,卻愴然詞窮……當(dāng)你駕車遠(yuǎn)行,卻發(fā)現(xiàn)沒有一家旅店愿意讓你留宿,而你不得不蜷在車上夜復(fù)一夜……當(dāng)你日復(fù)一日被“白人”和“有色人種”這樣的標(biāo)簽字眼所羞辱……你就會(huì)了解,‘等待’為什么對我們那么艱難。”
第四章初審失利
沙利文的律師讀到“黑人”一詞時(shí),故意讀成“黑鬼”,還說自己這輩子都這么念這個(gè)詞。法庭上,白人律師都被冠以“先生”頭銜,如“納奇曼先生”、“恩布里先生”。黑人們卻被稱作“格雷律師”、“克勞福德律師”、“西伊律師”。僅僅因?yàn)槟w色不同,他們居然連“先生”這樣的敬語都享受不到。更令人心寒的是,法官對這些統(tǒng)統(tǒng)置若罔聞。
第五章媒體噤聲
內(nèi)部人士透露:“《紐約時(shí)報(bào)》當(dāng)時(shí)正被內(nèi)部罷工和業(yè)務(wù)虧損折騰得焦頭爛額,要是輸了這些官司,報(bào)紙肯定會(huì)完蛋。”對于《紐約時(shí)報(bào)》根據(jù)憲法及時(shí)修正案提起的上訴,阿拉巴馬州較高法院用一句話直接駁回:“美國憲法及時(shí)修正案不保護(hù)誹謗言論。”只要每家法院都認(rèn)同上述論點(diǎn),《紐約時(shí)報(bào)》將永遠(yuǎn)無法勝訴。
第六章自由的含義
1797年,喬治?華盛頓即將卸去總統(tǒng)之位,告老還鄉(xiāng),費(fèi)城《曙光報(bào)》發(fā)文稱:“此人是我國一切不幸的源頭,今天,他終于可以滾回老家,再不能專斷擅權(quán),為害美國了。如果有一個(gè)時(shí)刻值得舉國歡慶,顯然就是此刻。政治邪惡與合法腐敗,將伴隨華盛頓的黯然離去而退出歷史舞臺(tái)。”政治漫畫家對華盛頓也毫不手軟,有人甚至把他的頭像安在一頭驢身上。
第七章言者有罪
共和黨人批評(píng)聯(lián)邦黨人偏好中央集權(quán)和英國政體,骨子里渴望著皇權(quán)專制。聯(lián)邦黨人則認(rèn)為,共和黨人就是一群雅各賓派,一旦得勢,必會(huì)推行法國式的恐怖政治。1798年,及時(shí)夫人阿比蓋爾?亞當(dāng)斯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親法集團(tuán),也就是共和黨人,正孜孜不倦地在全國“播下邪惡、無神論、腐敗和造謠惑眾的種子”。
第八章“人生就是一場實(shí)驗(yàn)”
1919年,年輕的漢德法官再次致信霍姆斯,認(rèn)為只有“直接煽動(dòng)”不法行為的言論方可追懲。他說,“既然案件發(fā)生時(shí),正趕上民意沸騰,這種情況下,讓陪審團(tuán)來判定某種言論的‘傾向’,恐怕效果不佳……據(jù)我所知,1918年的社會(huì)氣氛就是如此”。對此觀點(diǎn),聲望正如日中天的霍姆斯大法官頗不以為然。然后,五十年后,較高法院在“布蘭登伯格訴俄亥俄州案”中,卻正式采納了漢德的觀點(diǎn)。
第九章偉大的異議者
霍姆斯大法官風(fēng)流倜儻,對美酒佳人一向來者不拒。內(nèi)戰(zhàn)期間,他明知戰(zhàn)事殘酷,卻投筆從戎,三度負(fù)傷。他認(rèn)為社會(huì)改革運(yùn)動(dòng)難成大器,卻支持改革者們放手一試。布蘭代斯大法官向來不近煙酒,一生致力于推動(dòng)社會(huì)改革。霍姆斯習(xí)慣撰寫簡短有力,卻含義模糊的判決意見。布蘭代斯則喜歡長篇大論,分析各種社會(huì)問題。兩位性格迥異的大法官,在那個(gè)特殊時(shí)代,成為言論自由最堅(jiān)決的捍衛(wèi)者,和較高法院最偉大的異議者。
第十章“三天過去了,共和國安然無恙!”
在較高法院,明尼蘇達(dá)州助理司法總長詹姆斯?馬卡姆援引霍姆斯大法官1907年在“帕特森訴科羅拉多州案”的判決意見,認(rèn)為及時(shí)修正案只禁止“對出版的事前限制”。他話音未落,九十高齡的霍姆斯大法官突然插話:“寫那些話時(shí),我還很年輕,馬卡姆先生。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不這么想了。”
第十一章向較高法院進(jìn)軍
多年之后,韋克斯勒回憶道:“接下這個(gè)案子前,我對誹謗法沒什么了解。做案件背景分析期間,當(dāng)我意識(shí)到必須由被告來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時(shí),我受到極大震撼。那種感覺我至今記憶猶新,實(shí)在令人措手不及、驚懼不已。或許因?yàn)榕銓張F(tuán)在這個(gè)問題上一直比較溫和,過去,我一直以為誹謗法只是紙上談兵,根本沒有在這個(gè)國家適用過。”
第十二章“永遠(yuǎn)都不是時(shí)候”
“公民自由聯(lián)盟”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見書提出,連廣告言論都要追懲,恰恰說明對政治自由的打壓到了令人發(fā)指的地步。意見書寫道:“就算這是一起誹謗案件,可是,《紐約時(shí)報(bào)》僅僅因?yàn)橐粍t政治廣告,就涉嫌誹謗,并被判巨額賠償。如果連報(bào)紙都會(huì)因廣告中的無心之失而付出慘痛代價(jià),還有哪個(gè)異議團(tuán)體敢借助出版,表達(dá)他們對公共事務(wù)的看法?”
第十三章較高司法殿堂上的交鋒
沙利文的律師納奇曼堅(jiān)持認(rèn)為,《紐約時(shí)報(bào)》不作回應(yīng),就表示默認(rèn)。首法官沃倫因在“布朗訴教育局案”中推動(dòng)廢除校園種族隔離,近十年來,被南方人以各種方式惡毒謾罵、譏諷。他笑著說:“在較高法院,至少有一個(gè)成員,這些年被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攻擊謾罵,并指責(zé)他誹謗。如果他認(rèn)為自己沒有做這樣的事,是不是必須回信說明,或者承擔(dān)五十萬美金的判罰?”
第十四章批評(píng)官員的自由
雨果?布萊克大法官將意見草稿提交其他大法官傳閱時(shí),附了封親筆信給布倫南大法官。他說:“您當(dāng)然明白,除了我保留的立場和我的協(xié)同意見,我認(rèn)為您在‘《紐約時(shí)報(bào)》案’中的表現(xiàn)十分出色,在保障思想傳播的權(quán)利方面,您不僅恪盡職守,還向前邁進(jìn)了一大步。”
第十五章“這是值得當(dāng)街起舞的時(shí)刻”
后人多對這樣一個(gè)問題充滿好奇,如果沙利文當(dāng)時(shí)的索賠金額沒有那么高,《紐約時(shí)報(bào)》是否會(huì)不斷上訴?這場官司會(huì)被較高法院受理么?大法官們是否還會(huì)為此重新界定及時(shí)修正案的含義?在本案二十周年紀(jì)念研討會(huì)上,一審代表《紐約時(shí)報(bào)》出庭的埃里克?恩布里談及本案賠償金額時(shí),調(diào)侃納奇曼說:“這起案件能進(jìn)入較高法院,羅蘭居功至偉,如果他當(dāng)時(shí)只向我們索賠5萬美元,我們才懶得把官司打到那兒去呢。”
第十六章判決背后的紛爭
周一一大早,哈倫大法官就致信全體大法官,信中說:“親愛的弟兄們:我已通知布倫南弟兄,現(xiàn)在希望其他弟兄也知道,我已撤回自己在這起案件中的單獨(dú)備忘錄,并無條件地加入多數(shù)意見。”
第十七章連鎖反應(yīng)
福塔斯大法官單獨(dú)提出異議意見,他指出,越是對政府官員不利的報(bào)道,媒體越是應(yīng)承擔(dān)“查證真?zhèn)蔚牧x務(wù)”。末了,他意味深長地總結(jié)道:“公務(wù)員也是人啊!”
第十八章“舞已結(jié)束”
經(jīng)此一役,《電訊報(bào)》斗志盡喪,從此放棄報(bào)道政府的不法行為,并要求記者給任何采訪對象發(fā)函前,必先征求編輯意見,甚至銷毀了所有日后可能引發(fā)誹謗訴訟的信函、便條。一次,有人向《電訊報(bào)》爆料說,當(dāng)?shù)匾晃痪L涉嫌濫用職權(quán),編輯不僅放棄這一選題,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記者:“這次還是讓別人去冒險(xiǎn)吧。”
第十九章重繪藍(lán)圖?
第十章“三天過去了, 共和國安然無恙!”
1919年以來,較高法院內(nèi)部一直為如何界定及時(shí)修正案保護(hù)的“言論自由”爭論不休,但是,卻沒有人提到過與之并列的“出版自由”話題。“吉特洛案”中,多數(shù)方大法官贊同將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一并納入基本自由范疇,使之不得受聯(lián)邦及各州侵犯。然而,時(shí)至1930年,較高法院仍未審理過一起因報(bào)紙、雜志或書籍出版受限引起的案件。只有這類案件,才是檢驗(yàn)出版自由的試金石。
不過,1931年,較高法院終于迎來及時(shí)起重要的出版自由案件:“尼爾訴明尼蘇達(dá)州案”。十年后,大法官們又就“布里奇斯訴加利福尼亞州案”作出裁判,這也是一起關(guān)系到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重要判決。兩起案件的結(jié)果,均以5票對4票達(dá)成,而且都是維護(hù)表達(dá)自由一方獲勝。盡管多數(shù)方是靠“勉強(qiáng)多數(shù)”取勝,但是,兩起案件在憲法史上,都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對于正被警察局長沙利文提起的誹謗訴訟所困擾,并打算尋求憲法及時(shí)修正案保護(hù)的《紐約時(shí)報(bào)》來說,這些案件包含的表達(dá)自由價(jià)值,顯得尤為重要。
“尼爾訴明尼蘇達(dá)州案”的主人公杰伊 尼爾是名個(gè)性復(fù)雜的新聞人,熱衷揭露各類社會(huì)丑聞,俗稱“扒糞記者”。弗雷德 弗蘭德利在講述此案的《明尼蘇達(dá)小報(bào)》一書中,將尼爾描述成一個(gè)“反天主教,反猶太人,反黑人,反工會(huì)”的極端人士。1927年,尼爾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創(chuàng)辦周報(bào)《周六新聞》。這是份激進(jìn)的反猶太報(bào)紙,指責(zé)腐敗的警察局長與“猶太匪幫”沆瀣一氣,“暗地操縱著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切”。表面上看,尼爾是個(gè)不討人喜歡的角色,但弗蘭德利也發(fā)現(xiàn),此人疾惡如仇,常利用媒體的社會(huì)批判功能,挑戰(zhàn)大小權(quán)貴。弗蘭德利曾在福特基金會(huì)組織的一次餐會(huì)上,與朋友提到尼爾其人。鄰座的杜邦公司總裁歐文 夏皮羅湊巧聽到他們的談話,主動(dòng)搭話說:“你們討論的是‘尼爾案’么?我認(rèn)識(shí)尼爾先生。”夏皮羅的父親薩姆 夏皮羅,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經(jīng)營一家干洗店。當(dāng)?shù)貛蜁?huì)頭目巴內(nèi)特要求他停止?fàn)I業(yè),將干洗業(yè)務(wù)轉(zhuǎn)交他人處理。老夏皮羅拒不從命,巴內(nèi)特隨即派四個(gè)地痞闖進(jìn)店里,在客戶衣物上肆意潑灑硫酸。歐文 夏皮羅當(dāng)時(shí)才十一歲,躲在木制隔板后目睹了黑幫暴行。當(dāng)?shù)貓?bào)紙報(bào)道了這起襲擊事件,卻絕口不提巴內(nèi)特和他的無理要求。杰伊 尼爾從薩姆 夏皮羅那里得知此事后,在《周六新聞》上詳細(xì)披露了此事經(jīng)過。他不僅如實(shí)描述了巴內(nèi)特的所作所為,還痛斥其他報(bào)紙畏首畏尾,不敢點(diǎn)出黑幫頭目姓名。不久,巴內(nèi)特因這次襲擊事件被政府起訴,經(jīng)歐文 夏皮羅出庭指認(rèn),最終被送入大牢。
尼爾選擇批判對象時(shí),并非總是如此機(jī)敏。他最喜歡批評(píng)的官員之一,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海樂平郡檢察官弗洛依德 奧爾森。奧爾森其實(shí)是位自由派改革者,后來曾三度出任明尼蘇達(dá)州州長。但是,當(dāng)尼爾用污穢、下流的文字,接連向他“潑臟水”時(shí),奧爾森選擇了令自己日后追悔莫及的回應(yīng)方式:提起誹謗訴訟。他根據(jù)一部名為《防治公共滋擾法》的法律,將《周六新聞》告上法庭。“滋擾”其實(shí)是個(gè)法律術(shù)語,主要指騷擾鄰人的行為,如亂丟垃圾、制造噪音等。但是,這部法律格外與眾不同,居然將一些特定行為納入滋擾范疇,即任何經(jīng)營“惡意誹謗、毀人清譽(yù)的報(bào)紙者”,均構(gòu)成“滋擾罪”。法官審理此案后,根據(jù)《防治公共滋擾法》相關(guān)條款,判令《周六新聞》停止發(fā)行,永遠(yuǎn)歇業(yè)。其實(shí),州議會(huì)1925年制定《防治公共滋擾法》,就是為懲治一份名叫《德盧斯鋸報(bào)》的“扒糞類報(bào)紙”。不過,這部法律當(dāng)時(shí)并未遭到其他報(bào)紙反對,因?yàn)榇蠹移毡榍撇黄鹉切┙杞衣冻舐勚星迷p勒索之實(shí)的小報(bào)。1927年11月,弗洛依德 奧爾森向法官提出申請,要求勒令《周六新聞》停止?fàn)I業(yè),法官立即批準(zhǔn)。才發(fā)行了九期的《周六新聞》,就此關(guān)門大吉。
尼爾上訴至明尼蘇達(dá)州較高法院。他的律師提出,《防治公共滋擾法》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以及州憲法中的出版自由條款,但是,州較高法院簡單、粗暴地駁回了尼爾的上訴。大法官們一致認(rèn)為:“我們的憲法從未打算保護(hù)惡意誹謗、蓄意中傷他人的不實(shí)之詞,或者動(dòng)機(jī)不良、別有用心的出版物。憲法只對誠信、審慎、盡責(zé)的報(bào)業(yè)提供保護(hù)。憲法規(guī)定出版自由,不是為放縱那些居心險(xiǎn)惡者肆意妄為,正如它賦予人民集會(huì)權(quán)利,卻不容許非法集會(huì)或騷亂暴動(dòng)。”這番說辭,難免讓人聯(lián)想起聯(lián)邦黨人當(dāng)年為《防治煽動(dòng)法》的辯護(hù)。與那部法律一樣,即使被告證明自己陳述、報(bào)道屬實(shí),《防治公共滋擾法》一樣要求他們必須具有“善良動(dòng)機(jī)、正當(dāng)目的”。正如霍姆斯在“施維默案”中的異議意見所言,州政府在這里只支持“我們所贊同的思想”的自由。
表面上看,“尼爾案”已塵埃落定,再無回旋余地。杰伊 尼爾已耗盡家財(cái),沒有資力上訴至聯(lián)邦較高法院。然而,兩家立場有著天壤之別的機(jī)構(gòu),卻同時(shí)向他伸出援手,一家是大名鼎鼎的左翼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lián)盟”,一家是極右翼報(bào)紙《芝加哥論壇報(bào)》。該報(bào)發(fā)行人羅伯特 盧瑟福 麥考密克并不認(rèn)同“美國公民自由聯(lián)盟”的所作所為,卻狂熱信奉新聞自由理念。麥考密克認(rèn)為,《防治公共滋擾法》已嚴(yán)重威脅到出版自由。他極力游說,最終促成那些起初對尼爾的遭遇漠不關(guān)心的報(bào)業(yè)同行們團(tuán)結(jié)一致,通過了一項(xiàng)譴責(zé)《防治公共滋擾法》的決議,將這部法律稱作“對人民自由最嚴(yán)重的侵?jǐn)_”。
1931年1月,較高法院開庭審理“尼爾案”。尼爾的律師韋姆斯 柯克蘭向大法官們表示,即使報(bào)紙刊登針對公眾人物的誹謗性文字,也不能成為政府打壓報(bào)界的正當(dāng)理由。“只要有人為非作歹,報(bào)業(yè)自然會(huì)有所謂誹謗言論。”柯克蘭還舉例說,19世紀(jì),《紐約時(shí)報(bào)》揭露臭名昭著的政客鮑斯 特維德的腐敗惡行時(shí),后者“就援引類似法律對付過媒體”。代表明尼蘇達(dá)州政府出庭的,是該州助理司法總長詹姆斯 馬卡姆。
布蘭代斯大法官向他提問時(shí),特地將話題轉(zhuǎn)向腐敗議題。布蘭代斯詳細(xì)研讀過此案卷宗,連碩果僅存的九期《周六新聞》也曾一一過目。他問馬卡姆:“在這些文章里,編輯努力證明警匪勾結(jié),操縱賭場撈錢的事實(shí)。他們甚至點(diǎn)出了警察局長與不法官員的姓名……我們的確不知道這些指控是真是假,但我們很清楚,如果這種警匪一體的情況確實(shí)存在,將是許多城市的恥辱。這些報(bào)人孜孜以求的,無非是揭露更多被官方遮蔽的黑幕,這樣的言論都不能免責(zé),還有什么樣的言論可以免責(zé)?如果我們不允許人民討論這類事務(wù),公共安全如何得以保障?是的,在很多情況下,誹謗確實(shí)存在。但是,你總不能一面揭發(fā)罪惡,一面掩蓋作惡者姓名吧。很難想象,一家沒有任何言論免責(zé)特權(quán)的媒體,能夠擔(dān)當(dāng)起維護(hù)民主社會(huì)安危的重任。如果不給他們免責(zé)特權(quán),那么,還有什么工作配享這種特權(quán)?”
馬卡姆采取的訴訟策略,是繼續(xù)堅(jiān)持布萊克斯通的古舊觀點(diǎn),即出版自由只保護(hù)出版物不受事前限制,而《防治公共滋擾法》并未施加任何事前限制。他的意思是,明尼蘇達(dá)州的立法沒有要求任何人在出版發(fā)行前,必須取得官方許可,那才構(gòu)成彌爾頓當(dāng)年譴責(zé)的英國出版許可制。《防治公共滋擾法》只是規(guī)定,報(bào)紙發(fā)行后,如果確實(shí)刊載了誹謗言論,可由一名法官?zèng)Q定對其是否追懲或查封。而且,在出版許可制中,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的并非報(bào)紙發(fā)行人,而是政府。馬卡姆指出,根據(jù)布萊克斯通對出版自由的闡釋,及時(shí)修正案中的“出版自由”,只能解釋為禁止事前限制。他還援引霍姆斯大法官1907年在“帕特森訴科羅拉多州案”的判決意見,霍姆斯在這起案件中聲稱,及時(shí)修正案只禁止“對出版的事前限制”。馬卡姆話音未落,已經(jīng)九十高齡的霍姆斯大法官突然插話:“寫那些話時(shí),我還很年輕,馬卡姆先生,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不這么想了。”
P112-116
以“沙利文訴紐約時(shí)報(bào)”案為核心,介紹美國及時(shí)修正案如何被法官、律師、媒體、公民社會(huì)激活,從而使得“言論自由”這一精神在美國生根及成長。
——清華大學(xué)劉瑜教授推薦
關(guān)于言論自由的經(jīng)典之作……劉易斯以記者視角,將整段故事娓娓道來。……書中穿插大量逸聞趣事,更是彌足珍貴……劉易斯獨(dú)家獲得布倫南大法官珍藏的私人文獻(xiàn),將本案判決內(nèi)幕抽絲剝繭,緩緩展開……那些對較高法院關(guān)于言論自由的裁判感興趣者,此書值得一讀再讀。
——《紐約時(shí)報(bào)》
劉易斯的作品條理清晰,幫助讀者理解如何看待道德、法律價(jià)值間的沖突,不同利益的博弈,比如,法官應(yīng)當(dāng)如何在個(gè)人免遭誹謗的自由,和人民討論公共事務(wù)的自由之間進(jìn)行抉擇。
——《紐約客》
安東尼 劉易斯是講法律故事的高手,寥寥數(shù)語,就能讓普通讀者弄懂晦澀、復(fù)雜的法律程序……他以“《紐約時(shí)報(bào)》訴沙利文案”為引,系統(tǒng)梳理了美國言論自由的歷史……當(dāng)其他法律史學(xué)家為重現(xiàn)此案,忙著查找案件資料,推測當(dāng)事人原意時(shí),采訪扎實(shí)、資料翔實(shí)、語言生動(dòng)的《批評(píng)官員的尺度》已閃亮登場,成為這個(gè)領(lǐng)域最的著作。
——《華盛頓郵報(bào) 書世界》
主要講述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對于言論自由的理解和保護(hù),并用制度來保護(hù)了媒體的監(jiān)督作用。對于我們理解什么是言論自由,什么是憲法,什么是司法獨(dú)立都有很好的幫助,絕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兩度普利策獎(jiǎng)得主安東尼·劉易斯原著,暢銷譯作《九人》譯者何帆翻譯。“我想不出什么案子,能比這起案件更有利于促進(jìn)整個(gè)國家的思想交流了。”本書以在美國家喻戶曉的“紐約時(shí)報(bào)訴沙利文案”連線展現(xiàn)了200多年來美國言論自由的司法斗爭史,既理性而堅(jiān)定地闡述和捍衛(wèi)了批評(píng)之聲與新聞自由的真正價(jià)值,同時(shí),又一再冷靜地提醒我們,自由不可濫用。
教授希望人手一本的好書,我就買了一本,新聞學(xué)的學(xué)生都應(yīng)該看看的,我琢磨了很久的書,里面慢慢的都是筆記,還上臺(tái)講解了這本書。確實(shí)能夠被稱為一本經(jīng)典。
教授希望人手一本的書籍,里面做的筆記慢慢的,我看得很認(rèn)真,還特地上臺(tái)講解了這本書,印刷不錯(cuò),字跡清晰,推薦這個(gè)版本的。這本書確實(shí)能夠被稱為一部經(jīng)典。
通過本書,了解了言論自由在美國的起源、發(fā)展和現(xiàn)狀。書中有一句話“如果批評(píng)不自由,則贊美毫無意義”一針見血的指出了言論自由最大意義。一個(gè)國家不但要保障民眾的生存和發(fā)展,更要給民眾言論自由的權(quán)利。
紐約時(shí)報(bào)訴沙利文案絕對是新聞傳播史上的經(jīng)典案例,全書通俗易懂,讀起來也很有趣,強(qiáng)烈推薦
掩卷略思,仿佛食淮南之橘。該案個(gè)中委曲及深遠(yuǎn)影響,自然毋庸贅言。但這一切建立在如作者在篇尾所說的美國的“樂觀主義”之上,亦即官民法的良性互動(dòng)。而在我朝,看不到如此局面。官對民,民對官與法,都有著近乎完美的道德、素質(zhì)期待,這種期待如不能實(shí)現(xiàn),則必陷入紛爭動(dòng)亂,將對方和自己分別置于天平的兩個(gè)極端。
這本書是老師多次提到并且推薦我們看的,于是便買了回來,感覺很不錯(cuò)。作者通過這個(gè)極具典型性的案例給我們詳盡介紹了美國的言論自由,媒體的權(quán)利,讓我們對此有一些了解。總體上不錯(cuò)。
社會(huì)必須容忍適度的批評(píng),尤其是公權(quán)力,就更得容忍。中國的政府官員好像沒有這個(gè)習(xí)慣,但是必須讓他們學(xué)會(huì)這一點(diǎn)。如果沒有思想自由,沒有思想的競爭,又何來創(chuàng)造,何來社會(huì)進(jìn)步?本書是好書告訴我們應(yīng)該怎樣對待批評(píng)。
這本書圍繞著一個(gè)經(jīng)典判例加以深入討論,有助于我們理解言論自由與誹謗的邊界。中國也常有類似的事情的發(fā)生,而且還會(huì)在博客和微薄世界引發(fā)海量口水。但是,中國的發(fā)聲人如果能仔細(xì)看看此書,其聲音才能多少有點(diǎn)兒意思
1.若批評(píng)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2.達(dá)至心中至善的最好方式是不同思想的交流,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確定一種思想是否是真理,就應(yīng)該讓它在思想市場的競爭中接受檢驗(yàn);3.容許空氣中充滿不和諧的聲音,不是軟弱的表現(xiàn),而是力量的象征。
人權(quán),自由,在美國的法制體現(xiàn)的如此完善。何帆也是位了不起的律師,很感謝他翻譯了這么好的一本圖書。讓非專業(yè)人士讀起來也是相當(dāng)?shù)木省7浅O蛲绹囊恍┓ㄖ疲谕覀儌ゴ蟮淖鎳材芙梃b到一些精華,完善我國的法律制度。
推薦擁有!“我想不出什么案子,能比這起案件更有利于促進(jìn)整個(gè)國家的思想交流了。”本書以在美國家喻戶曉的“紐約時(shí)報(bào)訴沙利文案”連線展現(xiàn)了200多年來美國言論自由的司法斗爭史,既理性而堅(jiān)定地闡述和捍衛(wèi)了批評(píng)之聲與新聞自由的真正價(jià)值,同時(shí),又一再冷靜地提醒我們,自由不可濫用。
言論自由,國人經(jīng)過了從百年前辛亥革命后的擁有到以后黨國體制下的逐步喪失,再到近幾年部分擁有的過程。有無言論自由,從某種意義上,其實(shí)也就是能不能由公民自由的批評(píng)政府。看看國外的案例,更加堅(jiān)定我們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信心。
“若批評(píng)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在這樣特殊的一年里看這樣一本書,內(nèi)心可謂是百味雜陳。但無論如何,人們總能等待到能說話的那一天,被壓制的言論與無奈的心情,終將化作一聲憤怒的吶喊。
看了微信訂閱號(hào)上的推薦買的,是很好的精神食糧~正如本書的譯者,中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何帆所說,批評(píng)官員是一種健康的傾向。這不是鼓動(dòng)大家去批評(píng),但如果沒有批評(píng)的聲音,僅僅是贊美,反而是可怕的。
這是紐約時(shí)報(bào)一位在資深記者的力作,還原了歷史上的一樁訴訟,總體感覺還不錯(cuò),但因?yàn)橹杏⑽谋硎龅牟町悾虚g會(huì)有一些晦澀的東西不能傳達(dá)出來。從這本書中可知,美國的自由和民主也不是與生俱來的,也是經(jīng)歷了很長時(shí)間的斗爭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