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歐美研究中國史奇才史景遷的精裝中文簡體版作品之一;
2. 以深厚的史學功底,付諸精彩的文學筆法,通俗易懂;他的作品敏銳、深邃、獨特而又“好看”,讓他在成為蜚聲國際的漢學家的同時,也為成學術暢銷書的寫作高手。
3. 歷史文學、人物傳記相結合的典范之作。
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世界著名漢學家,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史氏以研究中國歷史見長(從他取名蘊含景仰司馬遷之意可見他對此專業的熱愛)。他以獨特的視角觀察悠久的中國歷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講故事”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他的觀察與研究結果。他的作品敏銳、深邃、獨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為蜚聲國際的漢學家的同時,也成為學術暢銷書的寫作高手。
ⅰ總序妙筆生花史景遷 / 鄭培凱鄢
xv代譯序 / 李孝悌
致謝
注釋中所用的縮寫
前
及時章 觀察者
第二章 土地
第三章 寡婦
第四章 爭斗
第五章 私奔的女人
結語審判
附錄
參考書目
代譯序
李孝悌
以我自己的了解,過去三十多年,美國學者在中國史研究的領域中,表現最突出的要算是中國近代社會史了。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否定個別學者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或其他領域中的貢獻。我們說西方學者在近代社會史的研究上有突出的成績,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學者自己過去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或者空白,或者雖有著述,卻乏善可陳。在這樣的環境下,西方學者的社會史研究,原本就容易收開疆拓土之功,并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再加上論證精密,分析細致,幾十年累積下來,在實證研究和理論創建方面,累積了可觀的成果,也讓我們對中國歷史有了全新的領會。
這個領域研究的主要課題,包括中國社會的性質、民眾叛亂、民間宗教、基層組織及地方社會。史景遷教授在二十多年前寫的這一本《王氏之死》,在類別上可以歸到地方社會這一項,但在風格和取徑上卻和其他的研究大不相同。后面這一類學者,像孔飛力(Philip Kuh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或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重在資料的分析和理論的建立,走的是標準的學院派厚重的經典著述傳統。本書作者則一向偏重于文學性的敘事,試圖通過高超的敘事技巧和敏銳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時空和人物的生命。這一點,在《王氏之死》上,表現得格外突出。
以資料而論,《郯城縣志》和其他幾個地方的方志,是本書的重要依據。這一類資料,在中國史研究中再普通不過,我們大多數以中文為母語的史學家信手翻過,不費吹灰之力,卻從不曾在這些看似因循呆板的資料中,看到任何可以大作文章的質材。黃六鴻的《福惠全書》,對細節的記敘有超乎一般官箴的異常興趣,但如果用在我們只看到事實卻看不到故事的學者手中,恐怕也就平白糟蹋掉了。本書使用的第三種資料《聊齋志異》,屬于虛構的小說,作者大量使用來建構清初山東地方民眾的心靈圖像,在二三十年前的美國漢學界,曾引起一些爭議。但從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場看來,這種歷史文獻和文學作品并冶一爐的手法,反而顯現了作者的創意和先見之明。
我們有大量關于中國近代區域和地方社會的研究,在看完了一串串真實的數字、圖表統計和長篇累牘的征引文字后,卻依然對被研究的社會、人民一無所知。史景遷教授使用的資料,看似簡單、平常,但通過他奇幻的敘事和文字,郯城這個三百多年前中國北方的一所窮苦的聚落,卻以那樣鮮明強烈的形象逼近眼前,久久揮拭不去。一直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1668年的那場地震,如何具有象征性地將我們帶進郯城的歷史。通過一幅幅鮮明的圖像和具體的描述,我們才真正進入我們曾經靠著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鄉村世界,真正走進這些人的生活和他們的苦難與夢幻之中。
我還記得,婦人王氏如何經由幾條可能的路線,和不知名的男子逃離郯城,又屈辱地回到歸昌老家的三官廟里,再被她一度遺棄的丈夫帶回那間四望蕭然的林前小屋。我永遠無法忘掉那一幕,王氏穿著軟底紅布睡鞋,躺在被白雪覆蓋的林間空地上。王氏短暫的一生和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一切不幸與喧擾,雖然就此落幕,卻在后世讀者的心中,留下永難磨滅的記錄。
在將原文還原的過程中,我們根據資料,在幾個地方做了些微的更動。史景遷、金安平教授夫婦和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鄒秀寶小姐,協助我們查證部分譯文,并取得1673年版的《郯城縣志》影印本,謹此致謝。
另外,就本書的翻譯體例,特予以說明如下:作者引用原籍文句處,短則以原文呈現,長則以白話譯出,以利讀者閱讀,原文則另置于書末附錄。
本書作者則一向偏重在文學性的敘事,試圖通過高超的敘事技巧和敏銳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時空和人物的生命。這一點,在《王氏之死》上,表現得格外突出。史景遷教授使用的資料,看似筒單、平常,但通過他奇幻的敘事和文字,郯城這個三百多年前,中國北方的一所窮苦的聚落,卻以那樣鮮明強烈的形象逼近眼前,久久揮拭不去。一直到現在……——李孝悌
史景遷文體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別具慧心,從不大張旗鼓,宣揚新的理論架構,卻在不經意處,以生動的故事敘述,展現了歷史人物與事件所能帶給我們的歷史文化思考。史景遷運用文學材料的歷史書寫,當然不是呈現實際發生的史實,不是婦人王氏的“信史”,卻可以引發讀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東,在歷史意識上觸及當時歷史環境的“可能情況”。——鄭培凱
這事一本用小人物的遭遇展現中國宏大歷史的一本書,寫作的角度很好,有貼近性,史景遷用大量的史料重現了清初底層民宗的生存狀態。但是,也許是因為沒有生長在中國的緣故。對中國社會的描繪總體感覺有些吃力。另外,邏輯上也稍顯混亂,這一點倒不如日本的井上靖。
之前沒讀過史景遷的書,買完這本后才查閱了一些關于著者的作品。這本書總體上來說不錯,引用各種資料還原了歷史,這種歷史不同于口述的歷史,也不同于正體史書的敘述,類似于文學類的表達,卻又恰到好處。之前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讀的是奇幻,史景遷讀出了歷史,贊。
等了好久,終于到手,準備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起讀。
一直很喜歡史景遷,這本書也算代表作了。包裝很好印刷也很好。
作為耶魯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史景遷對中國史有著獨到而深刻的見解。由小人物的故事寫大歷史,在同時又保留一定的學術高度,史景遷的作品與中國當下泛濫的歷史八卦類書籍有著明顯的對比。
書本有些折痕,原書內容不錯,自認為是史景遷最好的一本書
書的名氣比較大,出版社也算名社。內容還不錯,海外研究歷史常常從一個小角度切入(比如《萬歷十五年》《叫魂》等等),逐漸展開到全面的社會生活,而不像我們的教科書,動不動就先拿什么歷史唯物主義來嚇唬人。所以有機會還是多讀讀海外的史書,國內自49年之后的史書,或許至少有一半是**。
以一個小人物的的視角記錄了清初山東人民的悲慘生活
廣西師大出版社的理想國系列一直為我所向往,《王氏之死》沒有讓我失望。
寫的不錯,可讀性很好,不過內容嚴謹性略微不足。
進來想閱讀一些海外中國學名著,想要一窺史景遷先生的風采。
站在別人想不到或想得到但做不到的底層視角、用得上別人用不上或者不知怎么用的材料、寫得出別人寫不出的文采,這是我推崇史景遷的原因。
史景遷從一本地方志書入手,寫了一個特定時代的一個小人物,書中還寫了很多法律上面的內容,我沒有很仔細的研究,就這樣翻看過去的,因此不敢多加評論。但是,這套書裝幀不錯,印刷質量不錯,看著很舒服,我想,先買了再說吧。
這是我第一本歷史小說 在看天下看到推薦就買了 現在正在讀 感覺今天就能看完 。作者角度新穎 給人一種穿透感 而且譯的流暢 不知道為什么讀起來還有點搞笑…可能是因為古人被描畫的非常鮮活。
以深厚的史學功底,付諸精彩的文學筆法,通俗易懂;他的作品敏銳、深邃、獨特而又“好看”,讓他在成為蜚聲國際的漢學家的同時,也為成學術暢銷書的寫作高手。
讀國外漢學家寫的中國題材著作,往往能給人很深的啟示。這本書就是一個例子,寫的是小人物,小地方,漫長歷史中一個小小的浪花,陰暗角落一點小小的熒光。小人物王氏就這樣走入了讀者的腦海。挑戰帝王家譜式的正史。
史景遷的書大學時就看過很多本,這本也看過,但是看到當當上有活動,還是義無返顧的買了回來重新溫習。看他的書能讓我們撇開本民族固有的一些觀念去看待中國的歷史,有時候這樣看到的歷史可能會更真實更客觀
書名是王氏之死,書中大半是整段的聊齋志異,切題的內容只有兩章而已。如果說前面都是鋪墊構建那個時期的社會形態的話,那么這種構建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實在是有點多余了。我還是再看一遍叫魂吧。
很多人因為不懂史學,讀不懂這本書。史景遷此書具有開創意義,他將別人不會用和用不上的史料,用于歷史考察,于是《聊齋志異》都能用來反映當時社會的現狀。小處著眼的微觀史寫法,比王侯將相的宏觀論述更需要功力。書有點味道,印制不錯,翻譯不如從前的譯本。
最近看了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孔飛力的《叫魂》,再加上原來看的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和一些余英時的書,國外漢學搞得有聲有色,有方法有思想,學術著作也能深入淺出,李澤厚說中國學術界現在是有學術沒思想,國內的同行們確實應該加把勁不落人后呀
海登懷特在元史學中,講史學應當具有詩性的美感。此書在歷史哲學上,對我國史學工作者是一個警醒,必須要重新恢復史學的美感。單論本書,裝幀精美,以史證小說,尤其是結尾,亦真亦幻的高潮。但就美感來講,比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前朝憶夢》要差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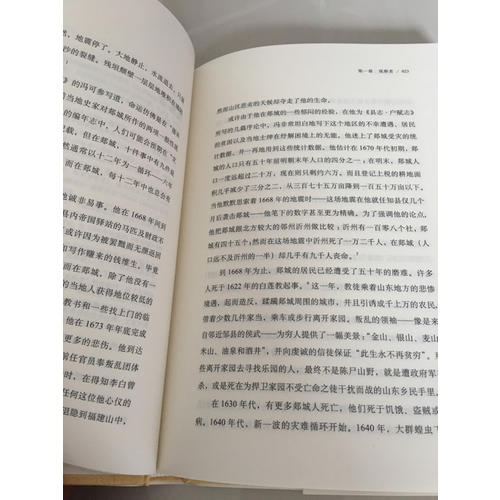 世界著名漢學家史景遷的作品,史學功底深厚,作品都比較精彩,是著名的漢學家。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這本書很不錯,而且是老師推薦讓讀的一本書。而且包裝也還行,書也比較薄。
世界著名漢學家史景遷的作品,史學功底深厚,作品都比較精彩,是著名的漢學家。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這本書很不錯,而且是老師推薦讓讀的一本書。而且包裝也還行,書也比較薄。
很喜歡封面的字體!非常喜歡!那個年代的外國學者的中文譯名都那么棒嗎?史景遷 在歷史研究上要景仰司馬遷 文筆非常不錯 哪怕是經過翻譯也能品味出其中的細微 視角非常獨特的歷史解讀 挺有意思的
我是在萬歷十五年里看到史景遷的名字,作者給予他很高的評價。史景遷對歷史可謂研精極慮。他的作品既能達到歷史的嚴謹,又不失閱讀的趣味性。是非專業人士的閱讀首選啊~~~~
很好的歷史書,雖然是美國人寫的,感覺比中國的更懂那個時代的中國。尤其好的是,作者把明末清初郯城的歷史與同時代的蒲松齡和他的書《聊齋志異》聯系在一起,讓人讀懂了《聊齋》。原來鬼怪的故事不僅僅是讓人恐懼,是有著產生的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