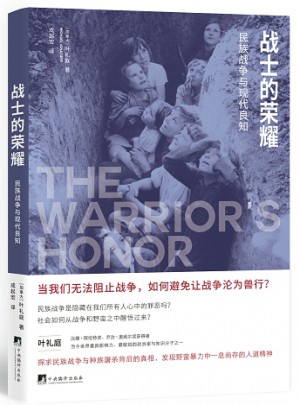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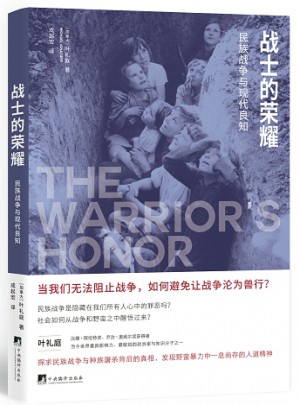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gè)世界,新的“民族戰(zhàn)士”(軍閥、歹徒與準(zhǔn)軍事部隊(duì))不斷涌現(xiàn),將戰(zhàn)爭(zhēng)推向一個(gè)前所未有的野蠻水平:數(shù)百萬(wàn)人死于內(nèi)戰(zhàn)與屠殺,平民與士兵毫無(wú)尊嚴(yán)地倒在槍口之下,暴力使昨日的鄰居變成今天的仇人。然而,事情非得如此嗎?
葉禮庭穿梭于各種民族戰(zhàn)爭(zhēng)景象之中,跟隨聯(lián)合國(guó)秘書(shū)長(zhǎng)探訪政盧旺達(dá)大屠殺背后的政治勢(shì)力,與國(guó)際紅十字會(huì)一起在阿富汗經(jīng)歷嚴(yán)重的人道危機(jī),在南斯拉夫見(jiàn)證兄弟間的仇恨……身處這些殘忍、血腥、反人道的戰(zhàn)爭(zhēng)之中,葉禮庭幾近絕望,但同時(shí)他看到了我們可能的出路:新的國(guó)際道德干預(yù)主義者(救援隊(duì)、戰(zhàn)地記者與外交官)試圖在世界范圍內(nèi)彌補(bǔ)人類(lèi)的身體與精神創(chuàng)傷,而“戰(zhàn)士的榮耀”準(zhǔn)則隨著一系列國(guó)際公約的簽署,在我們心中存續(xù),幫助我們從戰(zhàn)爭(zhēng)與野蠻中醒悟過(guò)來(lái)。
相關(guān)推薦: 《血緣與歸屬》product.dangdang.com/25155787.html
葉禮庭(邁克爾 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Ignatieff,1947—?):國(guó)際著名的學(xué)者、教授、作家,現(xiàn)為哈佛大學(xué)肯尼迪政府學(xué)院教授(Professor.of.Practice)、卡內(nèi)基倫理與國(guó)際事務(wù)委員會(huì)主席(Professor.of.Practice)。
目錄
導(dǎo)論 1
一、一切皆不神圣?電視的倫理學(xué) 5
I 5
II 6
III 12
IV 15
二、微小差異的自戀 20
I 20
II 23
III 27
IV 28
V 31
VI 36
VII 37
VIII 37
三、道德厭惡的誘惑 42
I 42
II 53
四、戰(zhàn)士的榮耀 65
I 65
II 77
III 84
IV 94
五、我們想要從中醒來(lái)的噩夢(mèng) 99
I 99
II 101
III 108
IV 110
V 111
來(lái)源索引 116
一、一切皆不神圣?電視的倫理學(xué) 116
二、微小差異的自戀 117
三、道德厭惡的誘惑 118
四、戰(zhàn)士的榮耀 119
五、我們想要從中醒來(lái)的噩夢(mèng) 120
索引 122
導(dǎo) 論
[3]1993年到1997年,我在現(xiàn)代民族戰(zhàn)爭(zhēng)的各種景象之中穿梭:到過(guò)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去了盧旺達(dá)、布隆迪、安哥拉,還到過(guò)阿富汗。我見(jiàn)過(guò)武科瓦爾[ 武科瓦爾(Vukovar),克羅地亞?wèn)|部城市,1991年前南斯拉夫內(nèi)戰(zhàn)期間,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在此展開(kāi)激戰(zhàn),整座城市變成廢墟。(本書(shū)所有注釋均為譯者注。)]、萬(wàn)博[ 萬(wàn)博(Huambo),安哥拉中西部省份。]和喀布爾(Kabul)的廢墟,奈阿盧布耶(Nyarubuye)[ 奈阿盧布耶(Nyarubuye),盧旺達(dá)城市。]教堂里的尸體,以及馬扎里沙里夫[ 馬扎里沙里夫(Mazar al Sharif),阿富汗第四大城市。]的孤兒。在檢查站,我遇到新型戰(zhàn)士:持有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自動(dòng)步槍的赤腳少年、戴弧形太陽(yáng)鏡的武裝分子、正在檢查槍支旁邊的祈禱跪墊、包裹頭巾的塔利班狂熱分子。
我展開(kāi)這些旅程,正巧是在新一波干涉主義的國(guó)際主義在海灣戰(zhàn)爭(zhēng)期間興起之后,又在這波國(guó)際主義于波斯尼亞退潮之前。我想找出是一種什么樣的道德團(tuán)結(jié)和傲慢的混合物,讓西方國(guó)家開(kāi)始這一推動(dòng)世界走向正確的短暫冒險(xiǎn)。是什么樣的沖動(dòng)讓我們?nèi)ケO(jiān)督緬甸的選舉,試著從薩達(dá)姆手底下保護(hù)庫(kù)爾德人,把聯(lián)合國(guó)部隊(duì)派遣到波斯尼亞,[4]恢復(fù)海地的民主,將安哥拉的戰(zhàn)士推上臺(tái)面?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話——仍舊聯(lián)結(jié)著也許是本書(shū)的大多數(shù)讀者和我所居住的安全地帶,與民族爭(zhēng)斗已經(jīng)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危險(xiǎn)地帶?
在此前的一本著作《陌生人的需求》(The Needs of Strangers)中,我關(guān)注的是在民族國(guó)家之中、在國(guó)內(nèi)環(huán)境下的陌生人之間的道德義務(wù)。在這里,我關(guān)注的是超越我們的部落,超越我們的民族、家庭、熟人網(wǎng)絡(luò)的道德義務(wù)。《戰(zhàn)士的榮耀》是關(guān)于一種沖動(dòng),那種當(dāng)我們?cè)陔娨暽峡吹侥硠t來(lái)自波斯尼亞、盧旺達(dá)或阿富汗的駭人報(bào)道時(shí),都覺(jué)得要“做點(diǎn)什么”的沖動(dòng)。為什么恰恰是我們中的一些人,會(huì)覺(jué)得對(duì)這些陌生人責(zé)無(wú)旁貸?除了偶然看到電視上播出的暴行圖像刺激我們采取行動(dòng),是哪種介入(involvement)的腳本和敘事,讓我們中的一些人承認(rèn)自己對(duì)那些人承擔(dān)義務(wù),而他們與我們毫無(wú)干系?
在十九世紀(jì),帝國(guó)的利益將兩個(gè)世界捆綁在一起:象牙、黃金和銅使得帝國(guó)的人深入黑暗之心[ 《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英國(guó)作家約瑟夫 康拉德的著名小說(shuō),敘述英國(guó)殖民者深入剛果河非洲腹地的故事。]。在冷戰(zhàn)的五十年間,如果某一個(gè)超級(jí)大國(guó)的人、間諜或是雇傭兵在一場(chǎng)特定的民族戰(zhàn)爭(zhēng)中出現(xiàn),那么對(duì)立的另一方也必定在那里現(xiàn)身。現(xiàn)在,不再有迫使安全地帶將危險(xiǎn)地帶視為自身事務(wù)的帝國(guó)競(jìng)爭(zhēng)或意識(shí)形態(tài)斗爭(zhēng)的敘事。剩下的是一種同情敘事,而這種變化無(wú)常的、模糊的關(guān)系正是我的主題。
為什么我們應(yīng)當(dāng)管遠(yuǎn)在半個(gè)世界以外、處于危險(xiǎn)中的人們的事情,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在人類(lèi)歷史的絕大多數(shù)時(shí)候,我們道德宇宙的邊界是部落、語(yǔ)言、宗教或民族的界限。僅僅因?yàn)橥瑢儆谝粋€(gè)物種,我們對(duì)于邊界以外的人類(lèi)就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義務(wù),這種理念是晚近的創(chuàng)造,是因?yàn)槲覀儙缀鯖](méi)[5]有做任何事情去幫助在本世紀(jì)[ 本書(shū)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本世紀(jì)指20世紀(jì)。]的恐怖實(shí)驗(yàn)和種族滅絕中死去的成千上萬(wàn)陌生人,從由此而產(chǎn)生的羞恥中覺(jué)醒的結(jié)果。這些實(shí)驗(yàn)沒(méi)有帶來(lái)任何好處,除了帶來(lái)一種意識(shí),即我們?nèi)际巧勘葋喫^的“天賦原形”:草味的人類(lèi),寒傖的、赤裸的兩腳動(dòng)物[ 莎士比亞劇作《李爾王》中的名句,譯文參考朱生豪譯本。]。正是“天賦原形”成了現(xiàn)代普世人權(quán)文化的主題——以及其基本理念。
以下文章探索這種新文化讓我們得以創(chuàng)造的道德聯(lián)系。部分文章是討論那些將陌生人的痛苦看作自己事務(wù)的西方人:激發(fā)他們介入的義憤和理想,緊隨介入而來(lái)的道德復(fù)雜性,以及常常伴隨心力耗竭和脫身之后的幻滅循環(huán)。這種介入是現(xiàn)代道德想象一個(gè)極重要的新特征。在十九世紀(jì),這些人可能是外交官、傳教士和帝國(guó)避暑山莊中的指揮官。現(xiàn)在,他們是援助人員、記者、戰(zhàn)爭(zhēng)罪行法庭的律師、人權(quán)觀察家,所有人都以一種無(wú)形道德理念的名義工作,即:不管其他人有多遙遠(yuǎn),他們的問(wèn)題都與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guān)。但幾乎每一個(gè)試圖按照這個(gè)理念生活的人都有一種糟糕的感覺(jué):沒(méi)有人能確定,我們的參與讓事情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壞;沒(méi)有人能確定,我們的參與應(yīng)當(dāng)擴(kuò)展到多遠(yuǎn);沒(méi)有人能確定,我們的承擔(dān)事實(shí)上有多么深入——畢竟,它們是通過(guò)電視傳播,而我們的參與可能是密集的,但卻浮于表面。康拉德的道德厭惡寓言——《黑暗之心》——仍然擁有令人不安的作用。
我的第二個(gè)主題是:一旦介入,我們將會(huì)面對(duì)什么?正在發(fā)生什么讓世界顯得如此危險(xiǎn)和喧囂?誰(shuí)是后現(xiàn)代戰(zhàn)爭(zhēng)的新建筑師,那些正在將1990年代的失敗國(guó)家撕裂的武裝分子、游擊隊(duì)員、民兵和軍閥嗎?[6]戰(zhàn)爭(zhēng)過(guò)去是在戰(zhàn)士之間進(jìn)行戰(zhàn)斗;現(xiàn)在,是非正規(guī)人員在戰(zhàn)斗。這可能是為什么后現(xiàn)代戰(zhàn)爭(zhēng)如此野蠻、為什么戰(zhàn)爭(zhēng)犯罪和暴行現(xiàn)在成了控訴戰(zhàn)爭(zhēng)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原因之一。
很不錯(cuò)的書(shū)
期待內(nèi)容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