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薦:
孤獨六講》是美學大師蔣勛的經典代表作,于初版十周年之際重磅回歸。新版收錄蔣勛親作長序——“做完整的自己”,與讀者再談生命個體的孤獨與完整。
殘酷青春里野獸般奔突的“情欲孤獨”;
眾聲喧嘩卻無人肯聽的“語言孤獨”;
始于躊躇滿志終于落寞虛無的“革命孤獨”;
潛藏于人性內在本質的“暴力孤獨”;
不可思不可議的“思維孤獨”;
以愛的名義捆縛與被捆縛的“倫理孤獨”。
這本書要談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獨,而是如何完成孤獨,如何給予孤獨,如何尊重孤獨。蔣勛以美學家特有的思維和情感切入孤獨,融個人記憶、美學追問、文化反思、社會批判于一體,創造了孤獨美學:美學的本質或許就是孤獨。
十年:《孤獨六講》跨越十年,已經成為一代人的文化經典。有人從中看到孤獨,也有人看到屬于自己的精神烙印。新版耗時長達兩年,于初版十周年之際,以全新面貌重磅回歸。
新版:蔣勛創作全新長序“不完整的自己”,并親作修訂全部內文。從裝幀設計到全書品質,均親自把關。精雕細琢,用真誠詮釋孤獨之美。
孤獨:蔣勛以一顆柔軟心,書寫讓我們內心安定的力量。與讀者談生命個體的孤獨與完整。也許很困難,也許還要很長時間的努力,但是,我們是否愿意試一試——做完整的自己。
經典:《孤獨六講》在華人世界創下百萬暢銷記錄,成為孤獨美學的代名詞。從明星到學者,無數人從中找到了共鳴。獨立面對世界之后,你更能知道它的價值。
裝幀:極簡裝幀,黑白灰三色清雅設計,賦予新版全新質感。
蔣勛,福建長樂人。1947年生于古都西安,成長于寶島臺灣。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1972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1976年返臺后,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并先后執教于文化、輔仁大學及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現任《聯合文學》社社長。
蔣勛先生文筆清麗流暢,說理明白無礙,兼具感性與理性之美,有小說、散文、藝術史、美學論述作品數十種,并多次舉辦畫展,深獲各界好評。近年專注兩岸美學教育推廣,他認為:“美之于自己,就像是一種信仰一樣,而我用布道的心情傳播對美的感動。”
新版序
自 序
情欲孤獨 021
語言孤獨 069
革命孤獨 111
暴力孤獨 157
思維孤獨 205
倫理孤獨 247
情欲孤獨 孤獨,是我一直想談論的主題。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每天早上起來翻開報紙,在所有事件的背后,隱約感覺到有一個孤獨的聲音。不明白為何會在這些熱鬧滾滾的新聞背后,感覺到孤獨的心事,我無法解釋,只是隱隱約約覺得,這個匆忙的城市里有一種長期被忽略、被遺忘,潛藏在心靈深處的孤獨。
我開始嘗試以另一種角度解讀新聞,不論誰對誰錯,誰是誰非,而是去找尋那一個隱約的聲音。
于是我聽到了各種年齡、各種角色、各個階層處于孤獨的狀態下發出的聲音。當社會上流傳著一片暴露個人隱私的光碟時,我感覺到被觀看者內心的孤獨感,在那樣的時刻,她會跟誰對話?她有可能跟誰對話?她現在在哪里?她心里的孤獨是什么?這些問題在我心里旋繞了許久。
我相信,這里面有屬于法律的判斷、有屬于道德的判斷,而屬于法律的歸法律,屬于道德的歸道德;有一個部分,卻是身在文學、美學領域的人所關注的,即重新檢視、聆聽這些角色的心事。當我們隨著新聞媒體喧嘩、對事件中的角色指指點點時,我們不是在聆聽他人的心事,只是習慣不斷地發言。
愈來愈孤獨的社會 我的成長,經歷了社會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小時候家教嚴格,不太有機會發言,父母總覺得小孩子一開口就會講錯話。記得過年時,家里有許多禁忌,許多字眼不能講,例如“死”或是死的同音字。每到臘月,母親就會對我耳提面命。奇怪的是,平常也不太說這些字的,可是一到這個時節就會脫口而出,受到處罰。后來,母親也沒辦法,只好拿張紅紙條貼在墻上,上面寫著“童言無忌”,不管說什么都沒有關系了。
那個時候,要說出心事或表達出某些語言,會受到很多約束。于是我與文學結了很深的緣。有時候會去讀一本文學作品,與作品中的角色對話或者獨白,那種感覺是孤獨的,但那種孤獨感,深為此刻的我所懷念,原因是,在孤獨中有一種很飽滿的東西存在。
現在信息愈來愈發達了,而且流通得非常快。除了電話以外,還有答錄機、簡訊、傳真機、e-mail等聯絡方式——每次旅行回來打開電子信箱,往往得先殺掉大多數的垃圾信件后,才能開始“讀信”。
然而,整個社會卻愈來愈孤獨了。
感覺到社會的孤獨感約莫是在這幾年。不論是打開電視或收聽廣播,到處都是call in節目。那個沉默的年代已不存在,每個人都在表達意見,但在一片call in聲中,我卻感覺到現代人加倍的孤獨感。尤其在call in的過程中,因為時間限制,往往只有幾十秒鐘,話沒說完就被打斷了。
每個人都急著講話,每個人都沒把話講完。
快速而進步的通訊科技,仍然無法照顧到我們內心里那個巨大而荒涼的孤獨感。
我忽然很想問問那個被打斷的聽眾的電話,我想打給他,聽他把話說完。其實,在那樣的情況下,主持人也會很慌。于是到,連call in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了,直接以選擇的方式:贊成或不贊成,然后在屏幕上,看到兩邊的數字一直跳動一直跳動……
我想談的就是這樣子的孤獨感。因為人們已經沒有機會面對自己,只是一再地被刺激,要把心里的話丟出去,卻無法和自己對談。
害怕孤獨 我要說的是,孤獨沒有什么不好。使孤獨變得不好,是因為你害怕孤獨。
當你被孤獨感驅使著去尋找遠離孤獨的方法時,會處于一種非常可怕的狀態;因為無法和自己相處的人,也很難和別人相處,無法和別人相處會讓你感覺到巨大的虛無感,會讓你告訴自己:“我是孤獨的,我是孤獨的,我必須去打破這種孤獨。”你忘記了,想要快速打破孤獨的動作,正是造成巨大孤獨感的原因。
不同年齡層所面對的孤獨也不一樣。
我這個年紀的朋友,都有在中學時代,暗戀一個人好多好多年,對方不知情的經驗,只是用寫詩、寫日記表達心情,難以想象那時日記里的文字會纖細到那么美麗,因為時間很長,我們可以一筆一筆地刻畫暗戀的心事。這是一個不快樂、不能被滿足的情欲嗎?我現在回想起來,恐怕不一定是,事實上,我們在學習著跟自己戀愛。
對許多人而言,及時個戀愛的對象就是自己。在暗戀的過程,開始把自己美好的一面發展出來了。有時候會無緣無故地站在綠蔭繁花下,呆呆地看著,開始想要知道生命是什么,開始會把衣服穿得更講究一點,走過暗戀的人面前,希望被注意到。我的意思是說,當你在暗戀一個人時,你的生命正在轉換,從中發展出的自我。
前幾年我在大學當系主任時,系上有一個女學生,每天帶著睡眠不足的雙眼來上課,她告訴我,她同時用四種身份在網絡上交友,每一個角色有一個名字(代號)及迥異的性格,交往的人也不同。我很好奇,開始上網了解這種年輕人的交友方式,我會接觸計算機和網絡也要歸功于她。
情欲的孤獨,在本質上并無好與壞的分別,情欲是一種永遠不會變的東西,你渴望在身體發育之后,可以和另外一個身體有更多的了解、擁抱,或愛,你用任何名稱都可以。因為人本來就是孤獨的,猶如柏拉圖在兩千多年前寫下的寓言:每一個人都是被劈開成兩半的一個不完整個體,終其一生在尋找另一半,卻不一定能找到,因為被劈開的人太多了。
有時候你以為找到了,有時候你以為永遠找不到。柏拉圖在《會飲篇》里用了這個了不起的寓言,正說明了孤獨是人類的本質。
在傳統社會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都以為找到了另外一半,那是因為一生只有一次機會,找對找不對,都只能認了。但現在不一樣了,如我的學生,她用四種身份在尋找,她認為自己有很大的權力去尋找最適合的那一半,可是我在想的是:是不是因此她的機會比我的多?
我是說,如果我只有一種身份,一生只能找一次,和現在她有四種身份,找錯了隨時可以丟掉再找相比,是不是表示她有更多的機會?我數學不好,無法做比較。可是我相信,如柏拉圖的寓言,每個人都是被劈開的一半,盡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學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解釋,但孤獨是我們一生中無可避免的命題。
“我”從哪里來? 后面我還會談到倫理孤獨,會從中國的儒家文化談起。儒家文化是最不愿意談孤獨的,所謂五倫,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系,都是在闡述一個生命生下來后,與周邊生命的相對關系,我們稱之為相對倫理,所以人不能談孤獨感。感到孤獨的人,在儒家文化中,表示他是不完整的。如果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那么在父子、兄弟、夫妻的關系里,都不應該有孤獨感。
可是,你是否也覺得,儒家定義的倫理是一種外在形式,是前述那種“你只能找一次,不對就不能再找”的那種東西,而不是你內心底層最深最荒涼的孤獨感。
“我可以在父母面前感覺到非常孤獨。”我想,這是一句觸怒儒家思想的陳述,卻是事實。在我青春期的歲月中,我感到最孤獨的時刻,就是和父母對話時,因為他們沒有聽懂我在說什么,我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而這并不牽涉我愛不愛父母,或父母愛不愛我的問題。
在十二歲以前,我聽他們的語言,或是他們聽我的語言,都沒有問題。可是在發育之后,我會偷偷讀一些書、聽一些音樂、看一些電影,卻不敢再跟他們說了。我好像忽然擁有了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私密的,我在這里可以觸碰到生命的本質,但在父母的世界里,我找不到這些東西。
曾經試著去打破禁忌,在母親忙著準備晚餐時,繞在她旁邊問:“我們從哪里來的?”那個年代的母親當然不會正面回答問題,只會說:“撿來的。”多半得到的答案就是如此,如果再追問下去,母親就會不耐煩地說:“胳肢窩里長出來的。”
其實,十三歲的我問的不是從身體何處來,而是“我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是關于生與死的問題,猶記得當時日記上,便是充滿了此類胡思亂想的句子。有24小時,母親忽然聽懂了,她板著臉嚴肅地說:“不要胡思亂想。”
這是生命最早最早對于孤獨感的詢問。我感覺到這種孤獨感,所以發問,卻立刻被切斷了。
因為在儒家文化里、在傳統的親子教養里,沒有孤獨感的立足之地。
我開始變得怪怪的,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出來。母親便會找機會來敲門:“喝杯熱水。”或是:“我燉了雞湯,出來喝。”她永遠不會覺得孤獨是重要的,反而覺得孤獨很危險,因為她不知道我在房間里做什么。
對青春期的我而言,孤獨是一種渴望,可以讓我與自己對話,或是從讀一本小說中摸索自己的人生。但大人卻在房外臆測著:這個小孩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有什么問題?為什么不出來?
張愛玲是個了不起的作家。她說,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清晨五、六點,你起來,如果不把房門打開,就表示你在家里做壞事。以前讀張愛玲的小說,不容易了解,但她所成長的傳統社會就是如此。跟我同樣年齡的朋友,如果也是住在小鎮或是村落里,應該會有串門子的記憶,大家串來串去的,從來沒有像現在說的隱私,要拜訪朋友前還要打個電話問:“我方不方便到你家?”以前的人不會這樣問。我記得阿姨來找媽媽時,連地址也不帶,從巷口就開始叫喊,一直叫到媽媽出去,把她們接進來。
儒家文化不談隱私,不注重個人的私密性。從許多傳統小說中,包括張愛玲的,都會提到新婚夫妻與父母同住,隔著一道薄薄的板壁,他們連晚上做愛,都不敢發出聲音。一個連私人空間都不允許的文化,當然也不存在孤獨感。
因而我要談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獨,而是如何完成孤獨,如何給予孤獨,如何尊重孤獨。
著名詩人席慕容曾這樣稱贊蔣勛:“是這個時代踏入藝術門檻的引路人。他為我們開啟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門窗,而是文化與歷史長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時光終將流逝,然而美的記憶長存”。
女神林青霞視他為“偶像”,稱他為自己的——“半顆安眠藥,能給予內心安定的力量。”
臺灣散文名家張曉風描述:“善于把低眉垂睫的美喚醒,讓我們看見精燦灼人的明眸。善于把沉啞喑滅的美喚醒,讓我們聽到恍如鶯啼翠柳的華麗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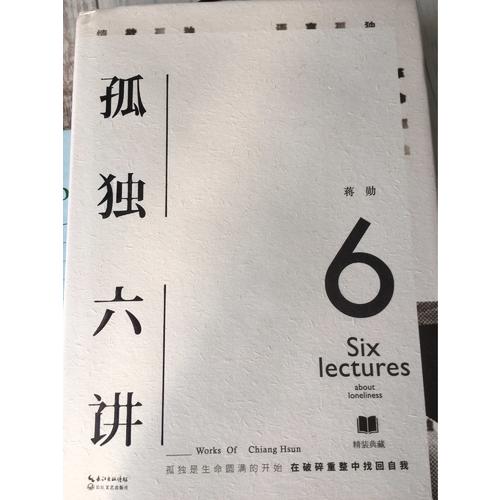 蔣勛把道理娓娓道來,不似狂風暴雨把你淋個渾身濕透,而是像一陣微風,讓你一點點的看到整個道理。講到有關在儒家思想中浸潤長大我們的骨子里所缺乏的東西,覺得很準確,還有人生來就是不完整的等等等等的東西,特別好,推薦推薦
蔣勛把道理娓娓道來,不似狂風暴雨把你淋個渾身濕透,而是像一陣微風,讓你一點點的看到整個道理。講到有關在儒家思想中浸潤長大我們的骨子里所缺乏的東西,覺得很準確,還有人生來就是不完整的等等等等的東西,特別好,推薦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