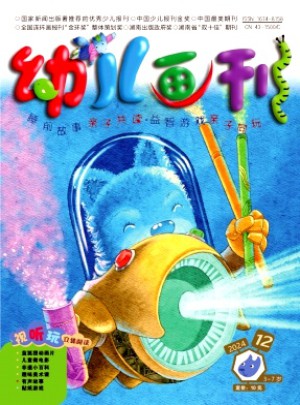引論:我們?yōu)槟砹?3篇幼兒繪畫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chuàng)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民間繪畫的文化內(nèi)涵和藝術形態(tài)代表著“民族文化群體的中國本原宇宙觀、美學觀、感情氣質(zhì)、心理素質(zhì)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反應了中國本原文化的哲學體系、藝術體系、造型體系和色彩體系。”從其文化內(nèi)涵和藝術形態(tài)可以看出民間繪畫具有內(nèi)容多樣、色彩豐富、構圖簡潔的特點。
1、內(nèi)容上———趨利避害、求吉納祥民間繪畫流傳于民間,是勞動人民在生產(chǎn)實踐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內(nèi)容囊括了生產(chǎn)勞動、衣食住行、人生禮儀、節(jié)日風俗等多個方面,蘊含著濃厚的鄉(xiāng)韻、鄉(xiāng)風、鄉(xiāng)情,且多運用諧音、象征等手法,通過典故、寓言故事,來表達吉祥、喜慶、教化的意味。如剪紙和刺繡圖案中常借鑒的一些中國傳統(tǒng)的吉祥紋樣:桃、竹、魚、蓮、牡丹、喜鵲等,幾種吉祥物象并置又會組合出如五福捧壽、三羊開泰、年年有余、金玉滿堂、喜報三元等吉祥寓意。民間繪畫中所表現(xiàn)出的吉祥意味,與中華民族自古流傳至今的“趨利避害、求吉納祥”的心理趨向息息相關。不僅如此,中國人民融合了集體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使作品體現(xiàn)出意味深長、生動有趣、雅俗共賞的特點。
2、色彩上———色塊豐富、自由奔放世間的色彩紛繁多樣,中國古人在很早的時候就將自然界中的色彩加以研究提煉,總結出了“五色論”———青、赤、黃、黑、白。民間繪畫中的用色,與中國傳統(tǒng)的五色論息息相關。首先,民間繪畫的色彩多為紅、黃、藍、綠這樣的飽和色,色彩純度高,色塊單純艷麗、鮮明飽滿,這充滿生命張力的色彩充滿著喜慶吉祥的韻味,使得其他色彩都黯然失色;其次,民間繪畫多運用色彩對比,如色相對比、冷暖對比和互補色對比等。有訣曰:“黃馬紫鞍配,紅馬綠鞍配,黃身紫花,綠眉紅嘴。”現(xiàn)代色彩理論指出,紅與綠,黃與紫是互補色,互補色并置會產(chǎn)生強烈的視覺沖擊力,且兩種顏色相互襯托更顯艷麗;再者,民間繪畫用色也會注重色塊的大小比例,通常是將一種顏色設為主體色彩基調(diào),其他顏色的小面積色塊起反襯和裝飾的作用。如具有中國傳統(tǒng)特色的黑紅搭配,在臉譜、春聯(lián)中經(jīng)常會運用,這樣的色彩搭配體現(xiàn)著朦朧的原始美感,具有現(xiàn)代裝飾色彩效果。
3、構圖上———畫面飽滿、散點透視中國民間繪畫的構圖主要分為兩種形式:一是采用與西方“焦點透視”相對應的“散點透視”,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視點可以自由游動,畫面飽滿,這在民間年畫中多有體現(xiàn);二是具有中國裝飾繪畫構圖特點,如剪紙紋樣中的太極式構圖。
三、民間繪畫理論對幼兒美術教育的作用及建議
1、提升幼兒審美能力中國民間繪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可以幫助幼兒提升發(fā)現(xiàn)美、鑒賞美和創(chuàng)造美的能力。首先,民間繪畫質(zhì)樸、率真,這不僅僅表現(xiàn)在物化的藝術語言上,而且要追溯到心靈的純真、樸實,“民間美術的率真使它的創(chuàng)造如童年的天真,既沒有裝腔作勢、無病,也沒有矯揉造作。”民間繪畫中所表現(xiàn)出的自然、質(zhì)樸與幼兒繪畫中異想天開的趣味相契合。在民間繪畫的熏陶下,幼兒的心靈得到凈化,創(chuàng)作時更加純粹、隨心所欲;其次,民間繪畫所采用的“散點透視”實則是無透視,這樣沒有規(guī)則和秩序,更有利于幼兒異想天開地表現(xiàn)事物,天上的、地下的、想象的、現(xiàn)實的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在畫面中;再者,民間美術色彩豐富、對比強烈,傳達出喜慶、生機、熱情和活力,幼兒開朗、活潑、生命力旺盛,這決定了他們更喜歡高純度強對比的色彩。我們可以根據(jù)幼兒的心理發(fā)展層次,創(chuàng)設富有民間美術色彩的生活與活動環(huán)境,通過藝術的滲透,增強幼兒對民間繪畫的情感。
篇2
收稿日期:2013-08-09
作者簡介: 白佩君(1971-),男,蒙古族,青海海西人,青海民族大學法學副教授,蘭州大學西北少數(shù)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學博士生。主要從事文化人類學、民族法學研究。
Discussion on Social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utter(Mar)
BAI Pei-jun
Abstract: Butter,called“Mar”in Tibetan language and“Tuolesi”in Mongolian,is a daily life necessity loved by Tibetan and Mongolian people in Tibetan-Qing Plateau. It is widely used in daily life,religion,art and medicine for its various functions and has become a highland cultural symbol. The paper explor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utter.
Key words: Butter;Diet;Cultural Symbol
飲食作為物質(zhì)文化,具有象征符號的性質(zhì)和特征,其功能包括人們對飲食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社會需要三重屬性。在人類活動的過程中,這種特殊的文化符號映射出差異性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提及青藏高原的乳制食品——酥油,人們往往會將其歸類為物質(zhì)文化的范疇進行理解,但在青藏高原的世居藏族、蒙古族等民族中,這種乳制品不單單表現(xiàn)出餐桌上的食用,而且還表現(xiàn)出禮儀交際、食療醫(yī)用、生產(chǎn)貿(mào)易等物質(zhì)載體的社會屬性以及與藝術審美的特征,具有行為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內(nèi)涵。正因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用途使酥油具備了多種文化屬性重疊的特點,成為了藏族、蒙古族等高原游牧民族特殊的文化符號,反映出迥異的民族文化內(nèi)涵。
一、酥油——高原游牧民族的特色食品
談到中國的飲食,人們總是精辟的概括道:南米北面,南甜北咸,東酸西辣。不同地區(qū)的民族由于地理區(qū)域與經(jīng)濟方式的不同,享用著差異性的食品。如同埃文斯·普里查德記述的努爾人[1]對于牛及奶制品的依賴一樣,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生活資料主要依賴畜牧肉食及奶制食品,在畜牧食品為主的飲食活動中,酥油隨之應用而生。酥油藏語稱為“瑪爾”(mar),是青藏高原藏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的食品精華。酥油是世界范圍內(nèi)游牧經(jīng)濟畜產(chǎn)乳制品的一種,是從牛、羊奶中提煉出的似西餐黃油的脂肪,營養(yǎng)價值頗高。即便是在食品結構較單一、冬季氣候寒冷的青藏高原牧區(qū),食用酥油能御寒暖胃、解渴潤肺,補充人體多方面的需要。由于酥油具備可塑性、發(fā)酵性、起酥性、融水性、可燃性等特性,是面粉類烘烤食品、手工藝品捏制、照明油料、飲茶等理想的原料油脂[2]。
酥油在青藏高原農(nóng)牧區(qū)的飲食結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酥油茶(周加 bsrubs ja )文化,千年來已深入到高原人的社會風俗、宗教禮儀和生活藝術等各個方面。根據(jù)《政教史鑒·附錄》中唐文成公主嫁入時帶去了內(nèi)地茶葉的記載,可知在藏族的飲食演進過程中,中原的茶葉與酥油結合,酥油茶隨即出現(xiàn)。酥油茶的飲法在牧區(qū)(卓巴 ‘brog ba)和農(nóng)區(qū)(絨哇 rong ba)和半農(nóng)半牧(絨瑪卓 rong ma ‘brog )有著迥異。①作為高原民族須臾不可離開的儀器飲品,盛酥油茶的器皿也非常注重。民間使用最多的是木碗,最好是藏式銀木碗或如意八寶玉制碗,不但具有防毒功能,而且彰顯華貴和飲茶品味[3]。由于游牧的機動性特點,為便于餐飲,牧區(qū)藏族、寺院僧人一般都隨身攜帶自用的木碗,隨時可拿出喝酥油茶、拌糌粑。這種特殊的習俗在衛(wèi)生條件局限的牧區(qū)防止了疾病的傳播。
酥油“糌粑”(rtsam pa),被藏民族公認為世界上最早出現(xiàn)的方便性食品之一,也使藏族成為世界上靠單一食物能夠生存的民族。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在青藏高原的探險之旅中生動描述“唐古特人”用碗做飯的情景,碗中做飯即指捏制糌粑。[4]糌粑由于油性較大,纖維細膩,消化較慢。為此,牧民早晨拌上一拌酥油糌粑,外出放牧既頂飽又便于攜帶。習慣酥油的味道,對于其他民族也是一種尚好的甜點小吃。酥油面點,即藏族用酥油炸制或調(diào)制的面餅類。藏歷年時面點種類很多,有酥油炸制的耳朵狀的“古過”、長形的“那夏”,還有青海藏族常吃的藏語稱“特”的水油餅,四川、東南部的藏族常吃巴差瑪爾庫(酥油澆面疙瘩)、瑪爾森(酥油面糕),②還有藏族及僧人常食用的大米、酥油、蕨麻、牛羊肉參合制成的蕨麻米飯等等。
飲食結構反映出一個群體的生活環(huán)境和生計方式,也確定了這一群體的生理特征和生活習性。民以食為天,在特定自然環(huán)境中解決肌體能量的前提下,生活群體在吃什么,怎么吃的嘗試中創(chuàng)造了豐富無比的飲食品種,在生產(chǎn)與消費食物的過程中又不斷融入了群體的智慧和文化底蘊,創(chuàng)造出了獨特的飲食文化圈。酥油不但成為高原藏族、蒙古族、土族的主要食品,而且在這一區(qū)域的回族、漢族等民族的飲食中也離不開酥油的影子,成為這一文化圈下各族共享的特色食品。
二、酥油作為物質(zhì)載體的社會功能
在青藏高原各民族飲食文化互動的過程中,酥油成為高原飲食文化圈下各族間社會化交融的一個紐帶,從生產(chǎn)加工、買賣經(jīng)營、食用餐飲、禮儀載體到醫(yī)療保健等方面都融入了高原不同民族的生活因子,帶動了社會文化各層面的流動,成為生產(chǎn)生活中的物質(zhì)載體。
(一)游牧生計方式下固有的生產(chǎn)者
作為乳制品的酥油,藏族、蒙古族等牧民成為固有的主要生產(chǎn)者。藏族傳統(tǒng)提煉酥油法俗稱“打酥油”,打酥油通常由婦女承擔。在打酥油的勞動中,婦女們甚至給勞動插上歌舞的翅膀,創(chuàng)造了許多勞動氣息的藏歌小調(diào),為其增添了藝術的色彩[5]。為便于保存和運輸,酥油往往被裝進牛羊肚兒中縫好,制成橢圓形皮囊裝存。提取完酥油后的奶渣“曲拉”(chur)可食用,分離出的“達曲”水可以喂牲畜,貧苦人家也有當飲料喝的。③
(二)變遷的生活方式,擴大的消費群體
在青藏高原,藏族、蒙古族以及藏傳佛教僧人成為酥油的主要消費群體。吐蕃時期由于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不平衡,酥油產(chǎn)量有限,顯得十分珍貴而成為上層社會的消費品。隨著畜牧經(jīng)濟的發(fā)展,酥油逐漸成為藏族等游牧民族的普及食品。到了近代,酥油仍是上層的主要飲食。例如舊的貴族階層盡管在飲食上比較講究,但每日的飲食仍舊離不開糌粑和酥油茶[6]。農(nóng)牧區(qū)的藏族、蒙古族、土族依然是酥油的主要消費群體,就連回、漢等民族也常常食用酥油。隨著生活方式的變遷,進入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大部分藏族、蒙古族每天也離不開酥油。筆者對10幾戶牧區(qū)退休后在西寧居住的家庭進行走訪,70%早晨常以酥油糌粑、奶茶為早餐,而90%的群體在通過禮儀、宗教祭祀等方面對酥油的功用仍然保留。特定的飲食結構中酥油成為必不可少的餐桌食品,常久伴隨在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生活周圍,又被賦予了禮品、祭品等功用,成為民族傳統(tǒng)的符號而得以保留。同時又被更多的群體所吸納,成為酥油的消費共享者。
(三)消費者與經(jīng)營人雙重身份的扮演
隨著畜產(chǎn)品成本的提高,酥油的價格近幾年也隨之不斷攀升,酥油生意的獲利不斷加大,穆斯林生意人的酥油買賣市場逐步繁榮起來,他們在自己食用酥油的同時,更成為主要的經(jīng)營買賣者,扮演了消費者與經(jīng)營人的雙重身份。筆者在對西寧市城東區(qū)共和路的韓某等幾位經(jīng)營酥油生意的穆斯林群眾(回族和撒拉族)的調(diào)查中得知,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寧城市居民多為漢族,對酥油的需求量不大,生意也很清淡。隨著近幾年農(nóng)牧區(qū)人口的城鎮(zhèn)化,特別是來自牧區(qū)藏族、蒙古族居住城市人口的攀升和消費群體加大使得生意紅火起來,店鋪增加到20幾家,上等酥油的價格由十幾年前的每斤5元左右漲到現(xiàn)在的50多元。
(四)禮物與通過禮儀中的價值
禮物饋贈織成了以個人和家庭為中心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維系和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7]。藏、蒙古、土族等民族常常用酥油作為禮物來傳遞敬重和表達禮儀。在卓倉藏族地區(qū)的婚禮儀式中,當“達其”(娶親牽馬之人)前往新娘家娶親時,新郎家要準備一方塊酥油和一條羊后腿肉,獻給新娘家,以示慰勞為新娘出嫁而操勞的家族老少。在婚禮儀式中,男方必須為前來吃席的女方家親戚制作一種碗口大小、形狀有點像草帽的圓形酥油叫“瑪爾國”,作為婚慶的象征性禮物展示于女方親戚面前,以示敬重。在卓倉的整個婚禮儀軌中,酥油處處可見,可謂沒有酥油就不成婚禮宴席。青海蒙古族在傳統(tǒng)節(jié)日、通過禮儀、歡慶豐收等活動敬酒祝酒時,在酒瓶或盛酒器皿上涂上一塊酥油敬給客人,客人按長幼依次用無名指粘償,從而成為一種特殊的待客禮儀。藏、蒙、土族等信徒到寺院進香禮佛或拜謝活佛高僧,以上等的酥油和哈達等物品作為禮品敬獻。可見,何種物品在什么樣的場合可以作為饋贈禮物并不是隨意的,而是經(jīng)過有目的的選擇,從而使禮物本身具有了文化的屬性。酥油在此展示了藏族、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的通過禮儀的規(guī)范,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饋贈過程中所蘊含的既定社會的內(nèi)在文化邏輯。
(五)食療醫(yī)用的功能
藏醫(yī)藏藥的治則和藥理主要依托于青藏高原這塊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因而,酥油常常被應用到藏醫(yī)藥用與食療之中,發(fā)揮了諸多功效。對于酥油的食用療效,《晶珠本草》早有記載。《四部醫(yī)典》中也詳細論述了酥油對人體的營養(yǎng)作用:“油類酥油芝麻髓和脂,味甘,后者重涼腹谷油。其性純細軟和又濕潤,老幼力小干瘦耗精血,瀉后勞神風害可裨益。[8]”在藏醫(yī)治療與藥用功能中,許多種病癥的治療都離不開酥油。如白酥油調(diào)制廣木香、雄黃、油松木等可治皰疹,高山柏子加融酥油煎后涂抹痔瘡處可治愈,還有治療黃水病的文官木酥油丸、治療痹病的蒺藜酥油丸、治理白脈病的三果酥油丸等等。也就是酥油具有強骨健腦、養(yǎng)胃健脾、潤腸通便、潤肺止咳等功效。另外,牧區(qū)藏族、蒙古族將酥油涂抹于臉上和手上,防止凍傷和曬傷,起到滋潤皮膚的作用。打完酥油提取曲拉后剩下的淺黃色達曲水,民間也常常作為醫(yī)用,孩子皮膚過敏或瘙癢時用其涂抹擦拭,具有止癢、解毒、消炎等功效。
飲食文化圈內(nèi)的特質(zhì)包括了食物生產(chǎn)行為,經(jīng)營行為,消費行為以及食物功能所延伸的食療醫(yī)用、禮儀習俗等社會化功能。酥油在蒙藏牧民的生產(chǎn)過程中體現(xiàn)出高原游牧經(jīng)濟文化特征;在穆斯林的經(jīng)營買賣中又呈現(xiàn)出民族貿(mào)易中的物質(zhì)載體的成分;不斷擴大化的消費群體,透視出高原游牧文化通過不同方式的向外延伸。在酥油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消費等社會化活動中,融入了不同民族對這一文化符號功能的體驗和認知,由而產(chǎn)生了不同的價值認同。藏、蒙、土等民族由于相同的和近似的生活習俗,酥油在這一群體的宗教活動、禮節(jié)表達和通過禮儀方面表現(xiàn)了特殊的蘊意。穆斯林經(jīng)營者在酥油的商品交換中加深了與藏、蒙等民族的溝通。更多消費群體在食療醫(yī)用、藝術鑒賞等文化共享背景下對酥油的認同,使之成為了各民族間文化互動的紐帶。
三、酥油蘊含的宗教與審美文化解讀
(一)酥油在宗教儀規(guī)和道場供奉中的角色
在藏傳佛教中將酥油視為圣潔之物。無論是活佛講經(jīng)弘法,僧人念經(jīng)修行,還是信徒供奉佛像、祈禱祭燈,都離不開酥油的影子。酥油燈帶來的是光明,在藏族、蒙古族的中占據(jù)著重要位置。格魯派認為,“光明是智力所固有的特征,由于我們一生中的所有思想狀態(tài)的這種光明,我們就可以看到、聽到和理解到智慧的目標[9]。”在寺院的法會和其他供奉儀式中獻燃百供(百盞酥油燈)或千供(千盞酥油燈),代表著深厚的信奉佛祖的蘊意。《塔爾寺志》中記載藏歷每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燃燈節(jié)(五供節(jié)),藏語音譯“安卻”(lnga mchod),燃燈節(jié)從二十五日起五天的時間中,對宗客巴大師的忌辰供養(yǎng),晚間在寺院僧舍屋頂燃燈供養(yǎng)。藏歷十一月初二,為班禪羅桑伯敦耶協(xié)的忌辰燃燈供養(yǎng),定為永葆常規(guī)[10]。點燈所需酥油由各噶爾哇(活佛院)自己開支,僧人所用酥油也由自己差分,這些酥油大多為信民朝拜提供所得。每個經(jīng)堂、佛殿專門由香燈師果尼爾④負責保證酥油燈干凈明亮、長明不滅。
在信仰儀式中,信民將酥油供奉于佛像之前以示進供、尊崇,煨桑及其它祭祀儀式也離不開酥油。特別是藏傳佛教藝術精華“酥油花”和祭祀禮儀中大量使用的“朵瑪”(gtor ma),均以酥油捏塑而成。“朵瑪”是用酥油、青稞炒面調(diào)和后用手工捏制的禮儀供品,上面常飾有酥油花制成的彩色圖案,形狀、顏色、大小也根據(jù)用途而不一。主要有三種形狀:一是供奉朵瑪,用于懷柔、增長及除障等儀式;二是錐形食用會供朵瑪,精神祝福的儀式舉行后將其切開分散食用,沾以福氣;三是神靈朵瑪,代表壇城的形象或符合某種神靈的“口味”[11]。有很多的文獻詳細記載了“朵瑪”的制作過程,說“朵瑪”至少有108個品種。例如一種叫做護地神“朵瑪”就是巨型供糕。還有青海黃南的山神祭祀中的葷祭和酥油糌粑制成朵瑪?shù)乃丶赖龋瑥挠枚洮敿漓胄郧楦鳟惖纳缴裰斜憩F(xiàn)出了人們在信仰供奉秩序中所確定的內(nèi)在邏輯。佛教寺院、藏族、青海河南縣蒙古族家中和場所莊嚴位置所供奉的“卓索切瑪”,是一種形同漢族傳統(tǒng)的五谷豐登斗,“卓索”(gro zhib)藏語意為麥子、谷粒,“切瑪”(phye mar)就是用酥油、白糖和糌粑做成的酥糕,特別是在藏歷新年等節(jié)日上,用染色五彩的麥穗、青稞、酥糕裝填裝飾切瑪斗,以示風調(diào)雨順,吉祥安康。青海德都蒙古人的“秀木乃”即是用炒面、奶皮、酥油、曲拉制成的供物,“秀木乃”中頂部酥油捏成太陽和月亮,代表日月同輝,中間堆積炒面代表地球雪山,四周擺放奶皮長條,曲拉裹邊表達四周方圓、五湖四海,可謂蘊意深刻。以上種種儀式與供物對酥油情有獨鐘,反映出酥油在宗教道場內(nèi)外的和儀式中的重要功用。
(二)酥油祭供品中的藝術審美
因宗教祭供而創(chuàng)造的酥油花是藏傳佛教藝術中的一種雕塑絕技,它是藏、蒙、土等多民族藝人的心血結晶。酥油在一定溫度下容易改變形狀,柔軟順滑、粘連吸附、光澤亮麗,是捏制手工藝品(酥油花)的尚好材料。加之酥油在藏區(qū)應用廣泛,久而久之,僧侶藝人們根據(jù)酥油的特性悟出了捏制工藝品的優(yōu)點,用酥油塑成佛祖、天神、人物、動物以及各種花卉草木、宮室建筑等形象,并有機地組合成佛經(jīng)以及重大歷史傳說故事的藝術品。民間傳說酥油花的緣起有文成公主說和宗喀巴托夢緣由說等。在藏傳佛教信徒看來,酥油花的繁榮景象乃是宗喀巴的夢境而已,所以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酥油花在展出后次日天亮之前必須全部焚燒完,以示曇花一現(xiàn)夢境的結束[12]。民國年間修《西寧府續(xù)志·志余》中對酥油花會的盛況就有記載:“五光十色,惟妙惟肖。架前燃銅燈百千萬盞,光輝相映,笙蕭和鳴。遠近觀者,人如山海”[11]。塔爾寺的酥油花在藏傳佛教寺院獨樹一幟,藝人們制作時為了保持手溫低于酥油的熔點,在青藏高原寒冷的冬季,邊制作、邊在刺骨的冰水中浸泡降低手溫,多年下來十指都不能伸展,有些甚至手臂殘廢。但他們深信,這就是心中有佛、自我修行、積累功德、超度眾生的完美實踐。除了酥油花被賦予了宗教和藝術展現(xiàn)的功能外,前面提及的顏色絢爛、造型各異的多瑪、切瑪以及秀木乃等酥油食用和祭供品,也展現(xiàn)了酥油被佛教僧人和民間百姓藝術化的文化氣息。
高原游牧文化的內(nèi)涵諸多方面關聯(lián)了宗教文化的內(nèi)容,這種文化通過宗教儀規(guī)、習俗、藝術等手段呈現(xiàn)出來并通過一定的載體加以表現(xiàn)。藏族、蒙古族、土族及寺院僧人在信仰中應用酥油以煨桑、供奉、祭燈等儀軌行為和多瑪、切瑪、酥油花等宗教物品來表達宗教活動。可以說,酥油除去飲食功能外,深深地植根于宗教場域之中,發(fā)揮了更廣泛的宗教文化載體的功能。同時,由于對信仰的虔誠和宗教活動呈現(xiàn)物的敬重,往往將呈現(xiàn)物精心美化,顯其柔美與莊嚴,達到了藝術品味的效果,從而被更多的信眾和其他群體樂而接受。不難看出,酥油在宗教活動載體、大眾藝術熏陶及宗教文化傳播中表現(xiàn)出了重要的功能。
四、酥油文化符號下的民族認同與文化共享
(一)酥油文化固有民族的族群認同
外來文化、現(xiàn)代化對高原游牧民族傳統(tǒng)文化帶來了挑戰(zhàn)和沖擊,在這一沖擊下的族群互動中,藏族、蒙古族在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也竭力保持著傳統(tǒng)游牧文化中最具民族特征的元素。如富有青藏高原民族特色食品的酥油,盡管從經(jīng)濟價值和外觀來看,無法與包裝精美的現(xiàn)代高雅食品相提并論,但在千百年的歷史過程中已延伸和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被賦予了特殊的文化象征意蘊。在藏漢民族的互動中藏族對酥油的態(tài)度,除作為特有的傳統(tǒng)食物外,還具有巴斯所認為的“一個群體(族群)通過強調(diào)特定的文化特征來限定‘我群’的‘邊界’以排斥他人”[14]的表現(xiàn)族群邊界的象征意義。吃酥油與不吃酥油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互動中構成了“我群”與“他群”之間不同的族群性特征。筆者與一位牧區(qū)藏族朋友聊天時對我說,“如果你會吃酥油糌粑,就很容易學會藏語,不吃酥油糌粑的人是講不好藏語的。”細細想來,話語背后的涵義應該是一個非藏族的“外來者”吃不了牧區(qū)傳統(tǒng)食品就很難真正融入到他們的生活圈子中。在藏族家中,對于熱衷于肯德基、麥當勞的孩子而言,多數(shù)家庭的早餐主食仍就擺上酥油、糌粑,家長們的民族情感中認為不吃酥油糌粑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藏族,吃酥油糌粑是強化年輕一代民族認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是進行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同時,每逢藏歷新年、佛教節(jié)日點燃酥油燈,全家老少定期攜帶酥油到寺院轉經(jīng)點燈,節(jié)日家中進行切瑪供奉等宗教禮儀,強化了年青一代的民族認同感。老年人更是堅定認為食用民族傳統(tǒng)食品酥油對人身體的好處,暫且不談營養(yǎng)學的觀點,從傳統(tǒng)觀念和習俗中窺視出族群心理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又使得傳統(tǒng)的飲食習慣得以保留和延續(xù)。
(二)酥油在族群互動中的文化共享
多年前,青藏高原之外群體的確較難接受酥油、糌粑、羊肉等民族傳統(tǒng)食品。他們對酥油糌粑的感覺,一如美國學者鮑大可對酥油糌粑的評價:“它有些像波特蘭水泥,對于我的舌苔來說,它的味道也像是我想象中波特蘭水泥的味道。”[15]前來高原觀光的內(nèi)地客人初到寺院,對酥油的氣味表現(xiàn)不適應,即便是在藏家做客時,很少主動要求吃糌粑、喝酥油茶,更不會把它們當作自己的日常飲食。主位和客位的觀點都認為,酥油糌粑是青藏高原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特有的食品,非青藏高原民族的“他者”是較難接受酥油的。隨著各民族文化習俗的進一步交融,經(jīng)濟社會和飲食互動的發(fā)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構建使不同民族的飲食品味與習慣相互交織和重疊,酥油作為高原民族食品特產(chǎn)逐漸被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外的群體購買食用。而在同一文化圈下,除游牧群體外被更多的他者接受并共享酥油所延伸的通過禮儀、藝術審美、食療醫(yī)用等社會與精神文化,表現(xiàn)出群體間的相互尊重和認同,可以說,酥油文化的共享拉近了不同民族間的交流情感。
綜上所述,酥油首先具有食用的飲食功能。從生產(chǎn)食用來滿足特定環(huán)境下生活群體的生理機能需求到消費用途、經(jīng)營買賣、醫(yī)用保健、藝術品味的過程中,融入了不同民族的生活習慣、生計方式和傳統(tǒng)思維定式的成因,反映出飲食文化社會化的特征。同時,特定群體在宗教、禮儀、藝術等精神生活中對它的依賴,使其成為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符號,表現(xiàn)出了特殊的蘊意。其次,在各民族文化互動過程中和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下被賦予了民族認同的象征意義。吃不吃酥油糌粑不僅是飲食習慣問題,也是區(qū)別青藏高原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與其他群體的文化邊界和民族身份的標志。酥油文化符號的民族性特征強化了他們的民族歸屬感以及“我群”和“他群”的區(qū)別。象征了“我群”之中老與少的代際差異,城市與農(nóng)牧區(qū)之間的身份之別,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時空距離。再次,隨著高原游牧文化圈內(nèi)外各族文化習俗的交融,不同群體對酥油文化的共享,拉近了不同民族間的交流情感和相互認同,從而增進了各族文化間的互動與互補。最后,酥油雖在食用之外更多體現(xiàn)了社會文化符號的功能,但就飲食層面而言,他的消費群體的限定性映射出在高原少數(shù)民族游牧文化與漢地文化長期的交流和互動過程中,漢地對待游牧飲食文化常常伴有體驗和獵奇的因素,一些畜牧食品被漢地所接受,但更多的還是呈現(xiàn)出單向的流向,即漢地飲食文化對游牧民族飲食結構、飲食活動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反過來看,處在同一地域空間的漢族卻很少接受游牧文化特別是藏族飲食文化中的成分,這也是今后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課題。
注釋:
①酥油茶的一種飲法是將燒開的磚茶水與酥油在專用的酥油桶中充分攪和,使茶油一體,稍加鹽,然后倒入陶制或金屬制的茶壺中,加熱(但不能燒開)后飲用。茶味的濃淡、酥油的多少及咸淡,因人而異,這種飲法在藏族牧區(qū)(卓巴 brog ba)民眾中比較普遍。另一種飲法比較簡單,即在碗中加入一塊酥油,大小隨個人需求而定,再添入燒開的磚茶或牛羊奶茶化開酥油后直接飲用,農(nóng)區(qū)(絨哇 rong ba)和半農(nóng)半牧(絨瑪卓 rong ma brog )民眾飲用普遍。
②“巴差瑪爾庫”是藏語,意即麥面湯圓,是藏族“生活美滿”的代名詞,如熟人相遇,一方問:“今天吃什么?”笑答:“巴差瑪爾庫!”即“吃最好的。”
③提取完酥油后桶中的奶水稱作“達拉”(dar ra),倒入鍋中燒開,即有塊狀物質(zhì)分離出來,濾出曬干即成奶渣,叫“曲拉”(chur)。剩下的水變清,稱作達曲。
④果尼爾:僧人,負責供奉酥油燈和圣水,管理佛殿法器、佛經(jīng)、佛像及財物等。
參考文獻:
[1][英]埃文斯·普里查德.褚建芳等譯.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
[2]喻峰,熊華,呂培蕾.酥油營養(yǎng)成分及營養(yǎng)特性分析研究[A]//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四屆年會論文摘要集[C].2005:142~145.
[3]何心,付興華.木碗相隨似情人[J].中華手工,2010,(1).
[4][俄]普爾熱瓦爾斯基.荒原的召喚[M].王嘎,張有華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2.
[5]陳立明,曹曉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29.
[6]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3:209.
[7]閻云翔.禮物的流動[M].李放春,劉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0.
[8]宇妥·云丹貢布.四部醫(yī)典(《甘露精要八支秘訣續(xù)》)[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1983:63.629.
[9][意]圖齊.宗教之旅[M].耿昇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84.
[10]色多·羅桑崔臣嘉措.塔爾寺志[M].郭和卿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191.
[11]羅伯特·比爾.藏傳佛教象征符號與器物圖解[M].向紅笳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222.
[12]楊貴明.塔爾寺文化[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195.196.
篇3
2.1在感知物體色彩方面具有敏銳性、豐富性。幼兒只對具有較強視覺刺激的色彩感興趣,較多地注意色彩對比強烈、顏色鮮艷豐富的物體。如:在組織幼兒觀察花和樹時,幼兒明顯地對五顏六色、色彩鮮艷的花感興趣一些,會停下來欣賞它,有感知它外形、色彩的興趣。在教學活動出示教具時,色彩對比強烈、顏色鮮艷的教具比色彩暗淡的教具更易引起幼兒的注意,更易激起幼兒感知的興趣。
2.2每個幼兒都具有自己的個性,在對色彩的審美感知上,幼兒有自己的偏好性。在感知色彩時,幼兒會特別關注自己中意的顏色,而忽視了對其它顏色的審美感知。在創(chuàng)造表現(xiàn)時幼兒會較多的用自己喜歡的顏色來表現(xiàn)物體的色彩。如:有的幼兒喜歡紅色,他在觀察物體時就會較多地去感知紅色的物體;有的幼兒喜歡藍色,他在生活中就會有意識地去尋找并感知藍色的物體;有的幼兒喜歡黃色,他在繪畫創(chuàng)造時就會大面積地用自己喜歡的黃色來表現(xiàn)物體的色彩。
2.3幼兒對物體的感知興趣、繪畫興趣有時也受情緒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情緒性。在高興、求知欲強時,幼兒對顏色鮮艷、對比強烈的事物感興趣,有用它表現(xiàn)自己情緒的愿望;在傷心、難過時,幼兒對顏色較暗、色彩協(xié)調(diào)的事物感興趣,有用它表現(xiàn)自己情緒的愿望。
3激發(fā)幼兒繪畫興趣的原則
3.1從注入式轉向啟發(fā)式。在活動中注意啟發(fā)幼兒的主體性、主動性,提供幼兒自我表現(xiàn)的機會,積極鼓勵幼兒用自己的表現(xiàn)方法;啟發(fā)幼兒的審美能力,提供豐富的視覺環(huán)境;啟發(fā)幼兒的創(chuàng)造能力,運用各種創(chuàng)造性的方法,引導幼兒的創(chuàng)作。
3.2從單純注重作業(yè)活動轉向審美活動的全過程。幼兒的美術活動不應單純地限制在課堂上,更不能單純地為完成一次作品而活動。在研究過程中重視整個活動的過程,在活動中,關心每個幼兒是不是感到有興趣,積極性高不高;能力強的、能力弱的是不是都在活動,是不是都得到發(fā)展等。只要孩子在興致勃勃地活動,就可以借助教學促進幼兒的自信心、求知欲、審美欲和創(chuàng)作欲。
3.3從單純模仿,以象不象看待幼兒作品轉向讓幼兒自由發(fā)揮,大膽想象。由于小班幼兒的觀察力、雙手協(xié)調(diào)動作不完整,幼兒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力異常豐富,千奇百怪,想怎么畫就怎么畫,絕不考慮自己想的與實際情況是否相吻合。于是幼兒的畫線條不直、歪歪扭扭、比例不正確、造型不完整、只是大致相似,甚至很不象樣。這時及時給予幼兒作品充分的肯定,不以成人的觀點說些帶有批評的話,因為那樣會挫傷幼兒的積極性,失掉繪畫興趣,引起厭煩情緒。耐心地引導,大膽鼓勵幼兒自由地發(fā)揮,表揚他們的所見、所想、所希望的事物,充分了解幼兒的創(chuàng)作意圖。幼兒在得到老師的鼓勵和支持后,才會感到他的畫是有意義的,繪畫的興趣更濃,進步更快。
4激發(fā)幼兒繪畫興趣的措施和方法
4.1措施。(1)題材內(nèi)容新穎。一定要選擇幼兒生活中熟悉的、感興趣的、具有較強吸引力的題材。幼兒喜歡動物,無論是小動物,還是大動物。幼兒喜歡色彩鮮艷、對比強烈的東西,如:紅旗、花、氣球等。幼兒吃的五顏六色的蔬菜、水果,如:蘋果、香蕉、蘿卜等。這些都易引起幼兒感知的欲望,繪畫的興趣。(2)形式活潑多樣。游戲能激起幼兒參與活動的興趣。利用多種玩色游戲、色塊拼圖、色彩填色、講故事、猜謎語等游戲形式,激發(fā)幼兒對色彩的興趣,對繪畫的興趣。
4.2方法。(1)相似聯(lián)想激趣法。同一物體聯(lián)想出不同姿態(tài),顏色、形狀相同或相似物體的聯(lián)想,可以激起幼兒表現(xiàn)物體的興趣。把所要畫的物體的主要特征概括為幼兒能理解的幾何圖形,啟發(fā)幼兒想象同一物體的不同姿態(tài)或與之顏色或形狀相同、相似的物體。這樣幼兒既有表現(xiàn)不同物體的興趣,又使幼兒有選擇地進行繪畫。(2)過程激趣法。重視幼兒在表現(xiàn)物體過程中審美感知、色彩運用等各方面的發(fā)展,肯定幼兒的作品,激發(fā)幼兒繼續(xù)感知與創(chuàng)作表現(xiàn)的興趣,不過分注重結果的效果。因為小班幼兒雙手協(xié)調(diào)動作不完整,創(chuàng)造性和想象力異常豐富、千奇百怪,創(chuàng)作無意識、不穩(wěn)定,幼兒最終的作品效果也許不如過程中好。(3)角色激趣法。把他們放入某個角色中、配以某種身份,使他們以角色的身份、游戲的方式進入繪畫活動中,帶著某種任務去參與活動,更有興趣,堅持性更好。
5幼兒繪畫興趣發(fā)展的三性
篇4
關 鍵 詞:體育史;英文“physical education”;法文“education physique”;杜博斯;盧梭
中圖分類號:g81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13)01-0020-04
國內(nèi)學者普遍認為,英語physical education來源于法語education physique,是education physique的譯詞。但對于英語何時和在什么文獻出現(xiàn)physical education以及法語何時和在什么文獻出現(xiàn)education physique,長期以來國內(nèi)的研究看法并不一致。
關于physical education最早何時在英語中出現(xiàn)以及出現(xiàn)在什么文獻之中,我國學者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1863年由英國的麥克拉仁(archibald maclaren,1819?-1884年)首先采用,但未說明具體出處[1]。一種認為最早出現(xiàn)在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著作中,但未說明具體時間和出處[2]。
關于法語何時和在什么文獻出現(xiàn)education physique,我國的已有研究都認為最早出現(xiàn)在1760年代,但對于具體時間和出處卻看法不一。有的認為最早出現(xiàn)在1760年法國的報刊上,但未指出具體時間和出處[3];有的認為出現(xiàn)在法國1760年有關兒童教育的著作中,但同樣未指出具體時間和出處[4];有的明確指出出現(xiàn)在1762年日內(nèi)瓦人巴勒克澤爾(jacques ballexserd,1726-1774年)用法語發(fā)表的《論兒童的身體教育》[5];還有的認為最早出現(xiàn)在盧梭1762年出版的名著《愛彌兒》[6],但均未給出任何論據(jù),也并未做出任何論證,從而表明這兩部著作確實使用而且是在歷史上首次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本研究通過以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為關鍵詞檢索了“早期英文圖書在線數(shù)據(jù)庫”(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①“十八世紀作品在線數(shù)據(jù)庫”(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②“《泰晤士報》數(shù)字檔案(1785-1985)”(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1785-1985)、③“十八世紀期刊在線數(shù)據(jù)庫”(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s portal)、④google books、⑤artfl project、⑥gallica數(shù)字圖書館⑦等英文和法文歷史文獻在線數(shù)據(jù)庫,查找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的歷史文獻,發(fā)現(xiàn)了新的史料對這兩個問題提出新的看法,并談一談對國內(nèi)已有研究涉及的若干問題的認識。
1 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現(xiàn)時間
1.1 physical education的最早出現(xiàn)時間
在上述數(shù)據(jù)庫和數(shù)字圖書館收錄的英文文獻中,最早使用physical education這一術語的是法國學者杜博斯(jean-baptiste dubos,1670-1742年)的法文著作《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第5版英譯本的第2卷,譯名為《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and painting》,譯者為托馬斯·紐金特(thomas nugent,生卒年和生平不詳),于1748年在倫敦出版[7]。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是一部比較藝術學著作,書名直譯為《詩歌和繪畫的批判性反思》,也被譯為《詩畫論》,第1版于1719年在巴黎出版,后多次修訂、擴充、再版。
據(jù)文獻檢索,physical education在托馬斯·紐金特的這一譯本(以下稱之為“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的第2卷共出現(xiàn)6次,分別在176、178、215、216、226、227頁。其中第176頁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原文為:
cannot some years prove more favorable than others to the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ildren,as there are some more favorable than others to the vegetation of trees and plants?(就像有些年份對于一些樹木和植物的植被的生長更為有利一樣,有些年份對兒童的physical education不是更為有利嗎?)
雖然未能從上述數(shù)據(jù)庫發(fā)現(xiàn)比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更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獻,但不能斷定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就是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獻,也不能斷定1748年就是physical education最早出現(xiàn)時間。這是因為,任何數(shù)據(jù)庫在理論上都不可能把歷史上存在過的文獻全部收錄在內(nèi),所以只能說physical education在英文文獻中的出現(xiàn)時間應不晚于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問世之年,也就是1748年。或許有一天,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比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更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獻。
1.2 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現(xiàn)時間
在檢索結果中,最早使用education physique的法語文獻是杜博斯的《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
e et sur la peinture》1733年法文原版第2卷[8](以下稱之為“杜博斯《詩畫論》1733年原版”),分別出現(xiàn)在這部著作的第238、240、292、293、307、309頁。這6例原文依次對應于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的6例physical education書證。例如,第238頁的原文與前文給出的第5版英譯本第176頁的原文相對應,語意完全一致:
certaines années ne peuvent-elles pas être plus favorables à l'éducation physique des enfans que d'autres années,ainsi qu'il est des années plus favorables que d'autres années à la végetation des arbres et des plantes?
通過檢索未能從上述數(shù)據(jù)庫和數(shù)字圖書館,檢索到比杜博斯《詩畫論》1733年原版第2卷更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法文文獻,但和不能確定1748年就是physical education的最早出現(xiàn)年代一樣,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杜博斯《詩畫論》1733年原版就是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文獻,也不能確定education physique最早出現(xiàn)在1733年,只能說education physique在法文文獻中出現(xiàn)時間應不晚于1733年。
2 對國內(nèi)已有研究涉及的4個問題的認識
2.1 盧梭的《愛彌兒》是否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根據(jù)對《愛彌兒》的法文原著電子版的檢索,《愛彌兒》的法文原著全書并未使用education physique,因此不可能是歷史上第一部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法文文獻。
筆者不清楚為什么國內(nèi)一些研究者認為《愛彌兒》首先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或許是因為盧梭在體育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受到中譯本的影響。的確,盧梭通過《愛彌兒》闡述的體育思想影響廣泛而且深遠,同時我國通行的《愛彌兒》中譯本(譯者為李平漚,以下稱為“李平漚譯本”)[9]的譯文有3處出現(xiàn)了“體育”,但其對應的法文原文都不是education physique。
李平漚譯本的第1處“體育”出現(xiàn)在第150頁,譯文是“所有那些研究過古人生活方式的人都認為,正因為他們有了體育鍛煉,所以才有那樣的體力和智力,使他們和現(xiàn)代的人有明顯的區(qū)別”,對應的法語原文是“tous ceux qui ont réfléchi sur la manière de vivre des anciens attribuent aux 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 cette vigueur de corps et d’?me qui les distingue le plus sensiblement des modernes”,⑧李平漚譯文使用的“體育鍛煉”對應的原文是“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并不是education physique。
值得一提的是,通過檢索找到的《愛彌爾》的3種英譯本——即barbara foxley譯本、阿蘭·布魯姆譯本以及grace g. roosevelt譯本。⑨都是用“gymnastic exercises”而不是“physical education”翻譯為“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例如,布魯姆的譯文是“all those who have reflected on the way of life of the ancients attribute to gymnastic exercises that vigor of body and soul which distinguishes them most palpably from the moderns”[10]。
李平漚譯本的第2處“體育”出現(xiàn)在第151頁,譯文是“為了使他有堅強的心,就需要使他有結實的肌肉;使他養(yǎng)成勞動的習慣,才能使他養(yǎng)成忍受痛苦的習慣;為了使他將來受得住關節(jié)脫落、腹痛和疾病的折磨,就必須使他歷盡體育鍛煉的種種艱苦”,對應的法語原文是盧梭從文藝復興時期法國著名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的著作中引用的,即“en parlant de l’éducation d’un enfant,pour lui raidir l’?me,il faut,dit-il,lui durcir les muscles;en l’accoutumant au travail,on l’accoutume à la douleur;il le faut rompre à l’?preté des exercices,pour le dresser à l’?preté de la dislocation,de la colique et de tous les maux”,譯文使用的“體育鍛煉”對應的原文是“exercices”。上述3種英譯本在該處都未用physical education對譯“exercices”,而是使用了“gymnastic exercises”或“exercises”。
李平漚譯本的第3處“體育”出現(xiàn)在第658頁,譯文是“活躍的生活、體力勞動和體育運動,對他來說是這樣不可缺少的東西,以至于如果不許可他做這些活動的話,他是一定會感到很難過的”,對應的法語原文是“l(fā)a vie active,le travail des bras,l’exercice,le mouvement,lui sont tellement devenus nécessaires,qu’il n’y pourrait renoncer sans souffrir”,譯文使用的“體育”對應的原文是“exercice”。
上述3種英譯本都未用physical education對譯“exercice”,而是使用了“exercise”。
2.2 巴勒克澤爾的《論兒童的身體教育》是否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巴勒克澤爾[11]是18世紀著名醫(yī)生,對兒科的發(fā)展做出了歷史貢獻。他的《論兒童的身體教育》是一部關于兒童和青少年體質(zhì)健康的著作,1762年在巴黎出版,原書名是《dissertation sur l'éducation physique des enfans,depuis leur naissance jusqu'à l'?ge de puberté》,直譯為《論孩童自出生到青春期的身體教育》。
與盧梭的《愛彌爾》不同,《論兒童的身體教育》法
文原著的確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根據(jù)檢索結果,除了題目之外,《論兒童的身體教育》法文原著還有4處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分別在第3、132和169頁以及附在全書正文之前的作者給其老師antoine petit寫的獻詞的第一句話中(該獻詞分為6頁印刷,但都沒有頁碼)。但由于杜博斯《詩畫論》1733年原版的第2卷已經(jīng)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而《論兒童的身體教育》的出版時間是1762年,因此并不是歷史上首部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文獻。
2.3 麥克拉仁的著作是否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麥克拉仁是19世紀英國著名體育家,在體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學校體育、軍事體育和體育理論方面都做出了歷史貢獻,physical education是其著作的常用詞和關鍵詞,但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第2卷已經(jīng)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而且,在18世紀后半期和19世紀早期,physical education已經(jīng)是流行的常用詞了,麥克拉仁是19世紀的人物,他的著作是不可能首先采用physical education的。
2.4 斯賓塞的著作是否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前文已經(jīng)介紹,我國有研究者提出斯賓塞的著作首先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但未說明具體時間和出處。根據(jù)有關研究的上下文推斷,研究者應該是認為斯賓塞的教育學名著《論教育》(on education)收入的文章《體育》(physical education)首先采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斯賓塞的《論教育》是一部文集(最早于1860年在美國出版,1861年在英國出版),共收有斯賓塞1850年代為英國的3家雜志寫的4篇與教育問題有關的評論性文章(即《什么知識最有價值》、《智育》、《德育》、《體育》)。《體育》最初發(fā)表在《不列顛季刊》(the british quarterly review)1859年4月號,是斯賓塞對《論幼兒的生理和道德管理》(a treatise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moral management of infancy,作者是andrew combe,1847年出版于愛丁堡)等6部著作的評論,原題名是physical training (并不是physical education)。
但是,和麥克拉仁一樣,斯賓塞也是19世紀的人物,《論教育》出版的年代比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第2卷的出版時間晚了一個多世紀,斯賓塞的著作同樣是不可能首先采用physical education的。
根據(jù)以上檢索結果和分析,可就英文physical education和法文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現(xiàn)時間做出如下結論:
第一,physical education在英文文獻中的出現(xiàn)時間應不晚于杜博斯《詩畫論》第5版英譯本問世之年,也就是不晚于1748年。
第二,education physique在法文文獻中的出現(xiàn)時間應不晚于杜博斯《詩畫論》1733版原版問世之年,也就是不晚于1733年。
第三,盧梭的《愛彌爾》和巴勒克澤爾的《論兒童的身體教育》都不是最早使用education physique的著作。
第四,麥克拉仁和斯賓塞的著作都不是最早使用physical education的著作。
王怡霖、jacqueline foelster、肖光志為本文使用的法文資料的搜集和翻譯提供了大力幫助,特致謝忱!
(《體育學刊》第2屆網(wǎng)絡發(fā)展論壇專題報告論文)
注釋:
① http://eebo.chadwyck.com/home。
② http://mlr.com/digitalcollections/products/ecco/。
③ http://gdc.gale.com/products/the-times-digital-archive-
1785-1985/。
④ http://amedu.com/collections/eighteenth-century-
journals-portal.aspx。
⑤ http://books.google.com/。
⑥ http://artfl-project.uchicago.edu/。
⑦ http://gallica.bnf.fr/。
⑧ 本文引用的《愛彌爾》法文版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learning technologies)網(wǎng)站制作的網(wǎng)絡版,訪問網(wǎng)址為http://ilt.columbia.edu/pedagogies/rousseau/contents2.html,訪問時間為2012年4月19日。
⑨ barbara foxley(1860-1958)是英國學者,以將《愛彌爾》譯為英文而著稱于世——該英譯本長期享譽英語世界。本文引用的barbara foxley的《愛彌爾》英譯本是古登堡計劃(project gutenberg)官網(wǎng)(http://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的電子版本,網(wǎng)絡地址為http://gutenberg.org/cache/epub/
5427/pg5427.txtx,訪問時間是2012年4月20日。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1930-1992)是20世紀美國著名學者,著有《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莎士比亞的政治》(shakespeare’s politics)等名著,譯著包括《愛彌爾》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等。grace g. roosevelt(1941-)是美國當代學者,本文引用的roosevelt的《愛彌爾》英譯本是網(wǎng)絡版,網(wǎng)址是http://ilt.columbia.edu/pedagogies/rousseau/index.html,
訪問時間是2012年4月20日。
參考文獻:
[1] 徐元民. 體育學導論[m]. 臺北:品度股份有限公司,2003:82.
[2] 韓丹. 談體育概念的源流及其對我們的體育認識和改革的啟示[j]. 體育與科學,2010,31(4):1-8.
[3] 吳正先,李躍生. 應取消“體育教育”一詞[j]. 教育科學研究,1992(4):8-9.
[4] 周西寬. “體育”概念古今談[j]. 四川體育科學學報,1982(3):9-17.
[5] 韓丹.
“體育”就是“身體教育”——談“身體教育”術語和概念[j]. 體育與科學,2005,26(5):8-12.
[6] 楊文軒,陳琦. 體育原理導論[m]. 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6:36.
[7] dubos,abbé (jean-baptist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and painting[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homas nugent. from the fifth edition revised,corrected,and enlarged by the author. volume 2. london:1748.
[8] dubos,abbé (jean-baptiste).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m]. seconde partie. paris,p-j mariette,1733.
[9] 盧梭. 愛彌兒,論教育[m]. 李平漚,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