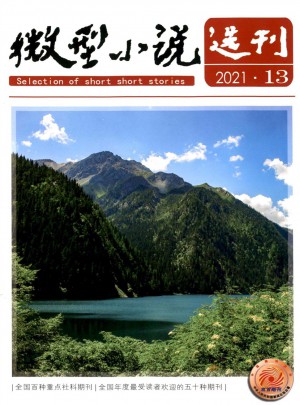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小說語言特征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文章編號】0450-9889(2012)01C-0090-02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一位作品語言風格獨樹一幟、具有獨特個性的作家。在他的許多小說作品中,構筑了一個充盈著濃郁湘西風情的世界,讓讀者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沈從文對家鄉的那份摯愛與真誠,并得到了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感悟。他在小說中以樸實、準確、生動的語言,描繪了湘西豐富多彩的風土人情,張揚了在民族地區生活的人們的魅力,讓讀者領略了湘特的風采,也體現了他的藝術思想。
回顧沈從文的創作歷程,他著有短篇小說二百多篇,中長篇小說十多部,其中以湘西題材的作品最富有吸引力,他的小說的語言特色也主要體現在這一類作品中。這些作品浸透著作者濃厚的湘西情結,以湘特的方言土語和諺語歌謠,再加上湘西特有的景致和風土人情,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安寧淳樸的湘西世界,而這些要素則共同構造了沈從文小說濃郁的地域特色。
一、沈從文小說中的地域內涵
地域,是一個區域性概念,也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沈從文成長的中國鄉村社會,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以戶為單位的處于自然經濟狀態的農村社會。由于長時期處于聯系緊密的生存環境下,許多地方逐漸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物質和文化形態,維持著濃烈的地方文化色彩,這也就形成了地域。沈從文小說的語言正是帶著地域文化的鮮明烙印。
沈從文的故鄉鳳凰縣處于湘西的崇山峻嶺間,北面流淌著一條清澈見底的沱江。河流的兩岸一邊是蒼翠高山,另一邊是蜿蜒的河街,沿河有久負盛名的吊腳樓,城中的街道大多是由青紅二色石板鋪成。沈從文生長的小城環境充滿著詩情畫意,令人神往,湘西世界的恬靜、純樸,以及如詩如畫的自然風光、醇厚的民風民俗在沈從文的心靈中早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也孕育了沈從文小說中對湘西美的淋漓盡致的描述,為他用富有湘西地方特色的純樸、簡潔、清新的語言去展現故鄉的美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而這種語言必然帶有濃厚的湘西地方特色,這也成為了沈從文小說語言的最大特色。
二、鄉味濃郁的湘西語言
沈從文小說中反映湘西特色的語言文字俯拾皆是,既有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俗語、諺語,也有湘西鄉味十足的景致和風俗人情,等等。從文學語言的顯著性來看,作者要使作品體現出地方特色,應該刻意有選擇地采用一些能引起讀者意會和共鳴的方言土語,并時時在作品中穿插體現。富有湘西地方特色是沈從文小說最顯著的特征,這些作品帶有湘西人民特有的純樸的語言氣質,刻畫出帶有民族風情、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例如,湘西人有一些特有的稱呼方式,如把青年男子稱為“小牯牛”,稱文化人為“風雅人”,把“生氣”說成“發氣”,等等。沈從文在小說中大量使用了這些充滿湘西韻味的地方土語,而這些語言文字在沈從文的小說中一脈相承,讓讀者在深讀作品的過程中對其小說自成體系的語言印象深刻,小說語言的地域特征彰顯無遺。
(一)人物語言
本文的人物語言獨指小說中人物的對話、獨白等。人物語言寫得生動與否,關系著人物形象刻畫的成敗,而人物正是小說作品的靈魂。沈從文小說中人物的語言,來源于他自小生長在故鄉的經歷,植根于湘西的生活土壤之中,濃郁的地方色彩躍然紙上。小說人物的語言,大多都是純樸明快、鮮活傳神,融合了湘西的方言土語,還穿插有俏皮、能令人回味無窮的民歌民謠。例如,《長河》里老水手和天天關于捉鵪鶉的對話,《貴生》中毛伏與貴生的齟齬口角,《蕭蕭》中鄉下人談論城里女學生的段子,《柏子》里水手與相好的相互埋怨、互相嗔怪,《邊城》里儺送向女孩示愛所唱的山歌,等等。在這些人物對白里,處處是湘西人質樸、活潑、隨便、大膽甚至有些粗野的鄉音,能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體會到湘西人生活的原生態、原質感,并漸生真實、親切之感。這些具有地方方言特色的語言,經過作者提煉并完美融入人物的對話或對唱后,回蕩著湘西特有的鄉味,加深了小說的地域特征和內涵。
除了在人物對白上體現地域特征,沈從文還把湘西的語言特色進一步深化,讓同在一部作品中一個地方的人的語言各具特色,做到了語言的個性化。而個性化則是塑造人物靈魂的核心,尤其是在以人物對話推動情節的小說中,人物說什么話、說話的語氣、用詞的輕重緩急等,都體現了該人物的身份、地位、經歷、教養,以及其思想觀點和性格特征,沈從文在小說中用人物的本色語言來符合他們各自的身份,切合他們各自不同的生活環境,散發出濃郁的生活氣息。例如,《丈夫》中寫老七的男人對水保談起在偶然中找到失去很久的鐮刀的事:“是的,得到了它那是好的。因為我總以為這東西是老七掉到溪里,不好意思說明。我知道她不騙我了,我明白了。我知道她受了冤屈,因為我說過:‘找不到么?那我就要打人!’我并不曾動過手,可是生氣勢也真嚇人。她哭了半夜!”這段老七的男人說的話,無處不流露出既高興又愧疚的心情,也表露和坦白了自責的情緒,用語和語氣都短促和直白,這也恰恰符合“沒有文化的厚道的鄉下男人”說話的特征。
(二)湘西的歌謠和俗語的運用
沈從文在小說中運用了許多湘西的歌謠、諺語和俗語,而這些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湘西口語性和音樂性的語言的適當插入,給予了小說別樣的情調,使讀者仿佛置身于湘西那充滿民族風情的地域。例如,《邊城》中翠翠聽唱的那首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愿迎神的歌:
“你大仙,你大神,睜眼看看我們這里的人,他們既誠實,又年輕,又身無疾病,他們大人會喝酒,會做事,會睡覺……他們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雞鴨肯孵卵,他們女人會養兒子,會唱歌,會找她心中喜歡的情人。”這些令人會心一笑的語言,直白而簡樸,就算不是太了解湘西風情的讀者也會很容易領會其中的意思,從而與小說中的人物取得共鳴。
除了民歌之外,沈從文在小說還常常用俗語和諺語來表現人物之間的瓜葛,而這些生動的語言則豐富了小說的情感,在大大增加了作品生活氣息的同時,還對營造鄉土氛圍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例如,在《邊城》中當寫到天保和儺送兩人同時愛上翠翠時,沈從文用這樣的俗語來闡述這三位年輕人的情感真實流露:“火是各處可燒的,水是各處可流的,日月是各處可照的,愛情是各處可到的。”另外,沈從文還很善于用俏皮和詼諧的語言表達小說中的情境,例如,《長河》中詼諧的節日對歌:“你歌沒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頭牛毛多,唱了三年六個月,剛剛唱完一只牛耳朵。”又如“什么畫,墻上掛”、“槽里無事豬拱
豬”、“拾了雞蛋被人打”,這樣的順口溜和俚語不僅充滿了地方的風味,而且非常口語化,讀者理解起來也很容易。類似以上這種新奇的比喻和適度的夸張,在跌宕起伏的情節中透出一種民間的機智和詼諧,讓人莞爾一笑。
三、對湘西特有景致和風俗的描繪
沈從文曾經評價自己的作品,在語言的描述內容上有兩大偏愛,一方面是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另一方面是怡人心緒的自然景物,“景物撐起了作品的半邊天”。這些景致不僅是小說中人物活動的背景,還是湘西地域風情的最好體現,沈從文也在潛意識下不斷表達著對家鄉的摯愛和想念。
篇2
作者簡介:萬建香(1973-),女,江西南昌人,博士,江西財經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環境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1-0115-05收稿日期:2011-07-24
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文獻關注政府環境規制對企業競爭力的微觀影響,并形成了傳統觀點、波特假說、不確定性假說三種觀點。傳統觀點認為,環境規制的執行以提高生產成本或對盈利性、生產性投資的擠出為前提,從而必然降低產業績效。Brock 等(2005)就認為嚴格的環境規制使企業承受額外的規制成本,阻礙了產業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傳統假說受到波特假說的嚴峻挑戰。波特假說認為,環境規制給產業造成的負擔可以通過技術創新途徑加以彌補從而提高產業績效(Porter et al,1995)。龐瑞芝等(2011)運用中國1998年~2008 年省際面板數據評估了轉型期間我國新型工業化的增長績效,最終支持了波特假說。王國印等(2011a)關于我國中東部面板數據的實證表明,波特假說在較落后的中部地區得不到支持,而在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則可以。何潔(2010)利用中國29個省份1993年~2001年工業SO2的排放數據來估計模型,對波特假說再次進行了驗證。趙紅(2008)運用1996年~2004年中國產業數據,再次驗證了波特假說。不確定性假說認為,環境規制對產業績效的影響可正可負,具有不確定性。環境規制強度、政策工具特點、產業和市場結構都影響環境規制的產業績效,各自表現為成本負效應或創新正效應,兩者的強弱決定環境規制的最終績效。王國印等(2011b)運用我國東中部地區面板的實證表明, 較發達的東部地區的情況支持波特假說,而較落后的中部地區則不支持。陳艷瑩等(2009)研究發現只有當環境管制引致技術創新節省的成本大于污染控制增加的成本時,波特假說才成立。單雪芹等(2009)從構筑國家競爭優勢時加強環境保護的必要性出發,分析了波特假說的不確定性問題。
上述研究大多假定一旦形成引致創新,就能提升產業競爭、獲利能力,而實際上兩者之間存在一定差距,至少存在時間滯后,其合理性、實用性有待驗證(趙紅,2007);其二,三種假說以波特假說最受推崇,同時也飽受爭議。因此,本文專門針對波特假說存在性問題,運用江西省24個重點調查企業①2002年~2009年的面板數據,設定產業競爭能力、創新能力、環保能力為被解釋變量,重新驗證波特假說的存在性,驗證其是否適合江西省的經濟實際。
文章第二部分為變量選擇和數據描述;第三部分為模型估計、經濟意義解釋及績效彈性分析;第四部分為結論。
篇3
一、小說語言的音樂美
趙樹理十分重視作品中語言的音樂美。他寫的東西是面向大眾的,為了便于讀者的接受,他特別注意聲律的和諧、節奏的勻稱。人們閱讀起來瑯瑯上口,聽起來都有明顯的節奏感,比如:《小二黑結婚中》中:“劉家峻有兩個神仙,鄰近各村無人不曉,一個是前莊上的二諸葛,一個是后莊上的三仙姑。”抑揚頓挫,聲調優美,易于上口,為整個段落增色不少。
趙樹理有時也用詞組的反復來體現小說語言的音樂美,如:不多一會兒,屋里、院里,你的嘴對我的耳朵,我的嘴又對他的耳朵,各里各得都嚷嚷這三個字――”“小飛娥”、“小飛娥”、“小飛娥”。[3](《登記》)這是張木匠結婚時,村里年輕人鬧新房的一個描寫,其中,“小飛蛾”三個字的多次應用活現出青年小伙子鬧新房的熱烈而歡樂的氣氛。
二、小說語言的樸素美
質樸無華,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鄉土風味,這一特點是趙樹理的小說語言最明顯的特色,具體體現在口語化、群眾化、濃厚的山西地方口音。他的創作是面向大眾的,他的文學語言,無論怎么去看,都看不出華麗、炫耀、做作、賣弄,而是用語實在,句句發自內心。如:《李有才板話》中對閻家山一段的描寫:“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窖……”[6]這段文字,沒有華麗的詞語,沒有起伏跌蕩、扣人心弦的情節,看上去平淡無奇如話家常,然而以簡潔的描寫,卻把當時的農村生活展現在讀者面前。
趙樹理小說語言的質樸自然,還表現在詞語和句式的選用方面。如:“有個農村叫張家莊,張家莊有個張木匠,張木匠有個好老婆,外號叫‘小飛娥’,‘小飛娥’生個女兒叫艾艾,算到一九五年陰歷正月十五元宵節,虛歲二十周歲十九。”(《登記》)這段文字同樣是短句,卻是一句敘一事,一句連一句,如流水一樣順暢,而且這種說法完全是用農民的口氣和習慣來寫的,從而體現出質樸自然的樸素美。
三、小說語言的修辭美
趙樹理小說中運用的修辭很多。本文重點從比喻的運用來說明語言的修辭美。首先是喻體都是群眾生活中的所熟悉的東西,如:“驢糞”“破蒲扇”一類比喻都很形象。其次是比喻新穎具有獨創性。他的比喻與眾不同,他主張比喻應該有自己的個性,更加體現小說語言的修辭美。
除了比喻,趙樹理還善于用借代,他把借代妙用在人物外號上。趙樹理作品中的綽號有兩個特點:一是量多,二是樣多。他善于捕捉人物外表或內在的某些特征,用準確的外號表現出人物的個性,如“尖嘴猴”,“塌眼窩”,“鴨脖子”,“小飛蛾”,“能不夠”,“糊涂涂”,“三仙姑”,“二諸葛”,等等,均能引起讀者聯想,增強人物的形象感。也有的外號從字面上看,看不出多大的形象性,但往往包含著生動有趣的來歷,知道它的來歷,再看這個外號,常常會使讀者發出會心的微笑。
四、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美
趙樹理善于通過人物的言行塑造人物,再加上他有一定的生活基礎和對描寫對象的透徹了解,所以他筆下的人物語言是很個性化的,讀他的文章時可以從人物的語言看出其出身、身份地位、性格特征。
人物性格是由社會地位、生活經歷和心理素質等因素決定的。不同性格的人即使地位身份相同,遇到的情況相同,語言也會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趙樹理還常常賦予一些人特有的習慣語,給某些人物涂上一種獨特的個人色彩,從而突出了眾多人物中的“這一個”。如:《李有才板話》里寫地主腿子張得貴迎接老楊同志說的一段話:“他一見老楊同志,就滿面賠笑說:‘這位就是縣農會主席嗎?慢待慢待!我叫張得貴,就是這村的農會主席,上午我就聽說你老人家來了去公所,拜望了好幾次也沒有遇面……’”這樣的客套話非常符合張得貴多年給地主跑腿兒的經歷,非常符合他這一類人的說話習慣。還有寫二諸葛時是“命相不對”,“恩典恩典”;三仙姑的“前世姻緣”;王聚海的“鍛煉鍛煉”,等等,體現出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美。
趙樹理小說的語言藝術音韻協調、順口悅耳、活潑明快。他十分重視作品中語言的音樂美,語言質樸無華,簡潔明了,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鄉土風味。他在語言上力求通俗易懂,文筆力求簡練,這一特點是趙樹理的小說語言最明顯的特色。從趙樹理文學語言的修辭運用中我們可以一睹他在文章中的比喻和借代的絕妙應用。他文章中的個性化的人物語言又一次讓我們確認了趙樹理的語言藝術有如此高的成就。
參考文獻:
篇4
例如,教師在小說教學過程中,通過多媒體課件,向學生展示與小說主題和內容相關的音樂作品、圖片及短片,調動學生的視覺感官,使學生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從而更好的理解小說的內容,激發學生閱讀興趣。同時,教師可以讓學生在課前共同制作出教學課件,結合小說內容,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使學生感受到被尊重,從而調動學生的學習動力。此外,教師可以根據所學文學作品內容,創設相應的教學情境,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角色進行扮演,在課堂上表演小說情節,從而調動學生對小說學習的熱情。
二、欣賞小說的語言美
文學欣賞中少不了對語言的欣賞,對語言文字的理解和運用也時時閃爍著文學欣賞的影子。新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學生“欣賞優美、精彩的語言”,并具體化為“積累、感悟和熏陶”,其實質是對學生的語言鑒賞方面提出的要求。語言是文學的重要內容,不僅具有生動優美的特點,還能表達出深厚的情感。因此在初中語文小說教學中,教師需要培養學生對小說語言的欣賞能力。不同的小說有著不同的語言風格,有質樸的、有幽默的、有華麗的、有蘊含人生哲理的,不同的語言風格具有不同的美感。在引導學生欣賞小說語言的過程中,教師不僅要關注小說語言表面的含義,更要發現小說語言的深層內涵,了解小說語言的精髓所在。主要體現在:第一,對小說中描繪人物行為、思想及言語的詞語進行把握,體會人物的性格特點;第二,了解小說的寫作特點,通過對小說語言中比喻、象征等手法的學習,掌握寫作手法,從而更好的把握小說的語言魅力;第三,培養學生對小說整體內容的認知,充分體會小說各個主題內容的聯系,體會小說語言的美感。
例如在蘇教版初中語文《社戲》一文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帶領學生走進小說的時代,首先幫助學生形成對小說語言的整體把握,從小說的字里行間體會作者的情感。文中的“我”與少年伙伴夏夜行船、船頭看戲、月下歸航:“兩岸的豆麥和河里的水草所散發出來的清香”,“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連山,仿佛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架起兩支櫓有說笑的,有嚷的,夾著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勾畫出一幅生動的行船圖。通過對小說環境的刻畫,描繪出少年活潑的性格,使讀者情不自禁的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通過引導學生鑒賞課文語言,讓學生在理解語言、運用語言中感悟其遣詞造句之美,感悟其謀篇布局之美。
三、體會小說的故事情節
篇5
一、自然樸實的語言風格
自然樸實是丁玲早期小說語言風格的一個突出特征。丁玲一生執著于追求
文學語言的質樸無華,追求“樸素的,合乎情理的,充滿了生氣的,用最普通的字寫出普通人的不平凡的現實的語言”[1],形成了樸實自然、不尚雕飾的語言風格。這個特點不僅表現在小說用語富于口語化、平實易懂,也表現在小說的句式簡短小巧,靈活多變,富于生活氣息,表現在修辭上多用排比、對比、比喻、比擬、夸張等語言材料普通,與現實生活貼近,為人們所普遍熟悉的辭格。這種語言特點充分顯露于丁玲早期小說的字字句句之間,給人以親切平實的深刻印象,讀之覺得好像是在和作者說話聊天、促膝談心一樣。如:
本來,酉陽是不必有那樣多學校的……只要有花,至少可以抓下一把來,底下看的人便搶著去撿花片。勻兒總該記得吧!” [2]
這段文字描寫了酉陽中學氣派堂皇、優美宜人的校園景致。文中多用口語詞、
語氣詞、疊音詞,少用成套的關聯詞;多用短句、省略句,少用成串疊加的附加
語;多用所用辭格都是人們習見習用的比喻、對比等辭格。這些表達手段的恰切
使用,讓我們覺得好像在跟著勻珍媽媽漫步于酉陽中學校園一般,感到十分親切
自然。這種自然天足的文學語言,能夠“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如眼見其人,長時
間回聲縈繞于心間。”[3] 體現了丁玲早期小說語言的魅力。
二、細致透徹的語言風格
細致透徹是丁玲早期小說語言風格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丁玲早期小說著稱文壇的鮮明標志。作者善于抓住一個中心、一個焦點,濃墨重彩地加以點染,把應該突出的部分寫得極為充分、詳盡;且喜用關聯詞語、數量詞語和成串使用同類詞語,使表意周全詳盡;同時多用長句、松句,使句子架屋疊床,盤桓繁復,信息量大,表達充分完整;排比、反復等辭格的綜合使用,使小說語言流暢繁復。這些風格手段的恰當使用,起到了積極的修辭效果。如:
現在她把女人看得一點也不神奇……依舊忍耐著去走這一條在純物質的,趨圖小利的時代所不屑理的文學的路的女人。[4]
引文運用長句造成了語言細致透徹的特點。作者在“阿毛真不知道……”這個長達170字的長句中嵌入了結構繁復、多達109字的附加成分,即“自己燒飯……在許多高壓下還想讀一點書”、“把自己在孤獨中見到的……趨圖小利的時代所不屑理的文學的路”,使句子枝繁葉茂,把城里那些以寫作為生的女人的生活和心理寫得紛紛揚揚,淋漓盡致,顯得語言腴厚,內容豐富,表意細致完整,給人以詳盡透徹之感。作者在刻畫人物心理時更是多方鋪敘、分析、闡釋,唯恐表意不盡,力求寫出人物復雜多變、深邃莫測、錯綜盤曲的內心世界,尤為體現了繁豐細致的語言風格。
三、明快率性的語言風格
明快率性是丁玲早期小說語言風格的一個鮮明特征。小說詞語意義明晰,多用直義;多用關聯詞語、方位詞語、序數詞語等,清晰連貫,層次分明;多用短句、反問句和斷然的肯定或否定句等,語意顯豁,情感鮮明;多用比喻、排比、借代、頂真、比擬、反復、對照等辭格,明白好懂。如:
我總愿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我真愿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5]
文字直寫莎菲不被人們理解的社會現實,直抒她因不得理解而倍感寂寞、孤獨、苦悶、失望、不滿的心境。詞語都是直義,讀時不需揣摩、推測、意會,一看就明;關聯詞語的運用使表達流暢,層次分明;副詞“總”、“真”、“偏偏”起到了強調的作用,使感情鮮明凸顯。以短句為主,結構簡單,表意單一、明確、清晰,沒有歧義,沒有疊加的修飾語;而“我總愿意……”、“我真愿意……”、“我真不知……”、“我要……做什么?”、“愛我的……肺病嗎?”等肯定句、否定句和反問句的較多使用,使表述更加直露明快。主要使用了反復辭格,詞語反復,語意凸顯,感情強烈,鮮明地表達了莎菲渴望被人理解的愿望。這些風格手段的綜合使用,充分顯示出小說顯豁明朗、率性明快的語言風格,這與丁玲豪爽、豁達、坦誠、大氣的性格是分不開的。
四、親切溫柔的語言風格
親切溫柔是丁玲早期小說的一個突出特征。小說擅長使用能夠觸動心靈深處、表現細枝末節、細膩深沉、柔和溫馨的詞語,以及疊音詞、語氣詞、代詞、模糊詞語、昵稱、尊稱等;注重長短句交錯,整散句結合,多用插入語,且句子的主語、修飾語、賓語又長又多,結構自由散漫,節奏松軟;修辭上常用擬人、比喻、摹擬、婉曲等辭格,顯得親切委婉。如:
更使阿毛不愿常見的……并且每天她和他都并坐在一張大藤椅里,同翻一本書,或和著高低音共唱一首詩歌。
這段文字一是選用了大量表示親近甜蜜的詞語,如“斜靠”、“漫步”、“擁著”、“踏著”、“并坐”、“同翻”、“和著”、“共唱”等;二是使用了多組音節自然和諧、悅耳動聽、表意細膩的疊音詞,如“鏗鏗鏘鏘”、“細細柔柔”、“談談講講”、“悠悠閑閑”等;三是在句中使用了語氣助詞“的”,用逗號分開,輕聲,舒緩了節奏;四是使用代詞“那樣”,增加了音節,大大舒緩了語言的節奏,與后面的兩組疊音詞“細細柔柔”、“談談講講”相結合,似實似虛,柔婉溫馨;再加上結構松散、自由散漫的句子,讓人感覺如春風拂面,如潺潺流水,輕柔婉轉,秀麗嫵媚,纏綿繾綣,表現了阿毛對美好生活的熱切憧憬和向往之情。正是因為小說“終是比別人要來得溫柔細膩,所以歡喜看這類文章的讀者還不十分零落。”溫柔親切的語言風格為丁玲及其小說贏得了讀者,贏得了廣大年輕讀者的喜愛。
丁玲早期小說的語言風格特征,是她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中辛勤耕耘、努力探索的心血和結晶,其內容十分豐富,而且對我國的現代文學語言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里論述的四個方面,雖然還不夠全面科學,但基本上能夠反映出丁玲早期創作語言藝術風格的概貌輪廓。關于這些小說語言藝術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在今后的學習和研究中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丁玲.美的語言從哪里來[A].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8卷[C].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40
[2]丁玲.夢珂[A].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3卷[C].(第1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5
篇6
一、小說與視角
根據Mick Short(1996)的觀點,我們至少需要三個話語層面來解釋小說(即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語言,因為在角色―角色層面和作者―讀者層面之間插入了一個敘述者―被敘述者的層面:
信息發出者1―信息―信息接受者1
(小說家) | (讀者)
信息發出者2―信息―信息接受者2
(敘述者) | (被敘述者)
信息發出者3―信息―信息接受者3
(角色A) | (角色B)
上圖只能說明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因為在解釋小說組織形式時這三個層面和三組參與者都是不可少的。但與其他體裁(即詩歌和戲劇)相比,小說的基本話語結構中有六個參與者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在其敘述中有更多的視角,小說家須經過慎重考慮這些視角彼此之間相互聯系。
I―敘述者:講述故事的人在事件發生后作為講述者,所以也可能成為小說世界的一個人物。此時,評論家們稱敘述者為“第一人稱敘述者”或“I―敘述者”,因為敘述者在故事里提到自己的時候,總是用第一人稱代詞“我(I)”。但在此類小說中存在“一定局限性”,因為I―敘述者不能了解所有的事實;有時也不可靠,特別在兇殺和推理小說中他們會保留信息或說謊來欺騙讀者。
第三人稱敘述者:這種類型是有爭議但占主導地位的敘述者類型。敘述者在涉及到故事虛擬世界中所有人物時,都會用第三人稱代詞“他,她,它或它們”(he,she,it or they)。
圖式語言:敘述視角也受圖式的影響。在相同情形下,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圖式,并與他們不同的敘述視角相聯系。因此,店主和顧客將有商店圖式。這些圖示在許多方面都會成為相互的鏡像,并且店主成功與否將部分地取決于他們能否考慮到顧客的圖示和視角。
除了通過選擇描述什么來表明視角以外,小說家也能通過描述的方式來表達,尤其是通過表示評價的詞句。例如:“She opened the door of her grimy,branch-line carriage,and began to get down her bags.The porter was nowhere,of course,but there was Harry...There,on the sordid little station under the furnaces...”在這段選自D.H.Lawrence的作品Fanny and Annie,評價“沉重”的形容詞“grimy”、“sordid”、“branch-line carriage”和“sordid little station under the furnaces”突出了此時明顯不滿的Fanny眼中Morley火車站。
舊信息和新信息:在故事開頭,我們能夠做出預言:對所有事物的敘述所指(narrative reference)(除了我們的文化中通常每個人都知道的事物,如:太陽)一定是新的,因此應使用不定所指(indefinite reference)。這正是Thomas Hardy的作品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的開頭的情況:例如:One evening of the summer,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reached one third of its span,a young man and woman,the latter carrying a child,were approaching the large village of Weydon-Priors,in Upper Wessex,on foot.第一次提到的man(和相關的woman)和child的所指不確定(a young man and woman,a child),因為我們以前沒見過他們。19世紀是確定所指,因為Hardy認為他的讀者已經知道這個詞組的所指。但是請注意:即使是如此直接的描述,Wegdon-Priors village 剛一提及就是確定所指,這鼓勵我們裝作自己已經很熟悉它。Hardy因此把他的讀者定位為某種程度上熟悉這個村莊(以及這個地區)而不是熟悉人物。
指稱:因為指稱是與說話者相關的,所以它很容易用于表明特定的變化中的視角。在下列選自The Secret Agent的例句中,我們從Mr.Verloc的視角中看出他妻子的行動。
例如:Mr.Verloc heard the creaky plank in the floor and was content.He waited.
Mrs Verloc was coming.
除了表示感知和認知的動詞heard,waited和他的內心狀況(was content),我們能從Mr.Verloc的角度(coming)看出Mrs.Verloc對他丈夫的行動。在小說中,僅僅從Mr.Verloc的視角來看待事件,具有戰略重要性。他沒有意識到妻子正準備殺害他。
二、言語和思維的表達
1.言語的表達
根據Short的觀點(1996),言語表達的連續可以有以下幾種可能:
1)直接言語(DS)
2)間接言語(IS)
3)敘述者對言語行為的表達(NRSA)
4)敘述者對言語的表達(NRS)
從1)到4)的過程中能夠產生一個更深層次的范疇即自由間接言語(FISA),它是直接言語(DS)和間接言語(IS)特征的結合體,它在言語表達的漸變群中位于DS和IS之間:
NRS NRSA IS FIS DS
以下Charles Dickens的作品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的例子可以用來闡明言語表達的大多數類型。例如:
①He thanked her many times,and said that the old dame who usually did such offices for him had gone to nurse the little scholar whom he had told her of.②The child asked how he was,and hoped he was better.③“No,”rejoined the school-master,shaking his head sorrowfully,“ No better.”④“They even say he is worse.”引號中校長(school-master)的話可以作為DS的例子。典型的IS可以在②句中看到:“The child asked how he was.”它提供給我們關于孩子所說的話的建議性內容,而不是她在說這些內容時所用的言詞。但是在句子“He thanked her many times...”中,在①句的開頭,我們甚至不知道校長的話是什么,更不用說校長致謝時使用的話語。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他重復使用了感謝(thanking)的言語行為。結果,段落的這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很長一段話語的概要,并因此比用IS有更多的背景。Mick Short 稱這種極小類型的表達為NRSA。另外一種比NRSA更小的言語表達的可能,是僅僅告訴我們言語發生了句子,甚至沒有指出有關的言語行為,例如:We talked for hours.這種句子稱為NRS。
FIS通常以一種形式出現,這種形式第一眼看起來好像是IS,但又有DS的特征。在這個段落里,FIS最清晰的例子就是②句的后半句:“...and hoped he was better.”(前半句“The child asked how he was...”明顯是IS,它給出了語句的建議性內容,而不是所用的詞語)雖然它肯定不是DS,但他確實有那個孩子所使用的言辭味道。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是:雖然在句子的前半部分,它與IS時并列的(這致使我們認為它將有相同的情形),但省略了插入的從句,而這個從句很容易就能從內容中推導出來。更清楚的句子是“...and said that she hoped he was better.”。
2.思維的表達
小說家們用來表達他們的人物思維的類別,與用來表達言語的類別是完全相同的。例如:
a.He spent the day thinking.他整天都在思考。(敘述者對思維的表達:NRT)
b.She considered his unpunctuality.她認為他不準時。(敘述者對思維行為的表達:NRTA)
c.She thought that he would be late.她認為他將會遲到。(間接思維:IT)
d.He was bound to be late.他一定會遲到的。(自由間接思維:FIT)
e.“He will be late,”she thought.“他會遲到的,”她想。(直接思維:DT)
由于與NRT,NARTA或IT相關的效果與言語表達大致相同,所以我們只討論兩種思維表達類型,即DT和FIT。
三、小說風格
作者的風格:當人們談到風格時,通常是指作者的風格。即使作品的主題、目的等不同但可識別的寫作風格屬于特定的作家,這種寫作風格使一個作者的作品與其他作家相區別,并且可以通過同一作家的一系列作品識別出來。如Jane Austen和Ernest Hemingway。
文本的風格:作者可以有自己的風格,文本也有自己的風格。評論家們能談論George Eliot的風格,也能談論作品Middle march或其某一部分的風格。在觀察文本風格時,我們更關心的是意義,而不是作者風格的世界觀形式。因此,當我們觀察文本風格的時候,需要觀察其語言的選擇,例如:
――詞匯模式(詞匯量);
――語法組織模式;
――文本組織模式(從句子到段落以及更上層),文本結構的單位如何安排的);
――前景化特征,包括修辭格;
――是否能觀察到任何風格模式的變化;
―― 各種類型的話語模式,如,依次發言和推論模式;
――視角處理的模式,包括言語和思維的表達。
四、結語
本文從小說的視角、言語和思維的表達、小說的風格三個層面剖析了小說的語言,最后就如何分析小說語言作了簡略探討。另外,我們還有許多途徑來分析小說語言,例如:
――在詞匯層面上有前景化表現時,可以運用形態分析來分析詞語的新組合。
――在詞序和句法層面上有前景化表現時,可以運用我們的詞類知識(即名詞、動詞、形容詞等)來分析不尋常的或“有標記的”組合。
――在語法層面上,可以分析句子結構或尋找不同類型詞組的組合和模式,名詞詞組和動詞詞組或許是小說語言很常用的。
總之,小說的魅力在于其豐富燦爛的語言,小說語言值得我們從各個角度仔細推敲,慢慢品味。
參考文獻:
[1]Lawrence,D.H.Lady Chatterley’s Lover,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篇7
獨特而豐富的人生經歷賦予了莫言獨特的文學語言特色,他的小說涵蓋獨特的修辭、方言、俗語、色彩詞等。諸多學者從語法、語義、句型等各種角度對莫言小說的語言特色進行了研究,本文將莫言小說里運用的語言分為四大類:常見修辭式語言、常規運用式語言、突破常規式語言、自由混雜式語言,力求全面概括并分析莫言小說的典型語言特色。
一、常見修辭式語言的使用
高考規定的8種常見修辭手法包括:比喻、比擬、借代、夸張、對偶、排比、設問、反問。我們認為,莫言小說中使用的典型修辭式語言指運用比喻、比擬、借代、夸張、排比這五種手法的語言。至于其他修辭手法,如仿擬、移就、返源等,我們將其歸為突破常規式語言,在后面進行分析。
(一)比喻
比喻是莫言在小說中最常用的修辭格,獨具特色不落俗套,形象生動,給人新奇感。我們認為,莫言的比喻可分為諷刺比喻和非諷刺比喻,而大多彌漫著諷刺的味道。
例如:她在我面前第一次用眼里的水而不是用口里的水把臉濡濕了。她眼里流出來的淚水淺薄透明,仿佛沒有重量,這張紅色大臉上掛著的水就像馬頭上生出的角一樣令我難以接受。(《爆炸》)
這個比喻是對人物的諷刺,而如《透明的紅蘿卜》中“他的心臟像只小耗子一樣可憐巴巴地跳動著”這樣的比喻沒有諷刺意味,我們稱之為非諷刺比喻。
(二)比擬
1.擬人:有一匹全身皆白、只黑了兩只前爪的白狗,垂頭喪氣地從故鄉小河上那座頹敗的石橋上走過來時,我正在橋頭下的石階上捧著清清的河水洗臉。(《白狗秋千架》)
2.擬物:奶奶鮮嫩茂盛,水分充足,她出口的細語被厚重的轎壁和轎簾吸收得干干凈凈。(《紅高粱家族》)
(三)借代
如“黃毛的臉皮很單薄,嘴唇紅得有點妖里妖氣;上唇上一層細軟的茸毛,平平坦坦的獅子鼻”(《金發嬰兒》)中的“黃毛”,“爺爺的隊員像木樁一樣倒在鬼子的腰刀上,啞巴屁股倚在汽車頂上,胸膛上有幾股血竄出來”(《紅高粱》)中的“鬼子”、“啞巴”,就是運用了借代的修辭,以代表人物特征的詞指代人,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生動。
(四)夸張
例如:你走回家,一頭栽到炕上,腦袋脹得如柳斗般大,四肢麻木,好像死去一樣……(《歡樂》)
(五)排比
莫言在小說中運用的排比式語言并非嚴格意義上結構整齊的排比語句,而是彰顯莫言天馬行空張狂性的長短參差結合的排比句。
例如:聽一聽,看一看,摸一摸,穿一穿,一聽如同銅鑼聲,二看如同綾羅緞,三看毛色賽黑漆……我擔保您在家里坐半個時辰,您家房頂上那厚厚的雪就化了,遠看您家,房頂上熱氣騰騰,您家院子里,雪水淌成了小河,您家房檐上那些冰凌子,噼里啪啦就掉下來了……(《生死疲勞》)
二、常規運用式語言的使用
(一)帶鄉土氣息的方言詞匯的使用
例如:不,我要說,姜寶珠拍拍門,對著房間里早已停止嚎啕的華中光喊:中光,你孬好還有一個哥哥在家,父母也健康,沒結婚無牽掛,你鬧什么?(《戰友重逢》)
“孬好”是高密方言,譯為“不管怎樣”。
(二)民間口語化的句式的使用
姬鳳霞在《從句式看莫言小說語言的民間口語化》中說:“莫言一直致力于營造一種‘民間話語’的敘事系統,口語句式被作為文本主要的構建材料,其中的短句、省略句、插入語、整句等都帶有鮮明的民間口語語體特征。”本文主要研究和討論的是莫言小說典型語言特色問題,所以我們在此僅舉出莫言廣泛使用的典型的插入語。
例如:兒媳婦剛拆洗過的被褥散發著清雅的肥皂味兒。――俺的兒媳婦名叫紫荊――紫荊嗓子略有點沙啞,語聲低低的,很甜,很迷人。――那天她對我說:娘,你摸摸看,我給你換了一條緞子被面。……真的,娘,我不騙你,你年輕了十歲――紫荊嘰嘰嘎嘎笑起來――俺兒媳婦就是愛笑――她的笑聲變化多端……(《金發嬰兒》)
(三)成語、俗語以及歇后語的使用
寫小說、散文等,恰當地引用成語和俗語不但能為文章添彩,增強文章說服力,而且能體現作者深厚的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底。莫言對成語和俗語的運用可謂是淋漓盡致、筆下生輝。
例如:老態龍鐘的支部書記從辦公室跑出來,六神無主地站在院子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盲人摸象般走到教室門口,聲色俱厲色厲內荏外強中干嘴尖皮厚腹中空地吼一聲:不許高聲喧嘩!然后頭重腳輕根底淺地走著,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如漏網之魚。(《歡樂》)
各類成語、俗語的運用行云流水,幽默詼諧地表現出支部書記步履蹣跚、心事重重、慌張不堪的生動人物形象。
(四)擬聲詞和疊音詞的使用
1.擬聲詞。例如:車輪破了,哧哧地泄著氣。汽車轟轟地怪叫著,連環鐵耙被推得咔噠咔噠后退,發親覺得汽車像一條吞食了刺猬的大蛇,在痛苦地甩動著脖頸。(《紅高粱》)
加點字都是擬聲詞,不僅形象生動,而且符合莫言的生活經歷,具有濃厚的山東特色。
2.疊音詞。例如:天蒙蒙亮時,父親感覺到有人在自己腰間摸摸索索做文章,打一個滾爬起來,急摸腰間,空蕩蕩沒有一物,才要轉身,兩支冰涼的槍口頂在了腰上,他聽到連長在背后冷笑著說:“兔崽子,舉起手來!”(《野種》)
“天蒙蒙亮時”比“天剛亮時”更具語言美和形象感,“摸摸索索”暗含出“偷偷地、謹慎地”動作行為,“空蕩蕩沒有一物”雖然沒有“空無一物”簡潔,但一方面可以體會出父親腰間的東西被人取走得徹底,一方面又暗含父親發現時內心的失落。
三、突破常規式語言的使用
(一)色彩詞的使用
色彩詞的廣泛使用是莫言小說語言區別于其他作家語言的最大特色之一。莫言認為“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據統計,在8萬字的小說《紅蝗》中,竟出現了400多次色彩詞。
莫言小說運用的色彩詞可謂五顏六色俱全,但毫無疑問,莫言小說的讀者首先會想到紅色。莫言小說《紅高粱》《透明的紅蘿卜》《紅蝗》《紅耳朵》等作品名稱中就有紅色這一色彩詞。又如《白狗秋千架》《白棉花》名稱中有白色這一色彩詞,《金發嬰兒》名稱中有金色這一色彩詞。
俄國著名的現實主義繪畫大師列賓有言:“色彩即思想。”莫言在小說中運用的色彩詞,有的保留了原本內涵,有的被賦予了特殊的意味。如:一輪巨大的水淋淋的鮮紅月亮從村東邊暮色蒼蒼的原野上升起來時,村子里彌漫的煙霧愈加濃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那種凄艷的紅色。這時太陽剛剛落下,地平線上還留著一大道長長的紫云。(《枯河》)
此段描寫渲染了一種凄清的氛圍,暗示著一種不祥的結局。紅色原本象征著熱情、喜慶、陽光等,但莫言運用紅色表現的是傷感悲涼的境界。“紫云”中的“紫”保留了不祥、惡毒之義。我們知道,孔子曰“惡紫以奪朱”,因為紫色為間色。金庸先生博學多識,就很擅長運用色彩詞給小說人物命名。如《天龍八部》中的阿朱和阿紫,雖為姐妹,但二人性格秉性不同,阿朱為人善良,而阿紫力圖取代姐姐阿朱。還有,我們知道,導演往往將電影中扮演深藏武功的惡狠太監的演員的嘴唇涂成紫色,以表惡毒無情。
此外,綠色的運用也很傳神:
A.表示憤怒:他的眼睛因激怒發出綠色的光芒。(《紅蝗》)
B.表示生命的枯竭和衰敗:二奶拼盡全力嚎叫一聲,好想奮身躍起,但身體已經死了,她眼前一片黃光閃過緊接著出現綠光,最后漆黑的潮水淹沒了她。(《狗皮》)
(二)對在邏輯上相矛盾的語言的使用
例如:我終于領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紅高粱》)
我們知道“美麗”和“丑陋”,“超脫”和“世俗”,“圣潔”和“齷齪”,這三組詞明明是相對立的,為何莫言放在一起來形容自己的家鄉,而我們認為這樣突破常規的語言運用在內容上又合乎邏輯、可以理解呢?我們認為,莫言的語言特色是扎根于故鄉的,他是“尋根文學”作家,他的小說充滿了“懷鄉”、“怨鄉”之情,他所經歷的民間生活正存在著美麗與丑陋、善良與邪惡、燦爛與暗淡、寧靜與喧鬧等相對立的各種因素,那么莫言對在邏輯上相矛盾的語言的使用不但可以為讀者所接受,而且更能表現莫言對故鄉的愛恨交織,越愛越恨,越恨越愛的復雜情感。
(三)詞語組合搭配的變異
1.仿擬。
A.改變個別詞或字,創設陌生化新奇效果。例如:因為,這個具有一部分俄羅斯血統的雜交二代一定會成為掌上鉆石。(《十三步》)
將“掌上明珠”中的“明珠”換成同樣貴重的“鉆石”其實意義并沒有多大改變,但恰恰營造了陌生化、新奇、獨特創新的語言效果,讓讀者接受的同時,更加佩服莫言推敲語言的超凡能力。
B.改變數量詞,增強表達的精確性。例如:你匆匆忙忙地換上了一件唯二的襯衣。(《歡樂》)
莫言仿擬“唯一”做出“唯二”一詞,運用得十分巧妙,暗含農村青年只有兩件襯衣,要換也只能換唯有的兩件中的另一件,因此稱其為“唯二的襯衣”再恰當不過了。“唯二”將農村青年的貧困程度精確到了極點。
2.移就。例如:班長遞給你兩片安眠藥他說沒有水,你一仰脖子吞了藥說不要水。班長,給我兩片吧……從班長身后伸過一只失眠的手,可憐巴巴地說。(《歡樂十三章》)
一般認為,移就指將描寫甲事物性狀的詞語用來描寫乙事物的性狀。“失眠”本是形容一個人睡不著覺,這里用來形容“手”,我們認為作者其實要表達的是“失眠的人伸過一只有氣無力的手”,但這樣說實在太過呆板,不如“伸過一只失眠的手”簡潔形象。
(四)語義系統中不常用意義的激發
我們來看《紅高粱家族》中的一句話:“路西邊高粱地里,有一個男子,亮開坑坑洼洼的嗓門……”起初我們或許認為“嗓門”的修飾形容詞與它搭配不當,我們都知道“坑坑洼洼”指地面或器物表面凸凹不平,應該改為“高低不平”,但莫言將“坑坑洼洼”置于句子中以后,由于受“亮出”和“嗓門”這兩個詞語的擠壓,“坑坑洼洼”語義系統中高低不平的意義便被激發和凸現出來了,莫言如此用詞新奇又形象。
(五)返源格的使用
江南參見王希杰的《說話的情理法》提出莫言小說運用了返源格的手法,他說:“所謂返源格是指偏離一個詞語的通行的一般的語義,而返回到它的語源意義上使用它,以便達到某種反常的效果。”江南所舉例子最經典的是《歡樂十三章》中的“我咬牙切齒地不笑”。“咬牙切齒”本來是形容極端仇恨和厭惡的意思,莫言在這里卻使用了它的原本意義:緊緊咬住牙齒。再來看一例:校長站在講臺上氣宇軒昂,他是一個中年人,面黃無須,人中漫長,下巴短促。(《歡樂》)“漫長”和“短促”一般是形容時間的,“漫長”也多用于形容道路,莫言在此只取二者的語源意義――長和短。這樣既押韻又幽默詼諧。
四、自由混雜式語言的使用
我們可以從《酒國》中酒博士寫給莫言的信中領略到自由混雜式語言的使用魅力。信中莫言將政治語言、學術語言、格言民諺、市井俚語任意交雜,任意拼接,展現了天馬行空的狂歡個性,使小說結構開放化、意義豐滿化,提高了諷刺的濃度,增強了表達的效果。如:“身在酒國,心在文學”;“在文學之海里扎猛子打撲騰”;“岳父者泰山也”;“我為了文學真格是刀山敢上,火海也敢闖”;“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我拜讀了您的所有大作,對您佩服得五體投地,一魂出世,二魂涅”;“您這些話猶如醍醐灌頂,使我頓開茅塞”;“正是:打開兩扇頂門骨,一桶茅臺澆下來”;“小的不敢嗦”;“弟子這廂有禮了”等。
參考文獻:
〔1〕張愛萍.莫言小說語言研究[D].安徽大學,2007.
〔2〕劉秋云.試論莫言小說語言的鄉土特征[J].時代文學(上半月),2008(2).
〔3〕江南.漫議莫言的修辭追求[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
篇8
一、由小說三要素與小說主題形成的小說“四面體”
三要素,也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小說三要素,包括小說的人物,環境和情節;而四面體,則是由三要素與小說主題構成的“四面體”。其關系圖如下:
以主題為中心,三要素為點,構成一個四面體,且將之稱為“小說四面體”。
小說閱讀鑒賞,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小說四面體”所反映的種種問題,解決了“小說四面體”中幾個要素的關系,也就解決了小說的閱讀鑒賞問題。
在“小說四面體”這個圖中,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都是相互的,是不能脫離任何一個要素而獨立存在的。“小說三要素”之間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所以,在“小說四面體”中的幾個要素都是以一個整體而存在的。
人物在典型環境中活動,環境反映人物典型性格,人物成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環境同時影響或推動人物命運發展,即推動或影響情節發展。
人物、環境之所以典型,是主要通過情節來表現。情節是按照因果邏輯關系組織起來的一系列事件。高爾基說:情節“即人物之間的聯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相互關系――某種性格、典型的成長和構成的歷史”。由此可以得知,小說典型人物的塑造需要通過情節來表現。小說通過情節表現人物性格特征,通過情節揭示小說主題,情節也可以暗示環境,渲染環境氛圍,突出小說主題。
環境描寫有多種作用,或反映時代特點,或反映地方風情,或渲染氣氛,或推動清節,或表現人物性格,或提供人物活動的場所……環境是人物的語境,因此小說教學必然要引導學生分析環境描寫。環境揭示小說主題的前提與背景,脫離了一定的環境,尤其是社會環境,也極大地影響了對小說主題的揭示。
另外,這里的人物包括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在這個關系圖中,人物中的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環境中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都存在著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
小說“三要素”與小說主題構成了一個“小說四面體”,他們之間關系都是息息相關,緊密聯系的。若想解開小說主題的謎底,還需要從小說“三要素”下手,逐個破解。
二、典型化理論與小說教學
在“小說四面體”中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中,小說人物與環境都具有典型性特征。這是小說這種文學樣式的典型特點。
典型化的基本內涵就是按照典型的特征塑造形象和形象體系。使之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和深刻的普遍性。也就是由不典型或不充分典型的生活原形變為典型的藝術形象的過程。
因此,小說作者將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作為目標,揭示小說主題。對于讀者而言,只有抓住了小說人物與環境的典型性特征,便把握了小說的靈魂。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說的情節可以虛構,人物可以虛構,但是,小說的典型環境和人物的典型性格需要真實,否則,小說主題便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
以《祝福》為例,祥林嫂這個人物可以是虛構的,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是,與祥林嫂這樣的社會底層的勞動婦女形象相似的,在社會中是存在的,并且是某一類中的某一員。魯鎮這個地方可以在現實中不存在,但是跟魯鎮這個環境相似的社會環境在現實中是存在的,不是“魯鎮”,可以是“李鎮”、“劉鎮”。也就是別林斯基所說的“熟悉的陌生人”,小說人物與環境對于讀者而言,既熟悉又陌生,這就是典型性特征。
三、鑒賞“環境”描寫,揭示小說主題的秘鑰
文學鑒賞中,所有鑒賞都離不開對語言的鑒賞與把握。雖然小說語言相比其他文學文體作品而言比較通俗易懂,但必要時候,我們仍需用鑒賞詩歌語言的方法對小說語言加以鑒賞,方能理解其精妙。
篇9
在網絡文學中,網絡小說的影響最大,發展也最快。有玄幻、奇幻、言情、武俠、游戲科幻等各種類型,還出現了微博小說等篇幅短小的網絡小說。這些小說與傳統紙質小說的差別不僅在于傳播媒體與寫作主體的不同,還在于其內容較時尚,語言較前衛,更受當下一些喜歡讀電子文本的年輕人的青睞。網絡這種傳播媒介使網絡小說的語言具有了更鮮明的時代潮流的烙印,使其成為時尚文化符號的代表,同時,網絡小說的語言也具有虛擬化、鄙俗化、機械化的特點,這些特點既彰顯了網絡小說語言獨異的創造力與鮮活的生命力,也暴露了其弊端,讀者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一、時尚化
網絡小說的作者具有較強的創新意識,他們對時代潮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喜歡追求時尚與前衛,這在網絡小說的語言上有非常鮮明的表現。
首先,網絡小說語言的時尚化體現在數字、英文字母、漢字、符號的大雜糅,形成了一種時尚文化符號。
趙趕驢的《趙趕驢電梯奇遇記》中就有許多用拼音縮寫符號與漢字組合寫出的句子,譬如“正在YY(聊天)”“一邊在心里猜測白璐還是不是CN(菜鳥),一邊BS(鄙視)自己。” “上眼皮和下眼皮老是KISS在一起” 、“白琳和老刑GAMEOVER了。” “這下是悲情牌,雖說有點兒窩囊。但湊合著也要用呀~~~” 這些時尚元素在網絡上常見,強化了語言的表現力,增強了作品的時尚性。
有些網絡小說作者還通過能表現聲調、表情的符號來加強作品的表意功能,使語言更為形象。如在風云小妖的《愛上狐貍精弟弟》中有這樣的句子,“額-_-|||熊貓眼??!”“O(∩_∩)O~魔鬼,這個人一定是魔鬼”。這些句子中通過各種符號來形象地體現人物內心的情感變化。在網絡小說中,作者常常通過一些表情符號來表達內心的情感。這種形象的表達方式與傳統文學作品中通過語言來描寫人物的表情相比較更直觀、更傳神。表情符號非常豐富,悲傷的、興奮的、氣憤的、懊惱的等等,網絡小說的作者常在作品中大量使用這類表情符號,如顧漫的小說《微微一笑很傾城》中就有很多表情符號,如:屏幕上,一笑奈何的人物還是安靜地站在柳樹下,幾分飄逸,幾分灑脫。微微看了半晌,發過去:“大神……你被盜號了么==”他說得還真自然,微微黑線了一下,打出笑臉:“大家好^_^。”因為這部小說的內容與網絡游戲有關,故小說中的人物對話常是QQ中的對話,因而使用了大量的表情符號,這符合現實生活中QQ對話的真實情境,是讀者能夠接受的。
其次,網絡小說語言的時尚化體現在時尚流行語的使用更為頻繁。
網絡小說的作者能靈活地運用流行在網絡上及現實生活中的時尚流行語,給讀者以新鮮感。這一點得到了許多論者的認同,有論者認為,“網絡是現代技術的結晶,網絡烙印著現代潮流的新時尚。網絡使世界的距離拉近,世界的流行時尚自然而然也彌漫于網絡小說而凸顯其前衛性。‘網絡’或許是由于通常游走于網絡世界,不僅對現實世界各地的風云變幻洞若觀火,而且更多地接受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新潮思想觀念,頻繁地追蹤,甚至追逐國際時尚。”①
如“菜鳥”成為新手的代名詞;“斑竹(版主)”成為論壇管理人員的新稱號;“樓上”“樓下”則成為先后兩個發帖人的稱呼。這些新詞充實了漢語的詞匯,使某些詞匯的表意更為豐富。再如,在網絡小說《粉紅四年》中,有一段話是這樣寫的,“如果一個男生身高不足160,我們就叫他半殘廢,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們叫她殘聯主席。如果一個男生一毛不拔,我們就叫他鐵公雞,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們就叫她雞舍清掃員。如果一個男生常常趁火打劫,我們就叫他土匪,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們就叫她壓寨夫人。”“殘聯主席”“鐵公雞”等,在這里都有了特殊的含義,增強了作品的幽默化效果。這類時尚化的語言在網絡小說中隨處可見,其中常還夾雜著大量流行語,如“我靠”“去死”“掛了”“哇塞”等,這樣時尚的語言吸引了大量年輕讀者。
二、虛擬化
網絡是一個虛擬的世界,許多網絡小說也是靠大膽的虛擬贏得了讀者。像玄幻、奇幻、魔幻、仙俠等類型的網絡小說都是非現實的,有的甚至以網游為虛擬背景來編織情節。因此,網絡小說的語言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虛擬化的現象。
譬如奇幻小說《褻瀆》的敘事語言就充分體現了虛擬化的特點。小說開頭就寫“神圣歷682年”“大陸的名字千奇百怪,基本上一個國家就有一種稱呼。近年來隨著神圣教會的興起和教權的擴張,各國逐漸接受了格羅里亞作為大陸的名字,意為神的贊美詩。萊茵同盟位于大陸東南角,是由十多個大小公國聯合而成,與大陸三大強國德羅、奧匈、阿斯羅非克相比國力只能算是二流國家。”這些地名完全與現實無關,虛擬的“大陸”,虛擬的國家,虛擬的人名,一切都是虛幻的。能營造出這樣豐富、神秘的世界,彰顯了作者想象力的豐富與怪異,也給讀者帶來了一定的閱讀愉悅感。“虛擬的網絡成就了虛擬化的言說網語,真實地表達了作者對未來美好世界的構想,為未來人們的生活模式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生存空間。”②
三、鄙俗化
由于網絡小說的作者一般都用筆名發表作品,其真實身份讀者了解較少,這種身份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給網絡小說語言的鄙俗化提供了“良機”。網絡小說的作者往往無所顧忌,使一些粗俗、骯臟的話語出現在作品中。
如《趙趕驢電梯奇遇記》中的句子,“到了。嘴上說,心里卻道:NND,偶們那邊離上海就幾小時的車程,怎么可能不到?” “MD,這個部門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很吊,可真正干的都是些沒人干的爛活……我在心里大叫:電梯呀電梯,你能不能下得慢一點,最好你 TM能給我停下來,……電梯,我 TM太愛你了!……”
這些粗俗、骯臟的語言頻繁出現在網絡小說中,似乎這些不文明的語言已成了敘述者的口頭禪,這無形中降低了網絡小說的美感,甚至引起讀者對其鄙俗語言的反感。
四、機械化
傳統小說中有許多經典名句流傳甚廣,語言精美且內蘊豐富。于是一些網絡小說作者便把這些經典的句子經過適當改寫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對此,有人認為起到了詼諧幽默的效果,有人認為是對文學經典的褻瀆。筆者認為,這類句子如寫得好,確實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寫得不好,則給人一種機械模仿、褻瀆經典的感覺,適得其反。
天下霸唱的《鬼吹燈》中就有許多借用經典流行語組成的句子,如“幾千年來,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流成了海,斗爭失敗了,失敗了再斗爭,直到取得最后的勝利,為的就是壓在我們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我革了半輩子的命,到頭來還想給我安排封建制度下的包辦婚姻?想讓我重聽慣二遍苦,再造二茬兒罪?我堅決反對,誰再提我就要造誰的反。”“看來我要去見馬克思了,對不住了戰友們,我先走一步,給你們到那邊占座去了,你們有沒有什么話要對革命導師說的,我一定替你們轉達。”這些經過變異的經典名句不僅勾起了讀者的閱讀回憶,也增強了作品語言詼諧幽默的效果,運用得還是不錯的。
再如九夜茴的小說《匆匆那年》中也有這樣的句子:“小學時我們一邊在老師面前唱‘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小鳥說早早早,你為什么背上小書包’;一邊在伙伴面前唱“我去炸學校,從來不遲到,一拉線,我就跑,小學校轟的一聲炸沒了。”這里改寫了經典歌詞,體現了我們這一代的叛逆與嬉戲心理,語言幽默,給人以妙趣橫生的感覺。
但像下面這些句子運用得就有些機械,如《蔣干過江請鳳雛》中的一段話:“你倒是跳啊,屈原不是跳下去了?李白也快跳下去了,所以請你也快點吧。你倒是跳啊。……跳,還是不跳,這是個問題。”這段話是模仿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的對白改寫的,作者是想營造一種幽默的效果,把嚴肅的事情詼諧化,但表述很機械,內容也牽強。
再如《笑嘆三國?巧借荊州》中有一段話把“沉魚落雁”說成是“水深火熱”,“魚沉入水底,是不是水深?月亮閉了,晝夜太陽,是不是火熱?”這種聯系無疑是歪曲成語的本意,引起讀者的誤讀,這是褻瀆經典的表現。
此外,還有一些英文的縮寫不夠正規,導致很多中英文都懂的人也莫名其妙,這也是網絡小說作者在使用這些英文縮寫詞應注意的問題。
綜上所述,網絡小說具有時尚化、虛擬化、鄙俗化、機械化等鮮明的特色,但這些特色既彰顯了網絡小說語言有生命力的一面,也暴露了其糟粕的一面。但正如有論者所言,“網絡小說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形式,在語言上的一些鮮明‘創制’,給規范和習慣中的漢語及漢語表達帶來了巨大沖擊,引起了人們強烈的關注。”③就這一點來說,網絡小說還是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并深入研究的。
參考文獻
篇10
俄國形式主義提出陌生化概念,其出發點認為只有通過藝術程序(陌生化)的分析才能找到文學的內在規律,才能發現文藝作品成為藝術創作和審美對象的特殊性。英國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描寫了三位主人公的每個細微的語言、行動和思想的細微變化,充分展示了他對人生和生活的認識及細膩的洞察力。
一 陌生化語言的發展與特點分析
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陌生化”研究等都是以黑格爾的理論為基礎的。自從陌生化理論被廣泛傳播以后,這種帶有詩性語言特征的小說一直被作家嘗試,如托馬斯·曼的《魔山》、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等都是帶有非常明顯陌生化語言特征的作品。
在小說中,極其普通的日常語言被以美學的方式加以使用,它們完全背離了常規用法,通過一些手段使非指稱行為突現出來,形成一種與指定現實總體疏離的力量,使此在不斷地向他在轉化,現實主體不斷地與虛構主體相遇而重新確定主體的現實地位。這種語言的陌生化并不只是為了新奇,而是通過新奇使人從生活的漠然或麻木狀態中驚醒起來,“恢復對生活的感覺”。所以,語言的“陌生化”是為使讀者產生新鮮的體驗。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有這樣的描述,“陌生化”是一個人在感受童年與茶品的時候形成的通感,類似于“那被子上有太陽的味道”。通過這個感覺,童年的記憶變得深刻而親近,這就給了讀者一種新奇感,增加了陌生化效果,使得小說具有了虛構性。而讀者在反復咀嚼這句話、這個段落時,產生了與作者一樣的感覺。
二 英美文學中的陌生化
文學語言陌生化雖然發源于俄羅斯的文學理論,但是運用的相對比較明顯得是在意識流小說中,通過對意識流小說中陌生化語言的特點,我們可以看出隨著英美文學的發展,語言陌生化也發展起來。
“意識流”一詞是心理學詞匯,是在1918年梅·辛克萊評論英國陶羅賽·瑞恰生的小說《旅程》時引入文學界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為“意識流”作家洞察描寫人的心理起了規范作用。他們的理論相互依賴、相為支持,構成一整套完整的“意識流小說”理論。意識流小說盡管風格不同、表現不同,但他們都特別注意語言的表現形式,讓文中人物自己直接展現了心理活動過程,而這種展現大多是看似雜亂的、反復的,而且是一種狂歡似的跳躍。所以這種看似雜亂和反復的表現實際上孕育著語言陌生化的特點。再加上意識流小說家認為,只有把內心世界混亂無序、朦朧的潛意識活動直接展示出來,才能真正揭示其內在的真實。而這種創作觀點“不可避免地破壞敘述的邏輯性,使敘述語言支離破碎,甚至破壞了語言規則, 導致語言的扭曲,變形和陌生化,即語言的變異。”
英美意識流的小說很多,比較典型的有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維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威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作品,他們都是運用了陌生化語言使得作品別具一格。他們認為,人的深層思想內模模糊糊、缺乏邏輯性、沒有嚴密組織和思考的潛意識。因而作家常用一些不常規的不合乎語法規范的語句來表示,使人物的心路歷程的構建潛意識活動原原本本、生動逼真地反映出來,以引起人們思想的共鳴。如《尤利西斯》的第十八章中不分段落、沒有標點,描寫穆利根在朦朧欲睡狀態下,思緒飛揚。正如本書譯者文潔若說:“作者猶如天馬行空,浮云流水,想到哪里寫到哪里,還信手引入他過去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所以意識流的創作可以看成是對思想的還原,而意識流小說的閱讀則是從還原的思想中生發出讀者自己的思想。
三 典型作品中的典型陌生化語言分析
本文將更加清晰地概括《尤利西斯》中的陌生化語言特征,即:語言意象的可感性、語言組合的超常性和語言表現的體驗性。
1 語言意象的可感性
眾所周知,《尤利西斯》是用大量的愛爾蘭英語夾雜著標準英語寫成的。而對于愛爾蘭英語比較了解的讀者是可以了解到為什么在小說的中文譯本里那么多的倒裝句型是與閱讀習慣截然不同的,而且很多句式中也沒有關系代詞,甚至沒有連接詞,這都跟喬伊斯的愛爾蘭英語的特定語法結構有關。《尤利西斯》中大量獨白的運用讓讀者完全看不到作者的行跡,純粹是小說中人物自己的真實意識流露,充分體現了口語化特征。這些也使得語言雖然陌生化,但是語言的意象是可感的。比如小說中有一段描寫了布魯姆的妻子在回憶起他們年輕時的戀愛時所表現出來的混亂思緒:從鮮花到眼睛,從芬芳到心靈,幾乎都是帶給了讀者一定的空間去思考的,并不是說語言的陌生化就是不著邊際,而是還是帶有一定的聯想成分的,雖然在這個段落中沒有標點、沒有連接詞,但是其中對于思維的一定排列順序使得讀者可以通過自身的思維和意識去判斷文中人物的情緒和要表達的思想感情。眼睛是不能問話的,但是眼睛在這里變成了交流的工具,熱戀中的人能夠體會到那種眼神交流的令人陶醉的場景。因此盡管令語言學家費解,但是普通人能夠通過閱讀感知當時熱戀中的兩個人是多么的難解難分。
布魯姆在為妻子準備早餐歸來時,看到妻子還躺在那張床上時,想起那是從直布羅陀運來的老古董。然后他出門到德魯加茨肉鋪買了一個豬腰子,并對街上看到的女人們展開聯想。回到家時他發現有兩封新信和一張明信片,其中寫給莫莉的一封來自莫莉的經紀人(兼情人)“一把火”鮑伊蘭,他正籌劃著一場邀請莫莉參加的巡回演出,另一封是布魯姆在照相館工作的十五歲的女兒米莉寫給他的感謝信。然后他給莫莉送上早餐,盯起掛在墻上的寧芙沐浴圖看。這些聯想還是有著關聯的,比如從妻子聯想到老古董,又從妻子聯想到了街上的女人,又從信封和明信片聯想到了妻子的情人等。小說以莫莉長達40頁的內心獨白結束。莫莉躺在床上,在半睡半醒狀態中意識流不斷進行。一句話多達2000多個詞,完全無標點,無大寫字母,以此來表明她的意識流動的連續性和雜亂無章的流動的狀況,反映了她內心活動的復雜和思緒的紛繁。
在第八章的結尾,布魯姆跟在盲人的腳后走路,這一段是描寫盲人如何運用五官通感感知外部世界的內心獨白:“可憐的小伙子,他是怎么知道那輛載貨馬車就在那兒呢?準是感覺到了。”“也許用額頭來看東西,有一種體積感。”憑借通感,可用手指讀書,為鋼琴調音。憑借嗅覺感知春天和夏日的來臨,感知每條街、每個人的不同氣味。通過人的眼、耳、鼻、舌、身彼此相通,相互感應的“自由聯想”來介紹人物之間的關系和交代文章的情節。所以語言雖然高度陌生化了,但眼前任何一種能刺激五官的事物都有可能打斷人物的思路,激發新的思緒與浮想,釋放一連串的印象和感觸,使讀者能夠感覺到其中的含義和作者的意圖。
2 語言組合的超常性
小說《尤利西斯》的語言是從自由聯想與內心獨白、內心分析的角度來進行寫作,最大程度地挖掘了人物心靈深處的情感潛流,以一種徹底革新的藝術方式表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的精神失落和價值危機。但是這種語言的排列是令人費解的、超常的。
在第七章中,布魯姆在報社印刷所觀看排字工排字,這時他的思緒又無端地飄向死去的父親和猶太人的歷史、宗教和東方故園,隨后又跳躍到教堂和喪禮上的歌曲。該段中引述了希伯萊經書,有意識地不用標點,是為了傳達歌曲快速的節奏,使語言具有與音節旋律相類的節奏感。接下來的幾句是布魯姆本人對這部歌曲的理解,并引發了他自己的一番議論。最后布魯姆的思想又回到現實當中,“他排字排得真快”,經過一大段的內心獨白,小說語言上缺乏邏輯,但作者巧妙地表現了布魯姆內心微妙的變化,加深了讀者對主人公的理解。這種以眼前事物為依托,逐步闡述主人公的內心獨白,正是喬伊斯意識流中最常用的手法,更充分體現了語言陌生化的效果。
在第七章還有一段描述布魯姆在大街上看見正準備去和他妻子幽會的波依倫的心理活動,喬伊斯成功地運用了語言技巧表現了他的心緒,這一段并未點出波依倫的名字,但是喬伊斯巧妙地利用了“陽光下的草帽、棕黃色的皮鞋”的意象作了暗示。布魯姆一眼瞥見波依倫的身影,但他拿不準又不敢細看,因此感到心煩意亂、內心紛擾。此時布魯姆的心境被喬伊斯用了一連串的短句和一些不完整的句子、急促的節奏,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最后幾句模仿了布魯姆氣喘吁吁、心神不定、不知所措的心境。文中完全不合乎句法規則的語言把布魯姆極力想擺脫困境的心情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
3 語言表現的體驗性
在文章中,語言表現的體驗性有很多,其中有幾個段落尤其著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令專家學者難以分辨語體色彩中的含義。
語言陌生化的手法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表現出意識流動的多變性、復雜性等。陌生化的很大原因在于當時社會紛繁蕪雜、各種現象雜然其間,這使現代作家更難認識社會現象的真正面目。他們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像現實生活那樣雜亂無章,因而他們在如實地描寫這個五光十色、光怪陸離的世界時,往往故意給這一切加上一個秩序和良好的結構,喬伊斯用無拘無束的“神話的方式”來表現這個難以摸捉的世界,既恰當又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文學作品的表現力,影響了20世紀的世界文學。
四 小結
《尤利西斯》語言陌生化的表現,充分展示了喬伊斯意識流技巧的高的運用。小說語言表現上除了內心獨白、自由聯想之外,還有蒙太奇、重復出現的形象、平行與對比等等,它們將現實與幻想中許多截然不同的場面加以剪輯組合,構成一個復雜的畫面。此外,小說使用與人物的年齡、生活特點,即“言隨人動”來真實地再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意識活動,使讀者能身臨其境,直接進入人物的意識流中去。這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成功的一個秘訣。
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還巧妙地選擇了英語中固有的聲色詞匯,以和諧適應各章的主題。所有這些特點使《尤利西斯》成為在創作方法突破傳統的楷模。這部小說語言的陌生化特點也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道明,還留待我們更深層次的挖掘。
參考文獻:
[1] 卡勒,李平譯:《文學理論入門》,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
[2] 劉秀杰:《康德拉小說的陌生化詩學》,上海外國語大學,2009年版。
[3] 榮潔:《茨維塔耶娃創作的主題和詩學特征》,黑龍江大學,2002年版。
[4] 詹姆斯·喬伊斯,蕭乾、文潔若譯:《尤利西斯》,譯林出版社,1994年版。
[5] 張欣:《從對話看宗教因素對巴赫金小說理論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03年。
篇11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創作的過程,其實就是作者個性生命體驗的文字呈現過程。小說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語言的成功與否是小說成功的關鍵。享有“短篇王”美譽的劉慶邦十分重視小說的語言,他認為“創作上語言是第一位的,帶著自己呼吸、有個人氣質的獨特的語言才美”。他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儀式》等一系列鄉村題材小說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以及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個性化的語言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劉慶邦小說的語言個性主要表現為地方化、本色化、審美化三個方面的特色。
一 地方化語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載體,鄉土文學作家們無不有意識地從方言寶庫中提煉、采擷鮮活的富有表現力的語匯進入文學作品,用浸潤著泥土氣息的語言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劉慶邦生于河南沈丘,他在這塊大平原上生活了19年,那里的地方語言在其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其創作中使用農民方言俗語時是信手拈來,隨心所欲,濃郁的鄉土氣息使人感到既親切又自然。比如,豫東地區方言中名詞后面往往帶上“子”這一后綴,這一語言現象在劉慶邦的鄉村題材小說中有充分的體現:瓜庵子、瘋杈子、玉米辮子、辣椒串子、箔籬子、奶漿子、白面劑子,這樣的詞語隨處可見。劉慶邦還善于使用民間語言寶庫中一些表現力極強的詞語,比如:
吹奏者塌蒙著眼皮,表情是職業化的。(《響器》)
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棗樹,四月春深,滿樹的棗花開得正噴。(《鞋》)
凡是高玉華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一聽到有關高玉華的消息,他心里就美氣的不行。
二姨以為香當著母親的面礙口,想把香拉到一邊去問個究竟,二姨一拉,香就一“卜楞”,二姨不能夠拉她走。(《閨女兒》)
這孩子,恐怕要丟搭壞。(《小呀小姐姐》)
這是一只大號的瓦碗,雞蛋茶盛得溜邊溜沿,不只是五個六個,還是九個十個。荷包蛋已經成疙瘩打蛋。(《相家》)
上述語句中加點的詞是豫東方言乃至河南方言中極富地方特色的詞語,這些詞語在一定區域內被一代又一代人長期使用,很傳神,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在日常口語表達中常常有規范的普通話詞匯不能替代的作用和魅力。比如“塌蒙”一詞所表達的意思類似于“耷拉”,但“耷拉”很難表達出眼皮下垂蒙蓋在眼珠上的那種狀態。“噴”的意思是花開得正旺,但卻比“旺”顯得更有氣勢。“美氣”一詞則蘊含了興奮、快樂、幸福等多重意思。“卜楞”寫出了對外力拉拽的推拒和反抗。“丟搭”指的是由于忙碌、貧窮等原因而疏于對孩子、家禽家畜的照顧。“溜邊溜沿”指東西盛得很滿,但卻比一個“滿”字要具體生動得多。
地方化的語言也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為方言是真正地來源于生活,和人們的情感有著難舍難分天然一體的牽連。劉慶邦在小說中還大量運用民間俚語歌謠等表現農民對生活的體驗和理解,一腔一韻表達著農民最樸素而豐富的思想,使其小說語言既新鮮、生動,又很有嚼頭。比如:
二姨笑了,說,我說過這兩個孩子是一對兒,不會有錯兒,一個葫蘆嘴,一個嘴葫蘆,都抱著葫蘆不開瓢。(《閨女兒》
好看不過對肚子瓜,當媒人的兩頭夸,母親允許表叔的話有所夸張。待到表叔把話說成了車轱轆,母親才說了一句:她叔,閨女的事讓您操心了。(《相家》)
在鄉村題材的小說中,用地方化的語言去敘述產生、流行這種語言的地區的生活,可以起到兩方面作用:第一,做到“文”與“言”的統一,即內容與語言的協調,增加真實的質感,對人事生活的敘述得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于是產生鮮明的地域或地區文化特色。第二,對于本地域、本地區的讀者,自然有一種親切感,增加其閱讀興趣;對于外地域讀者則有一種陌生感、距離感,這也可以使之產生閱讀興趣。在詞匯現代化的今天,有許多方言土語都在迅速湮沒,而劉慶邦小說中運用的地方化語言不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當時農民們活生生的口頭語言,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富有濃郁的地方風情和生活氣息,具體生動,可聞可感。
二 本色化語言
劉慶邦的小說立足于民間生活,站在民間的立場來寫民間。其民間立場不僅表現在其作品的思想內容、敘事風格上,在小說語言上也有所反映,具體表現在:某種程度上放棄知識分子在語言上的優越感和敘事中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識,用極富鄉土本色的語言來書寫鄉村人物與鄉村生活。
劉慶邦認為:“我們寫小說寫什么呢?無非是寫人,寫人的喜怒哀樂,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寫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寫人性的豐富性……”那么如何來寫人物呢?劉慶邦強調要貼著人物寫:“看來還得貼著人物寫,這是我們寫作者的惟一選擇。要貼著人物寫,我們腦子里起碼要裝著一些人物。這些人物或者是故鄉的鄉親,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親人親戚,等等。對這些人物,我們是應該比較熟悉的,知道他們怎樣說話,怎樣走路,怎樣哭笑,怎樣咳嗽。閉上眼睛,他們如在眼前。否則我們就無從貼起。”貼著人物寫,表現在人物語言上,就是盡量讓人物用他自己的語言來講話,讓人物說貼合自己身份、性格及生活環境的本色語言,怎樣的人,處在怎樣的地位,具有怎樣的情趣,便現出怎樣的語言風采。
《誰家的小姑娘》里農村小姑娘改的弟弟開放哭時,改的娘問:“放兒哭啥哩?”得知兒子餓時,她又說“一會兒不嚼我他就不能過”,娘雖然累得沒勁了,還是“一聲沒吭”讓兒子“嚼”她。后來娘讓改把地里的魚送到黑叔魚塘里去,改拒絕去,娘問“那是為啥?”改只說“啥也不為”。在娘中暑暈倒時,改帶著哭腔喊“娘,娘,你咋啦?”小說中僅有的幾處人物語言充滿了泥土般的質樸氣息,通過這些簡短而生動的口語,娘的辛勞和改的倔強躍然紙上。在小說《鞋》中,因為妹妹動了守明視如珍寶的鞋,守明跟妹妹吵起來了,守明質問妹妹:“誰讓你動我的東西,你的手怎么這么賤!”“還敢嘴硬,看看上面你的臟爪子印!”母親過來勸架,把鞋底看了又看,說這不是干干靜靜的嗎!守明說:“就臟了,就臟了,反正我不要了,她得賠我,不賠我就不算完!”母親說:“不算完怎么了,你還能把她吃了,你是姐姐,得有個當姐姐的樣兒。”這是一場真實生動的吵架場面,幾乎是將生活中姐妹吵架、母親勸架的語言原滋原味地搬到作品里了。
不僅人物對話是人物本色語言,與之相關的敘述語言也是非常符合被刻畫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小說《鞋》中有這樣一段敘述:“又開始給棉花打杈子時,守明心里像是生了杈子,時不時往河那岸望一眼。河那邊就是那莊子的地,地盡頭那綠蒼蒼的一片,就是那莊子,她的那個人就住在那個莊子里。”沒有激情澎湃的語言,沒有用到“思念”、“相思”、“刻骨銘心”之類的詞語,只是寫主人公時不時往河那岸望一眼的動作,作者用極富鄉土氣息的語言刻畫出了鄉村少女內心對未婚夫“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思念與渴望。再如《夜色》寫周文興定親后,心里“美氣”得不行,走起路來都格外“帶勁兒”,“美氣”和“帶勁兒”是最實在最真切的農民語言,表現了周文興定親后掩飾不住的興奮與激動。《相家》描寫“母親”將要親自去為閨女兒相家:“她想把這個事暫且丟下,該干什么還干什么。可是不行,她低頭是這個事,抬頭人還沒有出門,夢里去相家已經去了好幾次了。”這幾句話簡潔素樸,通俗明白如家常話,既貼近農村婦女的身份和性格,又極富生活氣息,令人回味無窮。
本色化語言的運用使劉慶邦的鄉村題材小說從意識形態話語和知識分子精英意識所形成的夾擊里突圍而出,以生動傳神的對話和細膩到位的心理刻畫再現了民間生命豐富的情感世界。
三 審美化語言
劉慶邦曾說過:“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它的底蘊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用這些字的時候我是懷著敬畏之心,生怕哪個字用得不是地方,每句話,每個字都要推敲。”劉慶邦對待小說語言的態度是嚴肅的,他大量擷取民間語言寶庫的可貴資源用于小說創作,并沒有放棄知識分子對小說語言的駕馭,他的鄉村題材小說語言在地方化和本色化之外,還體現出審美化的特色。
審美化首先體現在對原始民間語言的提純凈化。在小說創作中,無論是地方化語言還是高度貼合人物身份、性格、生活環境的本色語言,對于鄉土文學作品的創作均具有普通話語匯難以替代的作用。但來自民間的東西往往是很俗的,如若把握不當,就會使得作品語言顯得過于粗糙、野性,甚至造成讀者理解的困難。劉慶邦在處理運用來自民間的語言時是很講究的,“俗”的表現方式也是極有分寸的。如《小呀小姐姐》對羅鍋子弟弟平路驅雞、罵雞的描寫,是用敘述人語言轉述的。這是一段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寫,用的是極其簡潔樸實的本色化語言,有幾分俏皮風趣,令人忍俊不禁。農家頑童那股子野性、倔勁活脫脫躍然紙上。若將口語中“罵雞”的語言原封不動地寫出,那必定給人一種過于粗俗之感,但經敘述人轉述,就化腐朽為神奇,既沒有改變原味,又顯得干凈和文雅多了。劉慶邦對少兒向來持肯定贊美態度,出于詩意化的需要,他把少兒的語言作了純凈化處理。
審美化還體現在小說敘述語言的詩意。敘述語言是敘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現的陳述語句本身,也就是作者為表達寫作意圖而使用的敘述、描寫等語言手段,它直接影響著作者表情達意的效果和讀者進行接受的效果,凡是優秀的作家,無不在這些方面刻意追求。劉慶邦的短篇小說都是從生活中捕捉一個人、一件事,或一個場景,娓娓道來,雖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也沒有委婉曲折的情節,敘述語言簡練含蓄,朗朗如白話,但卻總是能夠讓人感到一種細微而美妙的韻味,這就是他的敘述語言的魅力。如《野燒》中這樣描寫一條黃狗:黃狗似乎也認為自己這樣空嘴而歸對于三位貪吃的哥子不好交賬,它顯得很抱歉,遠遠地就塌下眼皮,低下頭,前腿一伸,臥倒在地,自我解嘲似地回過頭來啃自己的背。這樣的文字描寫,描神繪物,宛在目前,如同中國畫中花前月下必有一蝶一蟲一樣,在意境的寧靜平和中,增加了畫面的動感,強化了視覺效果。《曲胡》中也不乏優美雅致的語句:“秋葉飄零的夜晚,月白如霜,琴聲悠悠揚揚傳來,如泣如訴,使好多善良的農人癡癡呆呆,嗟嘆不已。”“三月春風戶外飄,柳條擺動,麥苗起伏,塘邊的桃花花蕊微微顫動,托春風捎去縷縷清香。”上述描寫典雅而通俗,有詩的意境、詞的節奏和散文的韻律,同時也與小說主人公凄美的愛情和諧一致。這份詩意更多的時候是素樸的、自然的,且看幾篇小說的開頭:
“清明節快要到了,地上的潮氣往上升,升得地面云一塊雨一塊的。趁著地氣轉暖,墑情好,猜小想種點什么。”(《種在墳上的倭瓜》)
“太陽升起來,草葉上的露珠落下去,梅妞該去放羊了。”(《梅妞放羊》)
“麥子甩穗,豌豆開花,三月三到了,三月三是柳鎮的廟會。”(《春天的儀式》)
這樣的開頭與汪曾祺的手法極其相似,開門見山,直入話題,用的是純自然的語言,自然得如日出日落、花開花謝、春雨冬雪一樣應時而至,于平淡中氤氳著素樸的詩意。
誠如劉慶邦所說:“我深信一個寫作者的價值就在于他對這個世界個性的獨立的表達。”作家在形成自己對生活的獨特體驗與發現之后,就要努力使小說的語言具有個性。反之,小說的語言個性又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小說的存在個性。劉慶邦鄉村題材小說的個性魅力即來自作家對鄉村生活充滿了審美理解的感受與關注,也離不開其地方化、本色化、審美化的個性文學語言。
參考文獻:
[1] 劉慶邦:《民間》,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篇12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7-0170-02
一、元小說的基本概念與發展簡史
“元小說” 英文名為Meta fiction , 從形式上看是“小說創作過程的小說”。是關注小說的虛構身份及其創作過程的小說。傳統小說往往關心的是人物、事件,是作品所敘述的內容;而元小說則更關心作者本人是怎樣寫這部小說的,小說中往往喜歡聲明作者是在虛構作品,喜歡告訴讀者作者是在用什么手法虛構作品,更喜歡交代作者創作小說的一切相關過程。小說的敘述往往在談論正在進行的敘述本身,并使這種對敘述的敘述成為小說整體的一部分。當一部小說中充斥著大量這樣的關于小說本身的敘述的時候,這種敘述就是“元敘述”,而具有元敘述因素的小說則被稱為元小說[1]。類似的還有: “超小說” (Surfiction) 、“自我生成小說” (Self begettingnovel) 、“內小說” (Introverted novel) 等[2]。雖然它也常與“反小說” (Anti novel) 共同稱謂, 但是從基本形式而言, “元小說”屬于眾多“反小說”中的一種。
在中國早期的評書、說書人傳統中,就有諸如“話說曹操”這種強調敘述者敘述的成分,歐洲早期的小說也有自我暴露敘述行為的典范[3],如喬叟的作品。而戴維·洛奇則認為最早的元小說是斯特因的《項狄傳》,它采用敘述者和想象的讀者對話的形式,表明敘述行為的存在。這種揭示小說奧秘和傾向的小說,曾被布魯克·羅絲命名為“實驗小說”,而愛德勒于1976年稱之為“超小說”,羅澤同年稱之為“外小說”。“元小說”這個術語在1980年左右開始得到公認。但據魯迪格的考察,80年代初的“元小說”無論創作還是批評,都羽翼未豐,到80年代末,“大批雄心勃勃的批評家和學者進入了這個現在屬于文學基本原理的領域。”
二、元小說的多維視角
元小說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體裁與表現方式,具有自身的多維多面表現特性。于根元在其著名的《語言哲學對話》中把文學語言定義為“多維的語言”,意即文學語言不僅僅是心智的產物,而且還是感官的、情感的和想象的產物[4]。同樣,元小說也正是體現了文學作品的這類特點。總體來說,元小說可以把語言層次和文化方面、物理尺度與心理視角、社會行為與個體意志有機地合為一個審美的虛擬世界,故我們把元小說的文學語言從以下三個視角來詮釋。
首先是理性視角。元小說是文學作品的一種特殊新型體裁,所以它必然具有文學語言本身的表現理性的一面。無論中國的《史記》,還是西方的《荷馬史詩》,這些具有元小說性質的文學和歷史敘事作品擁有理性鑒賞價值,如實描述了作者和客觀事實之間的互動。無論元小說進行怎樣的變化,它都是把敘事與創作過程結合而成的詞語進行合理的組合。在這一方面,小說用語的工具職能、邏輯規范以及理性特性表現得較為集中。所以,在本視角,語言理性、邏輯理性和社會文化等理性因素起著重要作用[5]。
其次是感性視角。元小說是借助作者創作自述來傳達故事的內容與內涵,于是元小說的獨創性又決定了文學語言的個性特征。比如作者自述的參與、內容事實的交織、情節的重組、陳述故事的獨特方式,都對文學風格施加影響,造成所謂的“語境變革”,使元小說所傳遞的信息帶上了穿越的心理色彩,自然,語言文字與順序也呈現出再造與重構,所以,這一視角的理解,須借助感性思維建構去進行。
最后是審美視角。元小說作為藝術形式,它必須是一種美的表達,所以元小說語言在傳遞內容、表現感覺、虛構故事時又必須以美的方式去完成,從而創造出具有審美感覺的文學語言來。于是,從外形的聲音色彩、內部的內涵情況,從時間上的表述過程到空間上的外在形態都必須也必然是符合審美原則的。所以,這一視角來說元小說又是符合審美規律的。
三、元小說作品的兩面視角
元小說除了表現出理性、情感和審美構成的三維視角特性,同時還具有藝術層面的正負兩面:“意蘊”和“意思”。關于文學語言的“意蘊”和“意思”,早在十幾年前,學術界就作過廣泛的討論,和元小說語言觀有直接聯系。可以肯定地說,這一中外都歷史悠久的“符號文獻”形式確實非常簡潔,道出了元小說的一個重要性質。在“開頭”中引用美國文學家薩丕爾“當表述非常有趣的時候,就管它叫文章”的觀點也是屬于這樣的認知[6]。然而重要的是,“意蘊”和“意思”本是“A身上有B,B身上有A”的一體關系,很難斷然分離開來。“有意蘊”的敘述“意義”和被元小說敘述的“意義”“有意蘊”往往是互為先后的。所以在元小說創作中把好多“意蘊”如情緒、趣味、印象等歸為“意義”,就是英國文學家杰里弗·利奇,也曾在《語義學》描述的七種內涵中多次涉及“意蘊”,如他說的“內涵”、“社會定義”、“感情涉及”、“反饋”、“配合”和“主義”中往往說的就是“意思”。那么,“意蘊”和“意思”、“有意蘊”和“有意思”的關系怎樣呢?我們認為,元小說是有思想的創作,表達的結果是創造出內外函一致的“意蘊”來,于是“有意蘊”本身也就成了“意義”;反過來,當我們解讀“意義”時,發現一個尋常詞語一經“有意思”的表達,往往舊瓶裝新酒,在原有思維意蘊之外產出了不少言外之意、模糊含義、兼容含義等,而這種一文多內容的“意蘊”自身就非常“有意蘊”。從這兩個層面,如果把“有意蘊”表述為“具有審美內涵”,把“有意義”定義為“具有具體指向”,那么,元小說就應該是“既富有審美內涵的,又有所指向內容”的文學語言。
四、總結
作為一種新興文學體裁,元小說引起研究和關注是正常的,但評論家和學者們真正關心的,是元小說所具有的巨大潛能:它解除了對“事實”的依賴,破解了現實主義風格的主導位置,并展示了現實主義風格的虛偽性和欺瞞性[7]。元小說以暴露自身生產過程的形式,表明小說就是小說,現實就是現實,二者之間存有不可逾越的差距。通過對元小說的多維視角,包括理性、感情和審美,和兩個層面,意蘊和意思的分析,來賞析元小說的特征與內涵。揭示藝術和生活的差距是元小說的一種功能。而敘事與現實的分離,使文本不再成為現實的附屬品,文本闡釋依據的框架不再來自于現實,文本的意義不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來自于純粹的敘事行為,文本因此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治權利,從現實和“真實”的桎梏之下獲得徹底解放。
參考文獻:
[1]、王蒙《小說創作與我們》,《上海師大學報》2000年第4期
[2]、高爾基《論文學》,孟昌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21、第302頁
[3]、王希杰《這就是漢語》,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頁
[4]、孔憲中《語法與文句的格局》,香港《語文建設通訊》1990年7月號
篇13
一、莫言小說的方言特色
1.莫言小說中方言詞語的不同類別
(1)自然、時節
傍黑、老春、穿堂風……
(2)動物、植物
魚狗子、雨信鳥、造橋蟲,地排子車、話殊子、八格棋、地龍、磨菇釘、傘扇、旗牌、面刺猬……
(3)衣著、食物
截瘧布條、水紅緊身衣、高麗褲子、褲權、尼龍襪子、火燒……
(4)描述、形容
好使、差不離、拐款、打眼罩、瘟頭瘟腦、閉了威、賊(很)、埋汰、膩歪、困覺、修理(整治)、風光(體面、熱鬧)……
(5)生理、人體
皮色、指肚、身腰、氣嗓子管、毛羽、耳巴子、眼翅毛、疤扭、抬頭紋……
(6)稱謂、人品
二賴子、姿子、半拉子勞力、舉子、大家伙……
以上是根據不同的角度來對莫言小說中方言詞語進行了分類,并且只粗疏地收集到了六類。所以,在收集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跨類的詞語,而對于這些詞語的出現,一般情況下,我們是按照不同種類來進行順序排列,并且將之歸納到相應的類別中。與此同時,在類與類之間存在較大區別的,并不是絕對的。原因在于,方言詞語出現的頻率較大,并且在行文中出現的情況也有所不同,并不是每次都是相同的。這都是根據語境情況而定的,在一些情況下,語境能夠在力度上給出足夠的支持,但是在另外的情況下,則會顯得軟弱無力。
2.方言詞語審美效果
(1)受驚的鵪鶉從馬蹄下飛過,我還看到,黑色泥土從馬蹄上的距毛甩了出去,我還看到,接骨草被馬蹄踏斷、婆婆丁、老鴉芋頭、野茄子與苦菜花……(《玫瑰玫瑰香氣撲鼻》)
“接骨草”“老鴉芋頭”“婆婆丁”“野茄子”“苦菜花”,這些詞語地域性很強,而且只存在于方言中,無法用普通話表達,如果用普通話表達的話,那么表達效果就不會那么出色,就顯得相對地生疏,通過方言表達,可以達到只能意會的效果。
(2)羅漢大爺逼他起來干活,他乜斜著眼說:“你算老幾?老子是真正掌柜的,我是女掌柜肚子里的孩子的爹。”(《紅高粱》)
“乜斜”,是指斜眼睛看,這個詞語使用將余占鰲不服氣的心理與高傲神態表現的淋漓盡致。
(3)那天晚上,余占鰲多疃了幾碗酒,不覺醉意已上七分。(《紅高粱》)
“疃”,意味無節制的暴飲暴食。用在此處,一個鐵骨錚錚的東北漢子就展現在我們面前,一個精忠報國、殺人越貨,“最好漢英雄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充滿野性的自由精靈。
二、莫言小說的諺語特色
諺語是一種具有極強的說服力,能給人以啟示和教育的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它把事物的深刻道理形象地表達出來,是群眾社會經驗和集體智慧的濃縮和升華。而諺語在語言上有其明快、機智、含蓄等獨到的特點,在莫言的小說中,應用了很多這樣的諺語,這些諺語給文學作品增添了不少藝術表達效果。如果通過功能方面對莫言小說進行劃分的話,這些小說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類,如下所示:
1.思辨功能
自古以來,世界萬物都在競爭。生理需求是人們在物我的競爭獲得的收獲,人如果想在自然界生存就需要在實際的人際關系上面,讓自己立在不敗的局面,就必須要能夠有清晰的頭腦,明白智理、分辨出是非黑白、洞察世間萬象。思辨能在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作出協調作用,更能夠使得人們在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上更積極,因而在競爭中成為適應者。
強調思辨的諺語在莫言小說中也是時常出現,例如:
(1)水滿則流,月滿則云,人歡沒好事,狗歡搶屎吃。(《檀香刑》)
(2)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豐乳肥臀·補五》)
這些列舉事理諺語,通俗表現了一些世界觀,體現了萬物生生相克、物極必反的人生哲理,而且更加明白清楚,體現了那個時代的人生觀。
2.教育功能
諺語這一獨特的語言類別是民眾智慧的集成體,是具有風土民性的常用語言。對于社會上的一些公道的討論,它言簡意賅,喻說諷勸、雅俗適宜,所以才能夠經久不衰,流傳深遠,從而不斷地取得發展,給后來的人啟迪教育。諺語在教育的這個功能上,不可忽視的作用就是提高民族的精神素質,穩定社會秩序,有助于構建良好社會關系。諺語所體現出來的精神,有著加強自我的修養、完善人格,對做人處事上等有巨大的作用,如:
(1)轟轟烈烈活三天勝過窩窩囊囊活千年。(《檀香刑》)
(2)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臉。(《檀香刑》)
諺語雖然是鄉村野語,似乎不登大雅之堂,但它獨特的魅力對作家們有著獨特的吸引力,正如《檀香刑》里的“俗言道:鳥為知音而鳴,士為知已者死,咱家為了報答袁大人的知遇之恩,重新撿起了那把放下的屠刀。正是:大清早手熱像個棒火炭,就知道咱肩又有重擔落下。”這里面所引用的幾句諺語,將趙甲作為劊子手的這種哲學以及人生的價值觀,逼真、完美地臨摹出來。
諺語的文學功能,還表現在修辭方面的作用上,柯爾克孜族的諺語中有一句:“美麗的草原離不開牛和羊,美麗的語言離不開諺語。”這就充分說明了諺語是語用美神頭上的一頂王冠、花環。諺語的修辭作用的表現,主要體現在它對語言的運用、調整、修飾的這個方面,比如《豐乳肥臀》中“窮到要飯不再窮,虱子多了不癢癢。”八姐在投河之前,還在想著如何維護好家庭的名聲,而文中另外幾個女孩已經將家庭的名聲鬧的夠戧。所以,無論是經典性質,還是說話上面的精準性,或者是在修辭上的藝術性,諺語都會對語言的說服力起著進一步的加深作用。
三、莫言小說語言民間特色形成的原因
1.作家的經歷
莫言,原名是管謨業,出生在1956年的春天,降生于山東省高密縣,大欄鄉三份子村。他剛出生的時候是落在一堆干燥的沙土上面,因為那里的人所信奉的是“萬物土中生”,所以孩子一出生的時候,就會被放在從大街上面所掃來的肥沃塵土中,希望他能夠像種子一樣,落在沃土中,有著美好的前途。莫言針對這一點,也說過:“這可能是因為我一直都是很土氣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我成為了一個‘鄉土’作家,而沒有成為一個城市作家的原因。”莫言上小學時成績一直非常好,但是5年級時“”開始了,從此他開始了他的農民生涯。1979年秋天,莫言從渤海灣調到了狼牙山下,在一個訓練大隊當政治教員。1980年,開始了文學創作。1981年5月,“蓮池”發表了莫言的短篇小說《售棉大道》,1983年,又發表了《民間音樂》。1985年,莫言寫出了成名作品《透明的紅蘿卜》。這些小說也都折射著莫言的某些生活經歷。
2.作家的苦難意識
莫言在創作過程中總是在他深刻思念與熟悉的鄉村上投入更多精力,將他成長的家鄉——高密東北鄉的人民艱難生存的形態在讀者面前呈現出來。在農村中,耕種與收獲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莫言通過對耕種、收獲的艱難與人禍天災的描寫,表達對農民的憐憫。莫言的苦難意識形成于沉重的民族災難。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民族文化輝煌燦爛,但同時中華民族災難深重,有著沉重的民族苦難與屈辱。深重的歷史苦難不僅可以塑造一個民族還可以毀滅一個民族。面對苦難,我們不是自甘屈服、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勇于抗爭、百折不撓。在他的作品中可以體現出中華民族強大的生命力,而這點也是民族在經歷五千年的苦難之后仍然可以傲立于東方世界的原因所在。苦難意識與面對苦難體現出的堅韌不拔,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中最核心的品質。而莫言是華夏兒女中的一員,自然也有這種品質。
在小說中,莫言最關注的主題還是:生存的苦難和不公平。他對饑餓的大幅度描寫,對渴望的不同表達,都體現在這一點上,要把這種不公平與苦難表達出來。也就是說,莫言真正找到一條走向故鄉大門的途徑,是在他對苦難和不公平的正視之后,所以,他才有了屬于自己的獨到的語言。
莫言小說的語言可謂是“雜語共生”,從方言到普通話,從最高雅的文言詞語到最粗鄙的粗俗罵詈語,從門類眾多的專業詞語到標新立異的自造詞語,莫言小說的語言像個巨大的熔爐,精華與糟粕俱在,美雅與丑俗并存。
參考文獻:
[1]王金城.理性處方:莫言小說的文化心理診脈[J].北方論叢,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