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shū)既從中國(guó)藝術(shù)的歷史演變中呈出了不同時(shí)期的藝術(shù)風(fēng)貌:遠(yuǎn)古嬗變,秦漢氣魄,六朝風(fēng)韻,唐代氣象,宋人心態(tài),元明清趣味,又從藝術(shù)的歷史展開(kāi)中,對(duì)各門藝術(shù)的中國(guó)特色進(jìn)行了深入的介紹:服飾、彩陶、青銅、建筑、繪畫、書(shū)法、詩(shī)文、小說(shuō)、戲曲。
作者的一個(gè)觀點(diǎn),是發(fā)現(xiàn)莊子的道與現(xiàn)代、近代西方思想家所討論的美與藝術(shù)的情況頗多近似或相同,從而認(rèn)定莊子的道正是中國(guó)的藝術(shù)精神。這對(duì)研究中國(guó)藝術(shù)精神具有開(kāi)創(chuàng)性的作用。
◎文化視野下的妙筆勾勒,上百幅關(guān)于中國(guó)藝術(shù)、西方藝術(shù)的精美插圖;
◎作者耗費(fèi)三十年心血,五易其稿,言簡(jiǎn)意賅,通俗易懂;
◎著名學(xué)者傅國(guó)涌老師作序推薦;
吳式南,溫州人,溫州大學(xué)文學(xué)評(píng)論教授。教授文學(xué)評(píng)論和寫作,研究中國(guó)藝術(shù)。
及時(shí)章 “寫生•寫意•寫千古”
中國(guó)的文化和藝術(shù),從總體上看,比西洋的文化和藝術(shù),要高出一個(gè)層次。這主要表現(xiàn)于以下兩點(diǎn):
一、 非“物文”、非“神文”,而是“人文”
在人和外界的關(guān)系上,中國(guó)的文化藝術(shù)遵循“天人合一”這一偉大的哲學(xué)精神,主張
從人、社會(huì)、自然的互補(bǔ)與和諧中,立足于無(wú)窮無(wú)息的廣大時(shí)空中,尋求瞬間與永恒、有限與普遍的契合。這使中國(guó)的文化藝術(shù)充滿了真正的人文精神(與古希臘文化的所謂“物文”精神和古印度文化的所謂“神文”精神不同)。在它的那些不朽的杰作中,總是洋溢著一種圓渾、蒼茫、照耀千古的光輝。而在西方的文化藝術(shù)中,往往強(qiáng)調(diào)人為中心,對(duì)自然采取分解和征服的態(tài)度,強(qiáng)調(diào)人跟自然、社會(huì)的對(duì)立和沖突。相比之下,中國(guó)的文化藝術(shù)是軟性的,西方的文化藝術(shù)則是硬性的。
從藝術(shù)的產(chǎn)生和根本功能是在于對(duì)人的生命和精神的滋潤(rùn)和調(diào)養(yǎng)這一根本點(diǎn)來(lái)說(shuō),軟性的藝術(shù)無(wú)疑是更為適合人的生存和需求的。中國(guó)文化藝術(shù)所依賴的哲學(xué)根基:儒、道(還有禪)互補(bǔ)精神從總體上看,與西方的基督、亞里士多德和尼采哲學(xué)等也迥然不同。
在中國(guó)的藝術(shù)家中,比如齊白石,出身農(nóng)村,習(xí)木工,熟諳傳統(tǒng)藝術(shù),又開(kāi)中國(guó)文人畫的新局面,對(duì)近現(xiàn)代的中國(guó)藝術(shù)影響極大,可謂是球型的人文藝術(shù)天才。躍居于世界文化名人之列。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無(wú)論其精神意態(tài)或技藝手法,都是中國(guó)文化的典型代表,又洋溢著極為強(qiáng)烈的個(gè)人創(chuàng)造色彩。他的花卉草蟲(chóng)之作已在全球不脛而走。學(xué)他的人很多,但總是露出破綻。總不及他!因?yàn)辇R的風(fēng)韻是任何人也學(xué)不會(huì)的。(齊自己說(shuō)過(guò):“學(xué)我者生,似我者死!”他的那些學(xué)習(xí)者頂多只是筆墨色彩和構(gòu)圖上的某些“似”罷了。)
試看下面這兩幅寫老鼠的小品,可把這個(gè)人類一向?qū)χ粦押靡獾男【`寫的那樣有趣,那樣生動(dòng),可愛(ài)極了,表達(dá)了畫家對(duì)生命的喜悅之氣,對(duì)生活的熱忱之情,對(duì)生靈的博愛(ài)之懷,體現(xiàn)了中國(guó)人的人生精神:中庸,和平,天人合一,與萬(wàn)物共諧。這是不同于西方民主和人道精神的一種更為寬泛的人文(含“物文”、“神文”)精神。
即使同是宗教意識(shí),都著眼于人類的苦難。西方的基督從人的“原罪”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上帝的救贖,地獄的可怖和天堂的安慰。中國(guó)的禪卻著重修煉和徹悟,以靜穆和溫馨把人生自我升華到極樂(lè)世界。正如熊慶來(lái)(數(shù)學(xué)家,對(duì)文化藝術(shù)也頗有造詣)曾說(shuō)過(guò)的那樣:“西方教堂和中國(guó)佛寺氣氛不同。前者是懸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血肉淋漓,寓悲劇色彩。后者則莊嚴(yán)肅穆,一派和平。”
我不信佛,卻愛(ài)佛。我參觀過(guò)新疆吐魯番石窟,敦煌石窟,大足石刻,各地佛寺廟宇,菩薩是多么莊嚴(yán)慈祥。王朝聞稱大足一尊菩薩為東方維納斯,可謂美矣!古代工匠,鬼斧神工,把世上美人之優(yōu)點(diǎn),全集中于菩薩身上,美輪美奐。我有一佛頭,眉、眼、鼻、口、兩腮、下巴、至三條頸飾,豐滿勻稱,百看不厭。除兩耳垂肩,有點(diǎn)過(guò)分夸張外,均是無(wú)可挑剔的。
中國(guó)人并不諱言人生的苦難,但沒(méi)有把人生和世界看得很陰暗;中國(guó)人并非無(wú)視世界的病態(tài),但卻不搞“惡之花”之類,而是把“憂郁扎成花朵”,把苦難通過(guò)堅(jiān)韌的錘煉而上升為超脫、散逸的藝術(shù)。齊白石就是一個(gè)活榜樣。
齊氏活到90多歲高齡,無(wú)論與只活了30多歲而命運(yùn)困頓的梵高相比,還是與跟他同樣高齡、另一個(gè)世界大師畢加索相比,他們的人生態(tài)度和遭遇都不相同。齊白石是中國(guó)文化中人,活出了藝術(shù)與生命的和諧。東西方藝術(shù)家生命與藝術(shù)精神的互涵,于此可見(jiàn)一斑。
懂得齊白石者,也就懂得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精華了。
再如,同是表現(xiàn)人類的生存苦難主題,東西方的三個(gè)神話故事卻見(jiàn)出其不同。
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被吊在高加索的懸崖上,白天讓鷲鷹啄其心臟,夜里則愈合,白天又再啄……;加繆的西西弗神話,主人翁被罰推巨石于懸崖之上,用大力推上崖頂又滾滾而下,復(fù)繼續(xù)推又繼續(xù)滾落……,而中國(guó)類似神話中的吳剛月中砍桂:砍而復(fù)生,勞作不息……
同是悲劇意識(shí),但中西顯現(xiàn)的調(diào)子,彼此的氛圍和氣象就不一樣:前者沉重,后者迂緩;前者黑暗,后者光亮。
還可舉一例。
一次,西北歌王王洛賓在紐約舉行民歌演唱會(huì),有記者問(wèn)王,何以能從北平到新疆而一住五十五年?王答:因?yàn)槟抢镉幸魳?lè),還有“一雙看到天堂的黑眼睛”。王洛賓的如此人生態(tài)度,簡(jiǎn)直是藝術(shù)至上、唯美是求了。王氏一生坎坷,當(dāng)時(shí)已年近八十高齡,但對(duì)藝術(shù)依然充滿赤子之心,孜孜不倦,說(shuō)自己好作品還未寫出,還在探討之中。
中國(guó)的書(shū)畫藝術(shù)家,大都心態(tài)和諧,淡泊名利,孜孜鉆藝,年高思健,美意延年。中國(guó)藝術(shù)家的這種健旺的精神生態(tài),是得力于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健旺的哲學(xué)生態(tài),是與中國(guó)歷史上深厚而綿長(zhǎng)的人文精神同構(gòu)、同態(tài)和一脈相承的。正如中國(guó)的文人總是把“人品”放置于“文品”之上。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事實(shí)上,藝術(shù)家的人格、氣象決定了其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品格和氣象。這兩者是同步并進(jìn)而不是截然分裂的。
下面這三顆齊白石中晚年自刻的印章,就是很典型的見(jiàn)證。
二、 非“反抽象”、非“全抽象”,而是“半抽象”
在藝術(shù)的形態(tài)和手段上,中國(guó)文化藝術(shù)不同于自然主義(反抽象),也不同于形式主(全抽象);既非純正的寫實(shí)主義,也非純粹的浪漫主義,而是以簡(jiǎn)筆、寫意、傳神、講究氣韻生動(dòng)為特征的情境創(chuàng)造(“寫生•寫意•寫千古”)。 李可染有言:不懂抽象的藝術(shù)家算不上大藝術(shù)家。藝術(shù)是高度的抽象。藝術(shù)總是創(chuàng)造形象的,但與純粹的生活的摹寫(具象)不同,也與純粹主觀的臆想(抽象)不同,中國(guó)藝術(shù)家在形象制作的形態(tài)和技藝上,既非反抽象的“具象”,也非全抽象的“抽象”,而是介乎摹寫和臆想之間的“意象”(或“靈象”)創(chuàng)造。它是“半抽象”的。
西方藝術(shù)講究微觀、地描摹對(duì)象的客觀真實(shí),追求對(duì)象和現(xiàn)實(shí)的所謂本質(zhì)和內(nèi)在的規(guī)律性。它所達(dá)到的科學(xué)性的度、心理分析的細(xì)致度、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的曲折度、性格挖掘的深刻度,是輝煌而驚人的。但缺乏中國(guó)文化藝術(shù)家那種創(chuàng)造中的揮灑大度、匠心獨(dú)運(yùn),敢于對(duì)生活和自然高屋建瓴、重新組合、大膽切割、提煉升華,從非現(xiàn)實(shí)的假定性中達(dá)到千古的真實(shí)。
再如西方藝術(shù)中對(duì)女性人體美的描繪,人物性格塑造中的多彩的畫廊,固然贏得了千古的光華,叫人贊嘆不絕。但中國(guó)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所追求和到達(dá)的人物的風(fēng)韻、神味、氣骨,卻是別一種境界。
從這一意義上說(shuō),半抽象藝術(shù)與具象藝術(shù)在境界上截然不同。但西方藝術(shù)從20世紀(jì)后又走入另一個(gè)極端,出現(xiàn)了抽象派,進(jìn)行全抽象,所謂幾何抽象(冷抽象)和感情抽象(熱抽象)叫人看不懂,無(wú)論是理智上或直覺(jué)上,簡(jiǎn)直是走入迷宮。這就不可取了。因?yàn)檫@種抽象派的作品,除了藝術(shù)家本人(也只是靠自己的聲明而已,別人還是無(wú)法領(lǐng)會(huì)和共鳴)或幾個(gè)同道之外,別人就無(wú)法問(wèn)津了。中國(guó)的藝術(shù)可從來(lái)沒(méi)有這種全抽象的東西。是否可以說(shuō),幾千年來(lái),中國(guó)的文化藝術(shù)一直是常態(tài)的,人文精神的,不像西方那么的走極端。
以下,且將臺(tái)灣“抽象派繪畫大師”陳正雄的五幅作品及畫家本人的自白、介紹者的解釋,再加我的評(píng)說(shuō)分列于下,讓大家看看。
畫家陳正雄自白——
“看不清是什么,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著色,這純粹是作畫時(shí)自我情感的盡情流露,非這樣不能淋漓地表達(dá)內(nèi)心深處潛藏的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介紹者的解釋——
“四十年來(lái),陳(正雄)先生的繪畫先由具象進(jìn)入半抽象,再由半抽象到抽象。在這種自然的演變和發(fā)展中,他漸漸領(lǐng)悟:只有抽象藝術(shù)是能宣泄內(nèi)在世界情感和潛意識(shí)需求的繪畫語(yǔ)言,這比做外界形象的奴隸來(lái)得更真實(shí),更能發(fā)現(xiàn)自己神秘的內(nèi)心和生命之源。
“抽象繪畫放棄了客觀形象的模仿,不依賴任何外借的東西,不純粹描繪具體之物,憑借的只有它們的本質(zhì)和精神,以抽象來(lái)注釋具體的物或某種感覺(jué),而用于創(chuàng)作形體的天生自然色彩,通常源自超越個(gè)人喜怒好惡的內(nèi)在世界,是超越自然重現(xiàn)的藝術(shù)。
“陳先生抽象繪畫,一向不打草稿,他把內(nèi)在的沖動(dòng)和生命直接訴諸畫布,此時(shí)畫布上的行動(dòng)軌跡又刺激他下一步的連鎖反應(yīng),如此隨著作畫行動(dòng)的發(fā)展,在揮筆滴彩之中,其內(nèi)在情感和生命就鮮活于畫面上,把不可見(jiàn)的內(nèi)在世界化為可見(jiàn)的視覺(jué)存在,讓觀賞者去體會(huì)神秘又真實(shí)的形象。”(李丹妮:《臺(tái)灣抽象派大師陳正雄》)
筆者評(píng)說(shuō)——
這些自白和解釋本身,也是夠抽象和虛玄的了。試問(wèn),面對(duì)大片色彩的斑斕和揮灑,任你怎么看和怎么想,都無(wú)法找到與其各自標(biāo)題相對(duì)應(yīng)的內(nèi)容,畫家的“內(nèi)心情感”和“生命源”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一片神秘和朦朧莫測(cè),如果找不到與對(duì)象心靈的共鳴和通達(dá)之路,這樣的“個(gè)體”是不是太孤奇了呢?與其說(shuō)這是繪畫創(chuàng)作,還不如說(shuō)是一塊塊花布的任意剪裁的零頭料。我們可以理解處在所謂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藝術(shù)家的精神困頓,但卻無(wú)法理解他們的繪畫自身。這無(wú)論如何也是一種表現(xiàn)的悲哀。
與此相佐證,我還可引一段資料,看看抽象繪畫在一些歐洲國(guó)家已到了何等離奇的地步——
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上有一篇報(bào)道說(shuō):“一次,我在一位瑞士畫家家里作客,他的房間里掛著一幅自己畫的抽象畫,畫面很簡(jiǎn)單,就是兩個(gè)凹弧形“⌒⌒”。我說(shuō)‘你的畫很高深,我難以理解。’他說(shuō):‘我一般是不跟人解釋我的畫意的。你給我講解了東方的古老藝術(shù),我也應(yīng)該告訴你我的畫意:兩個(gè)弧形表示人死后閉上眼睛,同時(shí)它是兩個(gè)翅膀,象征著靈魂飛向天堂’。”( 李國(guó):《瑞士人喜愛(ài)中國(guó)書(shū)法》)
如果抽象繪畫到了這樣的程度,那就是對(duì)繪畫自身的否定了,這不禁使我想到,列寧早在上世紀(jì)的開(kāi)頭,就那么怒不可遏地斥責(zé)現(xiàn)代派藝術(shù)是頹廢、丑惡和反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了。正像陳正雄的抽象繪畫成了花布剪棄下的凌亂的零頭料,這個(gè)瑞士畫家的抽象繪畫則簡(jiǎn)直就是赤裸裸的數(shù)學(xué)上的符號(hào)了。嗚呼!
縱觀中國(guó)的藝術(shù)傳統(tǒng),可沒(méi)有這種全抽象的東西。前幾年,有人在《美術(shù)》雜志發(fā)表文章,認(rèn)為中國(guó)的水墨畫“只是個(gè)語(yǔ)言范式的概念”,“從精神意識(shí)或從工具材料來(lái)界定中國(guó)水墨畫都不合適”,并認(rèn)為“抽象將是水墨畫的一個(gè)高峰”,因而提出“純粹抽象是中國(guó)水墨畫的合理發(fā)展”這個(gè)命題。(《純粹抽象是中國(guó)水墨畫的合理發(fā)展》)這是似是而非的言論,對(duì)中國(guó)畫的理解是膚淺的而浮躁的。顯然,這是不符合中國(guó)畫的根本精神的。中國(guó)水墨畫除了“語(yǔ)言物質(zhì)”,還不能忽視它的審美意識(shí),因?yàn)樗途€,作為傳“神”達(dá)“韻”,創(chuàng)造“意境”的手段,正是實(shí)現(xiàn)“物”“我”高度綜合這個(gè)中國(guó)古典藝術(shù)精神的不二途徑,深深滲透著東方民族的審美真諦,是中華民族對(duì)世界文明的獨(dú)特而燦爛的貢獻(xiàn)。怎一個(gè)“純粹抽象”了得!(以下還要詳論)
第二章 還自然以獨(dú)立的生命
中國(guó)藝術(shù)與西方藝術(shù)在對(duì)待自然的態(tài)度和方法上都有不同,這可以從同是花卉的描繪上作些比較。
中國(guó)繪畫藝術(shù)中,花卉和山水的題材占了極大的比重,取得了較高的成就,這在世界藝術(shù)史上是很獨(dú)特的。這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大概與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中特看重自然,強(qiáng)調(diào)人和自然、社會(huì)的和諧這一人文哲學(xué)精神有關(guān)。
被稱為西方“畫圣”的荷蘭大畫家梵高在西洋美術(sh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認(rèn)為是稀少的珍寶,曾以三千萬(wàn)美元的巨價(jià)創(chuàng)世界繪畫收購(gòu)十大記錄的第二位,而且梵高生前曾先后畫了七幅“向日葵”,據(jù)說(shuō)一幅比一幅輝煌。這幅《向日葵》(1888年)通體呈黃色,像一團(tuán)狂熱的火焰,反映了畫家燃燒的心靈。它不只色彩熱烈,就是花瓣的線條也呈燙灼般的顫抖,的確有一股跳盈的猛烈的心靈之火在燒炙著每一個(gè)觀畫者的感官。
梵高開(kāi)辟了以畫家的主觀心靈為源泉的作畫風(fēng)格,這比前期的印象派畫家(如附圖莫奈的《向日葵》)是一個(gè)進(jìn)步。但單以主觀心靈的色彩來(lái)觀照和變化自然對(duì)象,總感到個(gè)體性太強(qiáng),畫家的主觀壓倒了、排擠了自然的客觀,奇特雖奇特,但缺乏和諧和耐人尋味。以梵高來(lái)說(shuō),他的帶有病態(tài)色彩的精神,更會(huì)給他的表現(xiàn)對(duì)象帶來(lái)一定的損害,投合了現(xiàn)代西方富有階層尋求怪異刺激的欣賞趣味。
再看看中國(guó)畫家的幾幅花卉作品:齊白石的《牽牛花》、《雞冠公雞》,張大千的《荷花圖》,虛谷的《松鼠戲竹圖》、金農(nóng)(清)的《梅花圖》冊(cè)之一。每幅都是形神飛動(dòng),氣韻盎然,且筆情墨意、色調(diào)、疏密,全映入眼簾,仿佛是一首首有形的詩(shī),一曲曲無(wú)聲的樂(lè),和諧溫馨,使我們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機(jī),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氣,一片昂揚(yáng)的生命節(jié)律流溢心田,舒心無(wú)比。中國(guó)畫家的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是立足于人與自然的契合,把一種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滲透于特定的對(duì)象之中,是一種意象的創(chuàng)造形態(tài),而不是再現(xiàn)的形象形態(tài),是升華了對(duì)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畫家的主觀來(lái)扭曲變形。在創(chuàng)作的精神上,中國(guó)畫家總是執(zhí)著地追求一種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畫家那樣片面張揚(yáng)獨(dú)立于自然和社會(huì)、以個(gè)體為中心的個(gè)人主觀精神。
由于中西畫家這種創(chuàng)作態(tài)度和方法上的差異,中國(guó)藝術(shù)從本質(zhì)上看,不是模仿的藝術(shù),不是印象的藝術(shù),也不是抽象的藝術(shù),而是充滿了主客體的辯證統(tǒng)一精神,以意象創(chuàng)造而實(shí)現(xiàn)人、社會(huì)、宇宙和諧的中和的藝術(shù),是簡(jiǎn)潔、傳神、含蓄、雋永的藝術(shù),是達(dá)到了“氣”(藝術(shù)家的主觀心靈之氣,生命運(yùn)行之氣,宇宙間自然萬(wàn)物之氣)、“韻”(主觀、客觀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發(fā)射出來(lái)的風(fēng)華、光輝和耐人尋味)生動(dòng)的藝術(shù)。應(yīng)該說(shuō),中國(guó)的花鳥(niǎo)、山水畫中所表現(xiàn)出的這種整體性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牧歌式的親切精神,是十分有意義和價(jià)值的。是否可以說(shuō),中國(guó)人尊重自然,重視人的生存態(tài)的根本態(tài)度(所謂“詩(shī)意地棲居”),是對(duì)于社會(huì)改革的另一種熱情的表現(xiàn),至少它的重要性是決不亞于對(duì)社會(huì)進(jìn)行政治的和經(jīng)濟(jì)的改革的緊迫吧。
梵高是一個(gè)痛苦的悲劇的夭折的天才。他短短的繪畫生涯像一道慧光閃過(guò)天空,給后人強(qiáng)烈的震撼。他當(dāng)過(guò)經(jīng)紀(jì)人,當(dāng)過(guò)傳教士,但都不合適他的個(gè)性,然后就專門從事繪畫。他對(duì)鄉(xiāng)居生活和下層貧苦人民有感情。他的好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都是以鄉(xiāng)間和下層社會(huì)群眾的生活為題材的。但是,他的心卻是受了劇烈的創(chuàng)傷,他的藝術(shù)是與他痛苦而燃燒的生命、孤獨(dú)而躁動(dòng)的性格以及一種病態(tài)的熱情聯(lián)絡(luò)在一起的。從這樣的觀點(diǎn)看,梵高的藝術(shù)無(wú)疑也是天才的、病態(tài)的、不安的藝術(shù)。
齊白石,是一個(gè)健康、樂(lè)觀、高壽的天才。他出身于木工,來(lái)自民間,一生的藝術(shù)與底層農(nóng)民的生活、胸襟聯(lián)絡(luò)在一起,表現(xiàn)了勞動(dòng)者的質(zhì)樸、清新、矯健,充滿了生命的喜悅,蓬勃的情趣,向上的進(jìn)取,潑辣而爽朗的胸懷。他的藝術(shù)既有中國(guó)傳統(tǒng)文人畫的優(yōu)美和淡雅,又有民間藝術(shù)特有的濃麗和大方、剛健和樂(lè)觀,是有永恒生命的藝術(shù)。
第三章 “站在地球邊上放號(hào)”
中國(guó)真不愧是一個(gè)“詩(shī)的國(guó)度”。它的文學(xué)藝術(shù)精神,本質(zhì)上是詩(shī)性的。西洋文藝追求的是一個(gè)“真”字,中國(guó)文藝追求的是一個(gè)“似”字(“藝術(shù)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真”符合科學(xué)要求,“似”表達(dá)詩(shī)意精神。“真”的文藝,其中心是寫“典型”,即廣泛的代表性,突出的特征性,尖銳的沖突性,有較高的認(rèn)識(shí)價(jià)值等。而“似”的文藝,其中心是創(chuàng)造“意境”,即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家的情態(tài),傳達(dá)對(duì)象的風(fēng)神,體現(xiàn)廣闊的空間生命,有雋永的韻味等等。西方的藝術(shù)是“地上”的藝術(shù),它的視覺(jué)總是放置在一個(gè)塵世的某處,而中國(guó)的藝術(shù)則是“空中”的藝術(shù),它的視角是飄在空中的,仿佛是“站在地球上放號(hào)”(郭沫若語(yǔ))或是“站在城市建筑物的較高點(diǎn)來(lái)鳥(niǎo)瞰”(林語(yǔ)堂語(yǔ))。
試以表現(xiàn)田間勞動(dòng)的創(chuàng)作來(lái)看——
插秧,是極普通的農(nóng)夫勞作。我國(guó)臺(tái)灣一詩(shī)人的《插秧》,是這樣寫的:
插秧
水田是鏡子——
照映著藍(lán)天
照映著白云
照映著青山
照映著綠樹(shù)
農(nóng)夫在插秧——
插在綠樹(shù)上
插在青山上
插在白云上
插在藍(lán)天上
在這個(gè)東方詩(shī)人的視野中,它是一個(gè)何等巨大而新奇的鏡框(畫面空間),這就是達(dá)到了意境的創(chuàng)造。在這里,平凡的勞作,美麗的詩(shī)情,遼闊的天地,壯偉的農(nóng)夫在播種收獲、播種生命,美化宇宙,真是頂天立地。他們的身姿簡(jiǎn)直比古希臘人的雕像還要壯美。
如果把它與法國(guó)畫家米勒的同是寫農(nóng)人勞作的名畫《拾穗》(或《田間休息》相比較,我們覺(jué)得后者的視角和鏡框就低了,狹了,頂多只是傳達(dá)了農(nóng)人生活的艱辛、質(zhì)樸和心地善良罷了。它的空間和情思都是狹窄而單調(diào)的。
中國(guó)的詩(shī)可入畫。詩(shī)人總是身處塵世又跳出塵世,從廣闊的時(shí)間和空間的把握中,注重表達(dá)詩(shī)人和對(duì)象的意態(tài)、韻致,骨子里是入世,肯定和謳歌人生。而西方的畫則就空間寫空間,太注重寫實(shí),太入世,總感到人生是沉甸甸的,骨子里好像是活“膩”了。
“似”的藝術(shù)不同于“真”,還可以從中國(guó)人物畫與寫真照片的比較中看出其價(jià)值的相異——
魯迅是一個(gè)具有創(chuàng)造個(gè)性和生理個(gè)性的偉大作家。他的一幅肖像照片,是其個(gè)性的典型再現(xiàn),是具有特色和大家熟悉的。應(yīng)該說(shuō)是“真”的成功之作。但“似”的藝術(shù)卻并不滿足于如此的觀照,它要把藝術(shù)家們各自的靈性和對(duì)魯迅精神、風(fēng)韻的各自捕捉,通過(guò)各自特殊的工具加以創(chuàng)造性的顯現(xiàn)。
看曹白作的《魯迅木刻像》,也許不如照片的真,但畫家著意通過(guò)人物的眼睛傳達(dá)魯迅的冷峻、尖利而又具悲天憫人的胸懷,其氣度就遠(yuǎn)非照片所能擁有了。而背景的設(shè)置——代表作《阿Q正傳》、《吶喊》、《準(zhǔn)風(fēng)月談》,投槍似的巨筆,還有五角星、兩條吠犬、一個(gè)后仰的軍閥,再配上黑色的基調(diào),稀薄的天空,更高度地概括了這位偉大的戰(zhàn)斗作家一生的業(yè)績(jī)。方寸之幅所涵包的認(rèn)識(shí)意義和美學(xué)價(jià)值是十分巨大的。在這幅木刻里,并沒(méi)有西洋畫的那種焦點(diǎn)和透視,而是將其時(shí)空,點(diǎn)面,瞬間和永恒互相結(jié)合,是藝術(shù)家以其站在宇宙和生命高度的視野,進(jìn)行全鳥(niǎo)瞰式的宏觀把握的產(chǎn)物。
再如拙作的詩(shī)幅水墨簡(jiǎn)筆畫,粗略的線條,淡淡的墨色,夸張變形的動(dòng)作,有意簡(jiǎn)省的五官,雖然稚拙,但能傳達(dá)意志,從另外的側(cè)面,把魯迅的風(fēng)神傳達(dá)出來(lái)了。從這三幅小品中,還可領(lǐng)略中國(guó)毛筆工具的獨(dú)特性能和表現(xiàn)力度。
中國(guó)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這種獨(dú)特視角,所謂“在地球邊上放號(hào)”或“在城市建筑物的較高點(diǎn)來(lái)鳥(niǎo)瞰”,也可稱之為“宇宙視角”。它的可貴之處是既立足于生活原點(diǎn)又不拘泥于某個(gè)特定之點(diǎn),而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陸機(jī)),東西南北,春夏秋冬,正反側(cè)面,都可同時(shí)展現(xiàn),從而把一個(gè)特定對(duì)象表現(xiàn)得豐富多元,淋漓盡致。西方的一些人物畫名作,如烏桐的伏爾泰雕像,羅丹的穿睡衣的巴爾扎克(雕塑),盡管人物特定的個(gè)性、風(fēng)神也可展示的很深刻、鮮明,但總覺(jué)放不開(kāi),創(chuàng)造靈感局限于特定的情節(jié)或瞬間觀照,而中國(guó)畫家的魯迅像,雖只是提供一個(gè)概括性的情境(非情節(jié)),但魯翁的“橫眉冷對(duì)”和“俯首甘為”的多元性格側(cè)面,還有他的冷峻尖刻、悲天憫人、幽默嬉笑等等的心理狀貌,都一一凸顯無(wú)遺。這實(shí)在是中國(guó)藝術(shù)的得天獨(dú)厚之處。
再如我的另一幅水墨簡(jiǎn)筆的“魯迅流淚”,淡淡的水墨,只節(jié)儉地勾勒出魯迅的五官,甚至省去了他面部的輪廓線,也沒(méi)有畫出他的正富個(gè)性的頭發(fā),而獨(dú)出機(jī)杼只在其左頰橫添一顆淚珠,把先生一生的悲與憤與痛,作了創(chuàng)造性的體現(xiàn)。
中國(guó)藝術(shù)構(gòu)造中的這種所謂“散點(diǎn)透視”(與西方的“焦點(diǎn)透視”不同),同樣在中國(guó)的山水畫中,花卉畫中有驚人的表現(xiàn)。
在中國(guó)的山水畫中,你看不出哪里是焦點(diǎn),往往在一幅畫面中,上下左右,內(nèi)外空間,四時(shí)季節(jié)同時(shí)展現(xiàn),比如懸掛于北京人民大會(huì)堂的那幅巨幅山水《江山如此多嬌》(關(guān)山月等作),就同時(shí)描繪了祖國(guó)山河不同的地域景色及四季風(fēng)物,既磅礴壯觀,又嫵媚動(dòng)人。
在中國(guó)畫家的花卉之作中,諸如用朱砂色畫竹,用紅色畫牡丹花而配以潑墨的黑色之葉,又如把瑞雪和蝴蝶這兩件根本不互存的物象,赫然構(gòu)圖在一起。好家伙,這些生活中違反正常規(guī)律和邏輯的東西,卻都成了中國(guó)畫家美學(xué)領(lǐng)地中的瑰寶。
第四章 毛筆與水墨
中國(guó)藝術(shù),特別是中國(guó)繪畫,它的獨(dú)特的魅力是與它所使用的獨(dú)特的工具——毛筆與水墨不可分的。
下面試分析兩幅當(dāng)代人的畫作——
韓羽的《冷月葬詩(shī)魂》(林黛玉)是一幅很典型的中國(guó)水墨寫意人物畫。作為一幅《紅樓夢(mèng)》的插圖,畫家對(duì)原著做了很精辟獨(dú)到的篩選,表現(xiàn)獨(dú)具匠心,有很高的獨(dú)立性和觀賞價(jià)值。
首先,我們看畫家的落題,《紅樓夢(mèng)》中寫林黛玉的情節(jié)很多,詩(shī)詞亦很多,畫家特?fù)炱呤?ldquo;凹晶館聯(lián)詩(shī)悲寂寞”,即中秋夜黛玉和湘云于湖畔的一個(gè)聯(lián)句,但改了一個(gè)字,把原句的“花魂”改為“詩(shī)魂”,入神了。林妹妹固然如花美春,但她本質(zhì)上是詩(shī),豈不是“詩(shī)魂”一個(gè)?“
寫得很實(shí)在,也有先生自己獨(dú)到的見(jiàn)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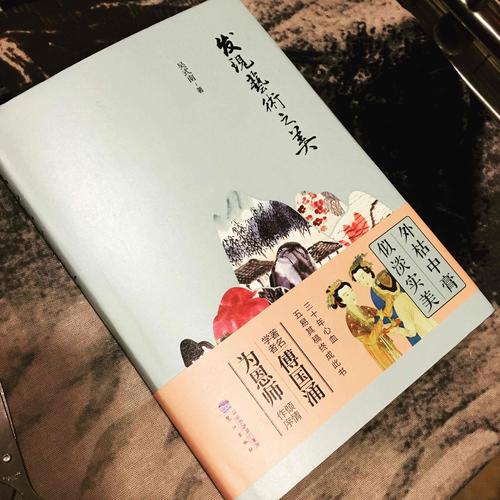 藝術(shù)需要批判。這樣互捧大可不必。里面好多觀點(diǎn)實(shí)在不敢茍同的很。。。作者稱自己的作品為拙作,我覺(jué)得的確很拙。從整本書(shū)看,作者十分欣賞魯迅,我覺(jué)得他完全可以寫本 魯迅作品之我見(jiàn) ,然后配幾幅自己的魯迅畫像,可能還頗有趣味些。
藝術(shù)需要批判。這樣互捧大可不必。里面好多觀點(diǎn)實(shí)在不敢茍同的很。。。作者稱自己的作品為拙作,我覺(jué)得的確很拙。從整本書(shū)看,作者十分欣賞魯迅,我覺(jué)得他完全可以寫本 魯迅作品之我見(jiàn) ,然后配幾幅自己的魯迅畫像,可能還頗有趣味些。
好書(shū)。簡(jiǎn)潔明快!
書(shū)質(zhì)量很好!包裝也好。快遞很快!
很好
自己買了一本,現(xiàn)在又買一本送人
喜歡的題材
不錯(cuò)
好
還沒(méi)看完
值得收存的書(shū)。
正版圖書(shū),內(nèi)容豐富翔實(shí)。
收藏的 大贊
不錯(cuò)不錯(cuò)不錯(cu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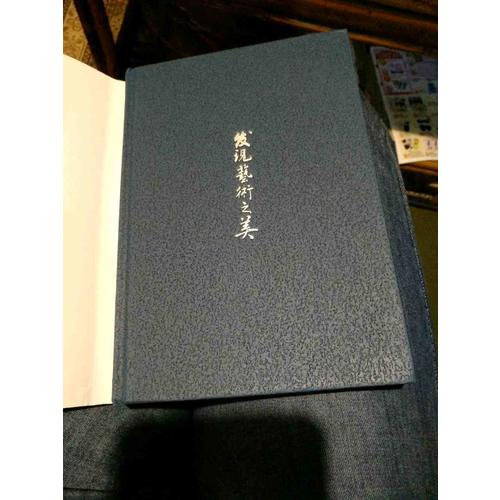 書(shū)籍中等厚度,彩色印刷,硬面精裝,內(nèi)容非常經(jīng)典,值得收藏。特價(jià)淘到寶。
書(shū)籍中等厚度,彩色印刷,硬面精裝,內(nèi)容非常經(jīng)典,值得收藏。特價(jià)淘到寶。
一次非常愉快的購(gòu)書(shū),知識(shí)無(wú)涯,很好。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作者耗費(fèi)三十年心血,五易其稿,言簡(jiǎn)意賅,通俗易懂
真的不錯(cuò)的書(shū),此書(shū)引領(lǐng)走進(jìn)藝術(shù)領(lǐng)域,心曠神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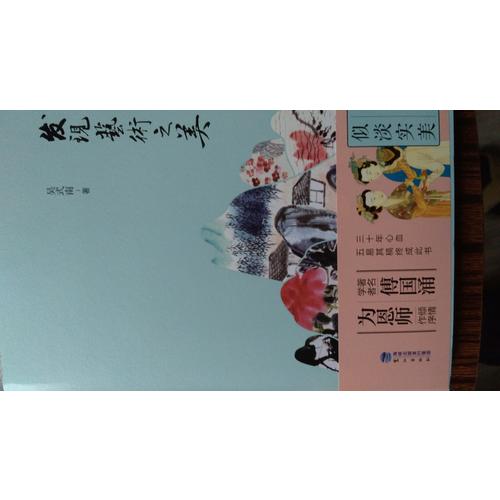 畫家個(gè)人的秉性和生活際遇、社會(huì)環(huán)境的變化等也促生了元代繪畫的生機(jī)多樣性。我需要特別提及一個(gè)文化現(xiàn)象:元代沒(méi)有權(quán)威的文化體系,是造成元代書(shū)畫藝術(shù)多樣性的根本原因。在唐有古文運(yùn)動(dòng)興起,在宋有新儒家體系出現(xiàn),在明有理學(xué)的大興,在清有樸學(xué)的存在,而元代卻什么都沒(méi)有,不僅僅是因?yàn)樗蹋且驗(yàn)槠洳恢匾曃幕ㄔO(shè),文化界遂成一盤散沙。鑒于中國(guó)古代繪畫與文化思想和文藝評(píng)論連系緊密,元代繪畫體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現(xiàn)象也就不奇怪了。這里就體現(xiàn)出繪畫藝術(shù)的一個(gè)重要意義:在正規(guī)渠道無(wú)法繼承和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的時(shí)候,繪畫藝術(shù)將比其他藝術(shù)形式,比如戲曲、雕塑…
畫家個(gè)人的秉性和生活際遇、社會(huì)環(huán)境的變化等也促生了元代繪畫的生機(jī)多樣性。我需要特別提及一個(gè)文化現(xiàn)象:元代沒(méi)有權(quán)威的文化體系,是造成元代書(shū)畫藝術(shù)多樣性的根本原因。在唐有古文運(yùn)動(dòng)興起,在宋有新儒家體系出現(xiàn),在明有理學(xué)的大興,在清有樸學(xué)的存在,而元代卻什么都沒(méi)有,不僅僅是因?yàn)樗蹋且驗(yàn)槠洳恢匾曃幕ㄔO(shè),文化界遂成一盤散沙。鑒于中國(guó)古代繪畫與文化思想和文藝評(píng)論連系緊密,元代繪畫體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現(xiàn)象也就不奇怪了。這里就體現(xiàn)出繪畫藝術(shù)的一個(gè)重要意義:在正規(guī)渠道無(wú)法繼承和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的時(shí)候,繪畫藝術(shù)將比其他藝術(shù)形式,比如戲曲、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