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爭議的藝術評論家——《致命的海灘》作者羅伯特 休斯,以熱愛與憎惡交織、才智與并存的眼光審視16世紀羅馬至20世紀80年代蘇河區的藝術品、藝術家以及藝術界。
羅伯特 休斯打破偶像、絕無虔敬、熱情洋溢、學識淵博,被認為是美國藝術評論家,也是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幾位偉大的藝評家之一。休斯在這本評論集中,對形形色色的藝術家提出了絕不妥協的觀點,如霍爾拜因與霍克尼、約翰 辛格尓 薩金特與弗朗西斯 培根、洛克威爾與畢加索、華托與沃霍爾,等等。
休斯涉筆成趣、新鮮生動、極善表達,以幾達百篇秀的散文喚起并界定了一系列藝術家的世界、作品和本質,并使之能為我們所了解,而且他敢于當頭面對藝術與金錢這樣一個命題。
羅伯特 休斯是這樣一個奇才,他獨具個性的聲音從一片圣詠合唱中浮現出來……足智多謀,幽默機智,很有見地,編年史般地記錄了藝術與金融投機聯姻之后的瘋狂蜜月。休斯對藝術品的物理特征有著一種格外強烈的意識。他的方法博學而優雅,他的想象力細膩而富詩意,他的才智貌似花花公子,卻經過深思熟慮,能摧枯拉朽不說,偶爾還頗慷慨大度。休斯把一個復雜的主題寫得能讓普通讀者讀懂,在當代藝術評論家中,縱有與之匹敵者,也少之又少。本書中的藝術批評猶如思想爆炸,對常態提出挑戰。隨著美國文化無精打采的走向,凡試圖把握這個文化的人,都會對此著迷。
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
1938年生于澳大利亞,2012年8月去世。當代著名藝術評論家、作家、歷史學家,也是電視紀錄片制作人。20世紀70年代起長期住在紐約。自1970年起為《時代周刊》撰寫藝術評論,其著作影響了澳大利亞乃至全世界藝術評論的發展,曾被《紐約時報》譽為世界上最著名的藝術評論家。代表作品有藝術史專著《新的沖擊》(The Shock of The New)、回憶錄《我不知道的那些事情》(Things I Didn’t Know)、澳大利亞流犯流放史《致命的海灘》(The Fatal Shore)等。
歐陽昱(譯者)
湖北黃州人,1955年生。華東師范大學英澳文學碩士、墨爾本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澳洲文學博士,中英文雙語作家、詩人、翻譯家、《原鄉》文學雜志主編。已出版中英文作品71種(含譯著36種)。曾為武漢大學講座教授,南京大學兼職教授,現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思源”學者兼講座教授。譯著有《女太監》(杰梅茵•格里爾著)、《致命的海灘》(羅伯特•休斯著)、《柔軟的城市》(喬納森•拉班著)、《我不知道的那些事情》(羅伯特•休斯著)等。
1989年,普通美國人幾乎把一半的清醒時間都花在看電視上。美國的兩代人——其中包括美國藝術家——現在都是在電視機前長大的:他們的意識中滲透了電視穿梭傳遞的明亮形象;他們注意力的持續時間,都因電視善于擺布操縱的速度而萎縮;他們關于成功的理念,受到電視把名聲變成名人的慣用伎倆的支配;他們焦慮的程度(至少在比較聰明的人中,其中包括藝術家),因電視滲透一切的力量而增強。
這不是一個選擇問題,更不用說是錯誤了。電視的威力已經超出了美術想要或已經達到的任何境地。像這種尼亞加拉大瀑布一樣的視覺垃圾,1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美國電視網絡耗干了世界的意義,使現實顯得枯燥、緩慢,能避免就可以避免。它是我們的“浮世”。它傾向于把想象流產,不給孩子留下任何可以想象的東西:所有的英雄和惡棍都在那兒,聲音沙啞,毫不含蓄,而且都是事先裁定的——這是一個充滿刻板印象的世界,大到不讓想象力得到發展或變化。難怪它已預先讓美國藝術家傾向于類似的刻板印象,雖然愚蠢,卻讓你欲罷不能,而繪畫和雕塑即使在進行宣傳或多愁善感的最糟時刻,也不會這樣。
從使用柯達相機的埃德加 德加(Edgar Degas),到使用銀幕的羅伯特 勞森伯格,從把新聞照片進行剪切拼貼的漢娜 赫希(Hanne Hoch),到利用電視和廣告的激浪派(the Fluxus group),15現代藝術家長期以來,都迷戀大眾傳媒。勞森伯格也好,利希滕斯坦也好,都很會在把玩這種迷戀的同時,又在美術傳統之內保持平衡。沃霍爾骨子里是個商業藝術家,他走(起初走得小心翼翼)到了美術傳統之外,以侍從的姿態擁抱了電視無涉價值的幽靈。美國藝術家的下一代人,也就是安迪的孩子那一代,成批地追隨著他。他們不可能想象出一個不為電視陰影所籠罩的美術傳統。于是,關于藝術和媒體,就產生了一種特別懈怠的思維方式(其在紐約的制度場所,就是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大自然已經死亡,文化就是一切,萬事萬物都被斡旋到了這樣一種地步,無法看到其真正的本質,所有的意義都取決于表現。“所謂高級藝術”與普遍感知相嚙合的方式,就是一步跨出古老的“精英”傳統走上“先鋒鋒刃”(cutting edge)的黃色磚石路,穿過“解構公寓”和“符號森林”抵達杰夫 昆斯(Jeff Koons)的陶瓷豬。
結果是這段路并不值得一走。它產生的是一種小聰明的新藝術,其回報越來越小。大眾傳媒的藝術來源遠遠不能給藝術家帶來持續的靈感,已經成為一條死胡同,而且已與制度性藝術教學結合起來,產生了一種向信息而非經驗徹底投降的美術文化。這忠實地反映了現代經驗耗干了具體性的那種普遍現象——即不讓事件而讓不加消化的純粹數據大行其道,通過讓想象生活的織物加以吸收來獲得意義。80年代藝術已經麻木的折衷主義,其對東拼西湊之作和歷史東搬西挪的喜愛,其把藝術史純粹當作一盒標本的短視——這都是文化向皮相徹底投降的標志,結果是只有風格而無實質。這種想象荒蕪狀態讓人想到俄國人開的一個可悲玩笑:今天,你可以電話預訂牛排——并在電視上拿到牛排。
繪畫和雕塑的價值觀以及大眾傳媒的價值觀之間,有著極度的差別。藝術需要長時間地觀賞。它是一個客體,作為人世的一件物體有其自身的比例和密度,其形象不會一晃而過,可以凝視之,可以重返之,可以根據其自身的歷史而細查之。藝術品層層疊疊地羅織著關于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指涉,這兩種世界并不僅僅是偶像的世界。它可以獲得(但不會自動地取得)一種精神的層面,因為精神的層面要通過其引人沉思的力量才能崛起。美術品比任何一組等待解構的社會符號都要大,無限之大。但其抵達社會的程度卻要比大眾傳媒抵達的范圍小,而且,它能通過成為大眾傳媒所不能成為之物,找到幸存的理由。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如果誰打開“藝術”,將越來越16多與藝術毫無關系的主宰媒介納入其中,那種外星人黏稠物似的東西就會占上風,其好的結果也只能是一種形式雜、影響時間短的概念藝術,還試圖蔚為壯觀。靜態的、手工制作的視覺藝術不可能為大媒介提供一種答案,甚至都不可能有效地揭穿其真相。大多數80年代藝術家與之的關系,就是一個相當堅韌的蒼蠅與蒼蠅紙的關系。
這一點可在羅伯特 隆戈(Robert Longo)80年代的早期作品中看到——一堆超大尺寸的大雜燴,其中混雜著老練的技術和露骨的傷感,快感多于共鳴。這一點還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芭芭拉 克魯格(Barbara Kruger)對約翰 哈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進行仿冒的作品中,以自認為帶有“挑戰性”的口號講述著被操縱的身份。在珍妮 霍爾澤(Jenny Holzer)的飾板和發光二極管讀出器(魅力可能致命,等等)中,這一點甚至更為純粹、更為枯燥——都是一些失敗的警句,無法作為詩歌發表,但能在藝術語境中幸存。其一本正經的說教,太讓人想起前電子化時代美國人的女兒常在采樣板上刺繡的那種貞潔的感傷。新表現主義之后,在美國大出風頭的作品都以政治正確為驕傲,但這些作品傳達出的大部分信息,多半像是從西聯匯款公司發出的。這一代人中,可能絕無僅有的一位美國藝術家是辛蒂 雪曼(Cindy Sherman),她好不容易才把一種真正讓人戰栗的感覺引入了根據媒介制作的作品中,為照相機展演一支由性別漫畫人物、噩夢和奇形怪狀構成的游行隊伍。
今日紐約正在創作的藝術中,似乎沒有多少真正具有重大影響,這跟50年代末的巴黎適成一種強烈的類比。那時,法國人忙著說服自己相信,蘇拉熱(Soulages)、波利亞科夫(Poliakoff)、哈通(Hartung)、馬蒂厄(Mathieu)以及其他藝術家等都是一代天驕,最終能步巴黎畫派創始人之后塵,那些人中除了畢加索和布拉克(Braque)之外,大多早已過世。幾位年紀較輕但很重要的藝術家尚還健在,仍在創作:賈科梅蒂(Giacometti)、杜布菲(Dubuffet)、巴爾蒂斯(Balthus)和讓 埃利翁(Jean Hélion)。當然可以相信,這些儲水罐一樣才氣橫溢的人并未江郎才盡。但在今天,300年來及時次,在巴黎從事創作的人里沒有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紐約也是如此。這座偉大的城市作為一個市場中心帶著瘋狂的精力繼續前行,那是一座巨大無比的股票交易所,以持續上漲的價格把各種各樣的藝術拿來交易。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新畫廊蜂擁而至,提前把作品封為經典、投標出價打破紀錄、把該城大部分博物館改成推銷機器等做法,使得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即激勵重大新藝術的產生并心智健全地加以培養的能力——大大降低。
這要部分歸因于經濟壓力,特別是來自房地產市場的壓力。它剝奪了青年藝術家——以及小型17戲劇公司、舞蹈團體及其他人——在曼哈頓的創作空間。
當然,關于這一點的怨言,是紐約生活質地中老早就存在的一個部分:早在20世紀20年代,人們就抱怨說,格林威治村聚居的那批放蕩不羈的文化人紛紛早夭,這個情況被后來的記者稱為士紳化現象。
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曼哈頓終于再也不能為藝術家提供他們能夠付得起錢的創作空間了。認為紐約畫家能住在市中心一間很大的白色閣樓的看法——放蕩不羈的文化人擁有工業空間——其真實性大約就如另一種誤解一樣,以為法國畫家都戴貝雷帽,住在蒙帕爾納斯高高的畫室里。紐約藝術家中那批搞創作的放蕩不羈的文化人背水一戰,是在70年代初。那時,蘇荷區尚未被命名,僅有兩家畫廊(保拉 庫珀和馬克斯 哈欽森),以及兩家酒吧,即法內利咖啡廳和早已夭折的路易茲酒吧。西百老匯現已被精品時裝店進占的底層樓面,當時都還頑強地做著小生意——硬木地板公司、磨刀店、注塑模壓機店、織物邊料倉庫:他們都是可以回溯到內戰時期往昔工業時代的幸存者。他們的實用主義,似乎為當時在上面閣樓居住、睡活動折疊床、租工業用地(一過五點半就不再送暖)的那些半合法身份租戶創作的那種藝術,提供了一種保險。美國這批放蕩不羈的文化人的編年史,至今仍不大有人撰寫。但是,普林斯大街1971年月租150美元,1974年作為無產權樓面售價為25 000美元的閣樓,到了1987年標價就到了75萬美元。
住在蘇荷的這類藝術家,能住那樣的地方,是在15年或20年前。今天,在下東區任何一幢冰毒販子住在門階,無業游民不脫褲子就在二樓樓梯平臺上撒尿的無電梯公寓, 每月租金都要每平方米一美元——畫家需要創作的話,就算公道至少也要1 000美元。于是,藝術家為了尋找創作空間,過河來到貝永或霍博肯,為了看畫展而乘車進城。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他們倒不妨別再自稱“紐約藝術家”了,因為他們早已不再構成一個社區。1970年,一個想搬到曼哈頓的青年畫家可能會自我武裝起來,準備為在紐約生活而掙扎一番,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她更可能會放棄這個想法而待在芝加哥不動。
這樣,盡管20世紀80年代末的曼哈頓作為里程碑式的中心和文化市場,在美國沒有任何一座其他城市能夠與之匹敵,但它以有意義的方式吸納新人、培養新人的能力幾乎消失殆盡。這是一個糟糕的兆頭。能為紐約加油助推的,一向都是活著的藝術家的作品。他們創作時相信自己的作品不可能在別的地方,而只可能在那兒得到的成長。藝術天才的臨界物質能放射出宣告中心成立的活力,其萬有引力場能不斷吸納更多的天才,仿佛一顆星星的燃燒能夠維持反作用力。18這一過程現正消亡。而且,這種熵的感覺雖在巴黎不成其為問題,但因紐約市民生活的衰朽而加重。在某種程度上,曼哈頓的堅韌、骯臟和掙扎,對藝術家來說是一種刺激:從它那種咄咄逼人的拜金主義中,能崛起各種各樣特別的詩意和特殊的樣貌——直到80年代后期,這時,紐約的不平等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此時,人們疑竇頓生:一座處在古亞述國王薩達納帕一樣富有和加爾各答一樣苦難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城市,能夠促生出一種心智健全的文化嗎?這座城市取自藝術家的東西,是否多于它給予藝術家的?干嗎不住在舊金山或芝加哥(或巴塞羅那、柏林、悉尼),偶爾造訪紐約,逛逛那兒的博物館和畫廊,其他時間就忽略其吸引力呢?
紐約從來不是天堂,而住在那兒,生活在四十分之一的美國人才能享受的那種收入水平之下,從來都不容易。(那些抱怨說曼哈頓街道骯臟,好像這是什么新鮮事的人,應該去查查19世紀40年代的紐約編年史,百老匯現存的那種收垃圾方式,那時是由一群群半野的豬代勞的。)但是,里根時代——私人暴富,公共污穢——的精髓,就是在紐約大出風頭、龍騰虎躍起來的。紐約市長郭德華(Ed Koch)治下有半數公共官員,就像里根治下的華盛頓官員,似乎都參與了某種犯罪騙局,要不就厚顏無恥地不知避嫌。城市生活蛋白質的曼哈頓中產階級感覺自己就好像被夾在一小撮新富大講排場、令人惡心的外殼和毫無希望的窮人越來越意志消沉的一大板塊之間,于是加大了跨橋過河向其他行政區移民的速度。電視新聞和通俗小報愈加貶值。現實短缺的情況,在大搞促銷崇拜和名人崇拜的誘使下變得尖銳起來。在房地產的貪婪、惡化的種族主義、對犯罪問題的恐懼、市場爆炸等壓力之下,市民空間感開始崩潰。跟著又出現了艾滋病。
上述這些痼疾,都不僅限于哈德森河上這座罪惡淵藪,盡管紐約人(個個都愛災難場面)喜歡動輒就說曼哈頓好像他們的特別實驗室,某種類似威爾斯科幻小說中莫羅博士島的地方,那兒滋生著各種各樣的畸形人。不過,即使社會處于緊張狀態,甚至有瘟疫,這些東西本身也不能保障一個偉大的藝術中心必定衰落。德拉克羅瓦的巴黎也不是烏托邦,除了對于少數人來說是如此,而200年前,許多倫敦人對倫敦的體驗,就像紐約人如今對紐約的體驗一樣:人人為錢而瘋狂,處處生活都危險,無時不受“犯罪階級”的威脅,無刻不因無產階級的吸毒成癮而大傷元氣。但那時和現在之間的差別在于,世界文化活動的模式早已使單一的帝國中心陳舊過時。換言之,紐約依19然只是一個中心,而不像其藝術界過去想象的那樣,是的中心。此外,其中心地位主要以市場為基礎,而市場跟文化活動毫無關系。幾年前,有一個很流行的新馬克思主義論點(反正在學院很流行)認為,細膩的品位和鑒賞力只是一種假面,下面掩蓋的是市場活動——那不過是一種溫文爾雅的方式,能讓巧取豪奪的重商主義為自己吐出委婉之語。凡是相信這一點的人,都應該看看今日的藝術市場,并改正自己的觀點。如今主宰這個市場的人,幾乎全部都是操縱金融者、時尚犧牲品和富有卻一無所知者。作為鑒賞者的收藏家早已被從中擠了出去。鑒賞能力對這個市場的進步是一種阻礙——它不過是通貨膨脹行進之路上的一撮灰塵而已。在市場惡性的左右之下,真正的專業技能實際上成了累贅,而且很快就會成為累贅。市場的目標就是抹掉所有可能阻礙任何東西成為“杰作”的價值觀。在紐約成為震源中心的這種情況下,博物館的地位就像批評家的地位一樣變得日趨削弱。而且,由于美國對國家贊助藝術的思想從來都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因此,它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機構無一不跟市場捆綁在一起。
羅伯特 休斯是美國爭議的藝術評論家——也是好的藝術評論家。
——馬丁 米勒《名利場》
他的攻擊到致命的程度……他關于‘清澈明朗、深思熟慮、誠實而又冷靜,這仍然是繪畫藝術的主要美德’的基本信念,成為他最熱情奔放的寫作支柱。
——多爾 艾什頓《華盛頓郵報》
休斯對藝術品的物理特征,有著一種格外強烈、幾乎到了放肆程度的意識。
——尼古拉斯 詹金斯《今日新聞》
羅伯特 休斯在“藝術評論家”的兄弟姐妹會中卓爾不群,獨樹一幟。如果你不信,只看幾頁就行——好還是把《批評》全書看完。他的見解一如他的散文風格,寫得至為明白曉暢。他的論點一如他對質量好壞、手法高低,特別是當代藝術個案中真偽之間差異的看法,也是極為敏銳的。
——弗蘭茲 舒爾茨《芝加哥太陽報》
18世紀有鑒別力的才子,都拿蒲伯作標桿。今日有鑒別力的鑒賞家,都有賴于休斯。
——查克 吐瓦迪《奧蘭多前哨報》
批評家很少能做到既誠實不欺,又口若懸河,誰都沒法做得像休斯這樣派頭十足,無比瀟灑。
——約翰 麥克唐納《悉尼晨鋒報》
一本頗有見地,而且常常極為尖刻的文化批評著作,研究了社會墮落和持久創造力之間的反差。
——《費城詢問者報》
(該書)意在澄清休斯迷戀的一個問題:現代藝術的情境,并通過這個問題,探尋現代性本身的整個思想……這離后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評判,已經近到不可能再近的地步。
——戴維 里夫《洛杉磯時報》
很好,經常在當當家買
有幾處紙張是爛的
很好
書的質量很棒,紙質好,是正版很滿意。這次送貨速度有點慢,因為讀書日買的估計包裹很多,收到書的瞬間等待是值得的。書大概是世界上最物美價廉的商品了吧……
好書!!!絕對精品!包裝到內容都好!
很好123
挺好。。。
很好,不錯呦!
整體感覺好
打折總是忍不住,買來細細研讀
紙張很好!
紙張很好!
書很好!!
包裝完好,物流很快!
非常好的一本書,作者寫得深入人心。當當正版書
紙張很好!
紙張很好!
我是好滿意的
書很好!!
挺好的,朋友幫忙收獲了還沒來得及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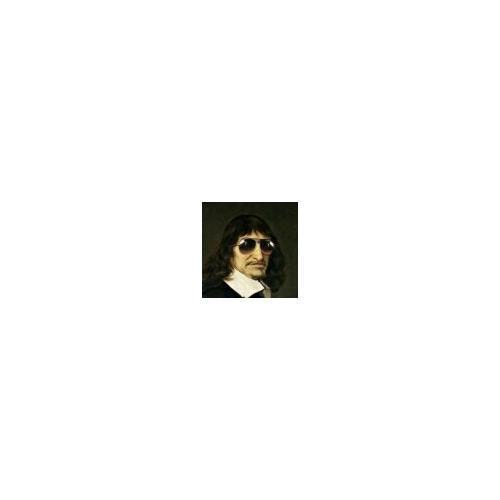 挺好的,值得收藏
挺好的,值得收藏
包裝精美,印刷不錯,老師推薦的書!
超級喜歡,nothing if not critical.
當當網促銷活動的書價格真是實惠,但是物流速度有些慢,客服水平有待提高。這是本推薦專業入門書,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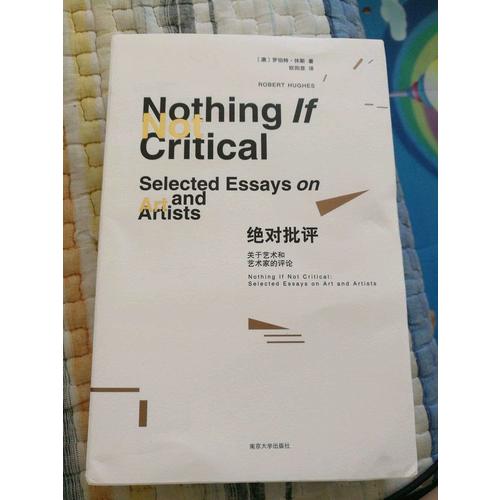 朋友推薦的書,很厚,還沒開始閱讀,從目錄來看是以年代為順序,講解的各時代的藝術大家
朋友推薦的書,很厚,還沒開始閱讀,從目錄來看是以年代為順序,講解的各時代的藝術大家
羅伯特·休斯是澳大利亞著名藝術批評家,書不錯
羅伯特·休斯是這樣一個奇才,他獨具個性的聲音從一片圣詠合唱中浮現出來……足智多謀,幽默機智,很有見地,編年史般地記錄了藝術與金融投機聯姻之后的瘋狂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