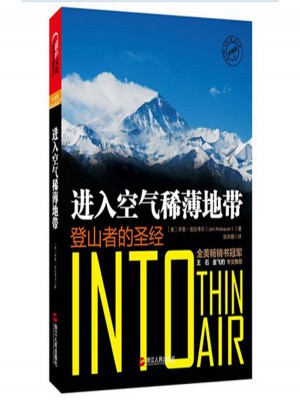
進(jìn)入空氣稀薄地帶(登山者的圣經(jīng))
- 所屬分類:圖書 >旅游/地圖>戶外探險(xiǎn)
- 作者:(美)[喬恩]?[克拉考爾]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
- 國(guó)際刊號(hào):9787213051111
-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shí)間:2013-04
- 印刷時(shí)間:2013-04-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shù):252
- 紙張:輕型紙
- 包裝:平裝-膠訂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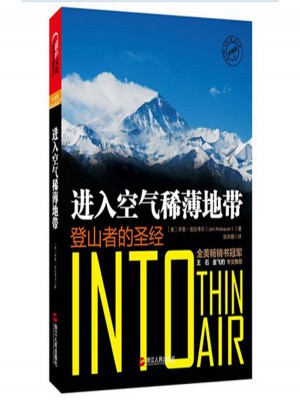
進(jìn)入空氣稀薄地帶(登山者的圣經(jīng))》是珠峰登山歷史記錄慘痛的一場(chǎng)山難,12名登山者罹難,是自人類搶先發(fā)售登上珠峰以來,死亡人數(shù)很多的一個(gè)登山季。
1996年,喬恩?克拉考爾作為《戶外》雜志特派記者跟隨一支商業(yè)登山隊(duì)攀登珠峰。5月10日,克拉考爾及其他幾名隊(duì)友成功登頂并安全下山。然而數(shù)小時(shí)后他才獲悉,其余的19名登山者在下山途中遭遇暴風(fēng)雪,被困在海拔8000多米的地方。很終12人葬身風(fēng)雪中,克拉考爾一個(gè)人坐在雪地上,想厘清過去72小時(shí)里發(fā)生的一切,事情為何會(huì)發(fā)展到如此地步?
如果一切可以重來,事情是否會(huì)是另外一種結(jié)局?
進(jìn)入空氣稀薄地帶(登山者的圣經(jīng))》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喬恩 克拉考爾(Jon Krauer)美國(guó)暢銷書作家,《戶外》雜志專欄作家、登山家。親歷1996年珠穆朗瑪峰山難后,他在《戶外》雜志發(fā)表的分析報(bào)道(后來擴(kuò)展為本書)獲"美國(guó)國(guó)家雜志獎(jiǎng)"。 除了本書,喬恩 克拉考爾還著有《荒野生存》、《艾格爾山之夢(mèng)》和《天堂的旗幟下》等。其中《荒野生存》出版后,長(zhǎng)踞《紐約時(shí)報(bào)》暢銷排行榜達(dá)兩年以上,為他贏得杰出探險(xiǎn)類作家的贊譽(yù)。
推薦序一 登山,僅憑勇氣遠(yuǎn)遠(yuǎn)不夠/王石
推薦序二 我用珠峰丈量人生/金飛豹
序言 生命中無法釋懷之重
前言 漫長(zhǎng)的24小時(shí)
Part 1 重拾珠峰夢(mèng)
01 因?yàn)樯骄驮谀抢?/p>
02 至關(guān)重要的信任
03 神秘的夏爾巴村莊
04 生命中從未企及的高度
Part 2 海拔8848米的考驗(yàn)
05 最初的考驗(yàn)
06 不合格的攀登者
07 第二具尸體
08 每座山都是一個(gè)神靈
09 加爾文式的艱難之旅
Part 3 狂熱登頂路
10 突如其來的死訊
11 名義上的隊(duì)伍
12 與時(shí)間賽跑
13 一個(gè)人的勝利
Part 4 真相72小時(shí)
14 決定生死的15分鐘
15 致命錯(cuò)誤
16 執(zhí)著的代價(jià)
17 8000米級(jí)的道德
18 難以直面的死亡數(shù)字
19 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
20 幸存者的內(nèi)疚
跋 山的陰影
附錄A 關(guān)于與布克瑞夫及德瓦爾特爭(zhēng)論事件的說明
附錄B 1996年春季珠峰攀登者名單
致謝
譯者后記
4月16日星期二,黎明前。在大本營(yíng)調(diào)整兩天后,我們?cè)俅蜗蚩撞急偾斑M(jìn),進(jìn)行第二次適應(yīng)性短程攀登。我小心翼翼、緊張兮兮地沿著咆哮的冰道蜿蜒前行,我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已不像靠前次冰川之旅時(shí)那樣粗重了,說明身體開始適應(yīng)這里的海拔高度了。但我對(duì)搖搖欲墜的冰塔的恐懼卻絲毫未減。
我曾希望海拔5790米處那個(gè)被費(fèi)希爾隊(duì)的一個(gè)家伙稱為"捕鼠器"的巨大冰塔已經(jīng)崩塌,可它仍晃晃悠悠地立在那兒,甚至比以前傾斜得更厲害了。我又一次在血流加速中和冰塔的恐怖陰影籠罩下急速攀登。到達(dá)冰塔頂部時(shí),我雙膝跪地,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并因血管中產(chǎn)生的大量腎上腺素而哆嗦不止。
靠前次適應(yīng)性短程攀登時(shí),我們只在1號(hào)營(yíng)地逗留了不到一個(gè)小時(shí)就返回了大本營(yíng)。這一次,霍爾計(jì)劃讓我們?cè)?號(hào)營(yíng)地里度過周二、周三兩個(gè)晚上,接著繼續(xù)向2號(hào)營(yíng)地前進(jìn),并在那里再過三個(gè)晚上,然后返回。
上午9點(diǎn),我到達(dá)1號(hào)營(yíng)地的時(shí)候,我們的夏爾巴領(lǐng)隊(duì)昂多杰正在凍得堅(jiān)硬的雪坡上挖掘搭帳篷用的平臺(tái)。他29歲,身材消瘦、五官清秀、性格靦腆、情緒憂郁,并且體力驚人。等待隊(duì)友們上來之際,我掄起一把空出來的鐵鏟跟他一起挖。不到幾分鐘,我就呼哧帶喘地沒了力氣,不得不坐下來休息,引得夏爾巴人一陣大笑。"感覺不行了嗎,喬恩?"他嘲笑道,"這只是1號(hào)營(yíng)地,才6000米。這里的空氣還稠密得很。"
昂多杰來自潘波切,那兒沿著崎嶇的山坡聚集著座座石壁房子和種土豆的梯田,海拔3960米。他的父親是位受人尊敬的夏爾巴登山好手。為了讓他擁有很好的攀登技巧,父親在他年幼時(shí)就向他傳授登山的基本知識(shí)。但在昂多杰十幾歲的時(shí)候,父親因白內(nèi)障失明,小昂多杰被迫輟學(xué),開始掙錢養(yǎng)家。
1984年,在為一群西方徒步者做廚師時(shí),昂多杰引起了一對(duì)加拿大夫婦馬里恩?博伊德和格雷姆?納爾遜的注意。博伊德說:"我想念我的孩子們。當(dāng)我逐漸與昂多杰熟悉以后,他讓我想起了我的長(zhǎng)子。昂多杰很好聰明,好奇心強(qiáng),有求知欲,善良得近乎天真。他每天在高海拔地區(qū)背著巨大的行李,還流著鼻血。"
在征得昂多杰母親的同意后,博伊德和納爾遜開始在經(jīng)濟(jì)上資助這位年輕的夏爾巴人,這樣他就可以重返學(xué)校完成學(xué)業(yè)了。"我永遠(yuǎn)都忘不了他的入學(xué)考試(為進(jìn)入希拉里爵士在孔布創(chuàng)辦的地方小學(xué))。他比同齡的孩子顯得矮小。我們和校長(zhǎng)還有另外四名教師擠在一間小屋里,昂多杰站在中間,雙膝不住地顫抖,他搜腸刮肚地想回憶原來學(xué)過的東西以應(yīng)付這次考試。我們都汗流浹背……他被錄取了,但是得跟小孩子們一起上一年級(jí)。"
昂多杰成為了一名能干的學(xué)生。在接受了相當(dāng)于八年級(jí)的教育后,他重返登山和徒步旅游業(yè)。博伊德和納爾遜曾數(shù)次回到孔布,見證了昂多杰的成長(zhǎng)。"因?yàn)楂@得充足的營(yíng)養(yǎng),他長(zhǎng)得又高又壯,"博伊德回憶道,"他興奮地告訴我們他在加德滿都的游泳池里學(xué)會(huì)了游泳。25歲左右的時(shí)候他學(xué)會(huì)了騎自行車,并迷上了麥當(dāng)娜的音樂。當(dāng)他靠前次將禮物――一條精心挑選的西藏地毯送給我們的時(shí)候,我們知道他真的長(zhǎng)大了。他希望成為施予者,而不是獲取者。"
昂多杰作為一名身強(qiáng)體壯、足智多謀的登山好手在西方登山界中聲譽(yù)四起,被提拔到了夏爾巴領(lǐng)隊(duì)的職位,并于1992年在珠峰上為霍爾工作。霍爾1996年的探險(xiǎn)活動(dòng)開始之前,昂多杰已經(jīng)登頂珠峰三次了。帶著無限的敬意和明顯的好感,霍爾稱他為"我的左膀右臂",并多次表示昂多杰對(duì)我們成功登頂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我的很后一名隊(duì)友疲憊不堪地走進(jìn)1號(hào)營(yíng)地的時(shí)候,陽光依舊燦爛。但到了中午,從南面吹來了一團(tuán)高卷云。下午3點(diǎn),濃云在冰川上空翻滾,呼嘯的狂風(fēng)夾著雪片不停地砸在帳篷上。暴風(fēng)雪肆虐了一整夜。清晨,當(dāng)我爬出與漢森共住的帳篷時(shí),30多厘米厚的新雪覆蓋了冰川。雪崩在十幾處地方順著陡峭的冰壁隆隆而下,我們的帳篷安然無恙。
4月18日星期四的黎明,天空放晴了。我們收拾好行裝前往2號(hào)營(yíng)地,踏上一段6公里或者說垂直距離520米的路程。路線將我們帶到西庫(kù)姆冰斗的緩坡之上。這里是地球上挑選的峽谷,是孔布冰瀑在珠峰山巒腹地挖出的一個(gè)馬蹄形的峽谷。努子峰海拔7849米的山體形成了西庫(kù)姆冰斗右側(cè)的冰壁,而珠峰巨大的西南壁則構(gòu)成其左側(cè)的冰壁。洛子壁那寬闊而高聳的冰峰在它的頭頂隱約可見。
我們從1號(hào)營(yíng)地出發(fā)時(shí),天氣異常寒冷,我的手都被凍僵了。但當(dāng)太陽的靠前縷光芒照在冰川上時(shí),西庫(kù)姆冰斗那鋪滿冰的冰壁就像一個(gè)巨大的太陽能爐子,吸收并向外散發(fā)著熱量。突然間我又熱得難受,擔(dān)心在大本營(yíng)襲擊過我的偏頭痛要再次發(fā)作。我脫掉衣服,只穿一條長(zhǎng)內(nèi)褲,并在棒球帽里塞了一把雪。接下來的三個(gè)小時(shí)里,我沿著冰川艱難地穩(wěn)步上行,偶爾停下來喝口水,或者當(dāng)雪在我亂蓬蓬的頭發(fā)上融化時(shí),往帽子里再塞一把雪。
到達(dá)海拔6400米的時(shí)候,我已經(jīng)酷熱難耐、頭暈?zāi)垦!E既婚g我發(fā)現(xiàn)小路旁有一個(gè)裹在藍(lán)色塑料布里的龐然大物。我那因高海拔而變得遲鈍的大腦用了一兩分鐘才判斷出這是一具尸體。我被嚇呆了,足足盯了它好幾分鐘。晚上,我向霍爾問及此事時(shí),他也不敢肯定,他認(rèn)為遇難者是一名死于三年前的夏爾巴人。
位于海拔6490米的2號(hào)營(yíng)地由120個(gè)帳篷組成,它們散落在冰川側(cè)磧邊緣光禿禿的巖石上。在這里,高海拔顯現(xiàn)出了它那可怕力量,使我感覺猶如受到烈性紅酒的折磨一般,吃飯乃至看書都讓人痛苦不堪。隨后的兩天里,我?guī)缀跏怯檬治孀∧X袋躺在帳篷里,盡量將身體蜷成一團(tuán)。到星期六感覺稍好一些的時(shí)候,為了加強(qiáng)練習(xí)盡快適應(yīng)環(huán)境,我順著營(yíng)地向上攀登了300多米。然而就在距離主路46米的西庫(kù)姆冰斗頂部,我在積雪中撞見了另一具尸體,更確切地說,是尸體的下半身。從衣服款式和老式皮靴來看,遇難者應(yīng)該是個(gè)歐洲人。他的尸體至少在山上躺了10~15年。
靠前具尸體讓我?guī)讉€(gè)小時(shí)都驚魂未定,但遇到第二具尸體時(shí)那種恐懼感轉(zhuǎn)瞬即逝。沒有幾個(gè)蹣跚而過的登山者會(huì)多看這些尸體幾眼。山上仿佛有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人們假裝這些干枯的遺骸不是真實(shí)的,仿佛我們無人敢承認(rèn)山上險(xiǎn)象環(huán)生。
P76-79
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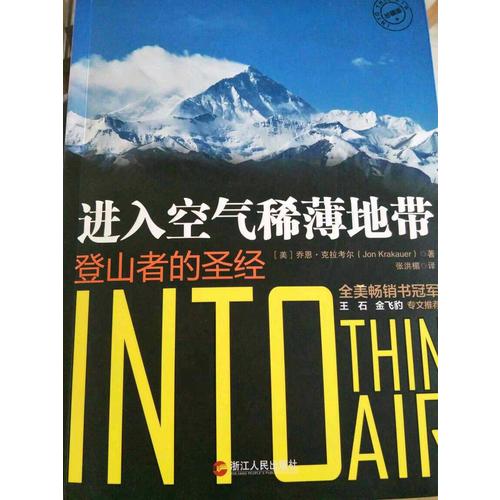 很好的書上次看馬未都的節(jié)目介紹的,就心心念念,終于買了,這下要好好看看了
很好的書上次看馬未都的節(jié)目介紹的,就心心念念,終于買了,這下要好好看看了
書的質(zhì)量挺好的,是正版書,看過了電影,兒子還要讀一讀小說才過癮。